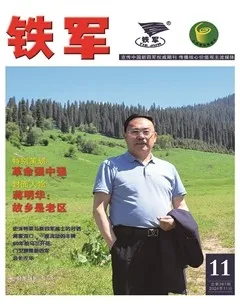革命强中强

能征善战、文武兼备的新四军,不仅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也培养铸就了一大批治国治军人才,为人民共和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新四军走出来的栋梁之材灿若繁星,他们有刘少奇、李先念、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粟裕、谭震林、黄克诚、方毅、张爱萍、吴学谦、邹家华、韦国清、叶飞、张鼎丞、陈丕显、彭冲、陈慕华、洪学智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也有薛暮桥、孙冶方、范长江、李一氓、钱俊瑞、夏征农、冯定、贺绿汀、沈西蒙、亚明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学者和文化人。
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走来的新四军,以“革命重坚定”的政治信仰笑迎惊涛骇浪,经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更加所向披靡,在克敌制胜中开创了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
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和锤炼了铁的新四军。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首批授衔到1965年授衔的1614名开国将帅中,新四军出身的将领总计371名,占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被授予了将帅军衔,而获得军事家称号的却为数不多。1984年,党和国家认定33位开国功臣为军事家,1994年又增补了3位,这便形成了世人熟知的36位共和国军事家阵容。36位军事家中有9位来自新四军,他们分别是陈毅、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罗炳辉、李先念、叶挺、徐海东。
陈毅是新四军元老级人物,先后任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新四军军长等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成就了这位治国治军杰出人才。他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认定为军事家当之无愧。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对党忠诚就是无论顺境逆境,都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说到这里,总书记动情地讲了一段陈毅的故事:陈毅同志把“革命重坚定”作为一生的座右铭。南昌起义时他没有赶上,后来冲破重重难关找到了起义队伍,到天心圩时队伍只剩下800人,他协助朱德同志收拢了部队,并对大家说:“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
只有经过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被党和国家认定为军事家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毕生心心念念在铁军,他被蒋介石囚禁数年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叶挺虽然没有看见革命胜利的一天,但他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却功垂千秋。正是抱定“革命重坚定”的铁的信念,新四军将士始终铁心跟党。参谋长张云逸,谨记“以遂初志,而尽己责”的信念,始终初心不改,被毛泽东称为“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第六支队司令员、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哪一位不是上马打江山、下马治天下的杰出英才。第一师师长粟裕,被誉为人民军队的战神,享有常胜将军的美称。曾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从八路军调往华中战场后,率领部队与日军连续激战,取得了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后,终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病倒在皖东战场上。皖南事变后,黄克诚从八路军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他领导的三师成为新四军战力最强的部队之一,无论是坚持抗战,还是挺进东北,都是党中央手中的主力和王牌。
古语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新四军纵使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7000余人的重创,依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经过重建军部后的这支英雄铁军,愈挫愈坚,最终发展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威武胜利之师。试想,领衔这支部队的优秀指挥员,日后怎能不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治国治军人才呢?
新四军始终举旗跟党的辉煌历程充分证明,党的绝对领导是风雨来袭时人民的坚实依托,是威武之师所向披靡的组织保证,更是惊涛骇浪中锻造领军人才的首要条件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冬子妈妈吟唱的《映山红》,以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道出了在黑暗中苦斗的苏区百姓和红军游击队渴盼共产党的强烈欲望。
“经历严寒的人,尤为向往和珍惜太阳;经历过远离党中央孤军奋战南方丛林的红军游击健儿,更加体会到与党永远在一起的极端重要性。”经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回忆往事时不约而同地说:一部新四军发展史,就是一部听党话、跟党走、为党举旗、对党忠诚的教科书。新四军视“坚信共产主义信仰为培养选拔干部之首”,从建军初期就十分重视根植共产主义信仰,坚持以加强党的建设引领人才建设。几位老战士不约而同地回忆道,早在1938年底,新四军各级党组织就发起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宗旨的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运动。袁国平、邓子恢还专门签署训令,强调“从政治上保证继承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一切优良传统,特别是自己军队固有的优良传统,以提高革命自信心、自觉心与觉悟性”。不仅如此,新四军领导人还经常亲自给部队授课,再三叮嘱各级干部要坚信共产主义,带头听党话、跟党走,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等都是如此。

一位在新四军长期从事干部工作的老战士动情地描述当年的情景:新四军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政治信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说到这里,这位新四军老兵由衷感叹:有坚决听党指挥的干部站立在前,铁军将士谁不坚信马列主义,坚信人民必胜?那时候,大家抱定“生是党的人,死为党的魂,宁可牺牲性命,绝不丧失信仰”的信念,自觉把个人的一切融入到听党话、跟党走的行动之中。这种铁心跟党的浓厚氛围,对新四军培养人才来说犹如春风化雨。
强军依靠人才,制胜亦靠人才。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铁军人才辈出,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胜利之时,新四军已拥有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万余次,毙伤俘(包括投诚、反正)日伪军47.1万余人,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历史充分证明,新四军不仅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也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人才准备赢得了先手棋。
从皖南教导总队,到华中抗大分校,再到战地草棚党校,新四军既吸纳人才,又倾力培养,在实战中造就了数不胜数的打赢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急需的各类人才
华中大地文化底蕴丰厚,人才济济的新四军从成军之初就显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这支相对有文化的部队,十分注重文化强军,通过以才纳才、以才育才等有力措施,努力把各方人才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形成了万众一心打败强敌的磅礴力量。
新四军从一开始就坚持用战略眼光聚集各方优秀人才。1937年11月,叶挺从延安受命一回到武汉,就为新四军吸纳人才四处奔波。他亲自请来了医学专家沈其震、留日归来的林植夫、擅长军需工作的叶辅平等加入新四军。1938年10月,项英在南昌听说经济学家薛暮桥想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爱才心切的项英当即热情邀请薛暮桥随车一起前往泾县云岭军部。
为保证抗战人才聚得拢、留得住,军部特别规定,知识分子的津贴费发放标准一律高于其他人员。新四军不仅广纳各方贤才,而且对投奔新四军的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军领导大胆选拔非中共党员的沈其震担任军医处处长,林植夫任敌工部部长,薛暮桥任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泰国华侨陈子谷任敌工部科长。仅据1941年10月新四军第一师统计,全师六成以上的营连排干部是25岁以下的知识分子,基层政治指导员中有80%以上来自青年学生。大批知识分子加入新四军,为聚才育才、推进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吸纳是基础,培养是关键。1938年1月,新四军成军不久就在南昌创办了第一所旨在培养军政干部的教导队。同年4月,教导队随军部移驻皖南岩寺,扩编为教导营,同年8月,又扩编为教导总队,还专门安排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一份新四军军师领导人亲自担任抗大分校校长政委的名单,足以见得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大背景下,在民族危急之际,新四军高中级指挥员是如何为培养抗战和根据地建设人才呕心沥血的。领导率先垂范,新四军各抗大分校越办越红火,贡献也越来越大。从1940年到1945年,新四军抗大毕业学员多达2万余人,这些干部迅速成长为华中抗日战场和根据地建设的骨干与中坚;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成为新时代值得永远景仰的超级明星。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根据敌后抗战急需大批人才的形势,于1941年四五月间果断决策并迅速在盐城建立了华中党校,并亲自担任校长。华中党校在盐城万寿宫坚持了不到两个月,为应对日军大“扫荡”,党校迁到阜宁县西南的汪朱集。那里是穷乡僻壤,连一个令人满意的大教室也找不到。刘少奇态度十分坚决:“党校一定要办,没有屋基向荒地要,没有砖瓦找芦苇。”他带领大家割芦苇、整荒地,盖起了一间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草棚作为课堂,草棚党校就此诞生。草棚党校开课后,不仅党校学员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跑过来听。刘少奇授课时,大草棚里挤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坐得满满的。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刘少奇干脆搬进了党校。他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在老百姓家里,前后达三四个月。坚持高标准教学的草棚党校虽然只办了4期,但正式学员就有1200多人,如果加上不定期来“蹭课”的人,整个办学期间的受教人数十分可观。经过党校学习,绝大多数学员都获得了哲学、党史、党建等方面比较系统的知识,对于新四军人才方阵的不断壮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日战场是没有围墙的顶级干校,在烽火硝烟中,新四军注重人才制胜的同时,坚持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培养军民融合人才的模式值得借鉴和传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不但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练就了善打险仗巧仗和智勇双全的过硬本领,而且经济工作方面也是游刃有余,用现在话说,就是军事经济两手抓、两手硬。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环境虽有改善,但处境依然相当艰险。在遭受日伪顽夹击、敌我悬殊、步步艰险的不利环境中,新四军迎难而上,培养各级善打险仗、出奇制胜的作战人才。1939年7月,粟裕派得力干将廖政国率领两个连的新四军追歼一股伪军,一路追到虹桥机场,机场有军警守护,外围驻扎着一个日军小队,旁边有敌人重兵把守。可只有两个连的廖政国判断敌人并未发现自己,应该出其不意地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他果断下令攻击机场,击毙了部分日伪军,又趁势放火烧毁了4架敌机。等到大批日军赶来时,廖政国的人马早已撤出多时。此役极大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手下的廖政国胆子如此之大,“尽打神仙仗”的粟裕的用兵如神那就可想而知了。黄桥决战直捣黄龙、大唱“空城计”;苏中战役大踏步进退,“七战七捷”歼灭美式装备的敌军;孟良崮战役冒着危险虎口拔牙,全歼敌王牌部队整编七十四师;把“小淮海”打成“大淮海”,60万对80万,将长江以北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歼灭殆尽……粟裕指挥打赢的一系列“神仙仗”,无不展现出新四军人才济济的风光无限。
从苦日子中熬过来的新四军,不仅精于打巧仗,还善于因地制宜搞经济。改编后的新四军,只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微薄军饷,皖南事变后被彻底断供,他们逆境求生,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动手搞经济,不仅为巩固壮大部队提供了装备军需保障,还为培养经济管理人才提供了难得的学习和实践平台。
新四军部队有的能打仗,有的能生产。粟裕的一师、谭震林的六师战斗力强,罗炳辉的二师、曾希圣的七师善于搞经济。当时,二师主要在淮南一带活动。淮南土地贫瘠,粮食缺乏,部队物资供应紧张。副师长罗炳辉开动脑筋,入股民营企业,办起了染布厂、被服厂、毛巾厂,解决了部队物资供应难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在铜城创办了卷烟厂,从上海运来了卷烟机、切丝机、印刷机,从定远、凤阳、泗县弄来优质烟叶,精心研制配方,生产出了大名鼎鼎的“飞马”牌香烟,不但受到新四军的欢迎,还成为硬通货销往上海、南京等地。这些工厂的建立,使二师走出了经费奇缺的困境,还有余力支援兄弟部队。
在新四军有个说法叫“富七师,甲全军”。皖南事变后,曾希圣被任命为新四军七师政委。组建部队急需经费,曾希圣一边收容突围人员,一边想方设法筹钱。他发动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创办了一大批军民两用工厂,探索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发展之路。七师从皖江地区北上山东后,当地老百姓惊喜地发现,这些南方来的兵不仅用上了刷牙牙粉,还有小镜子和梳子,军服面料也比八路军的洋气。善于发展经济的新四军不仅保证了自身需求,关键时刻还向八路军各根据地支援了大量物资钱款。从1943年秋至1944年10月,新四军仅给太行根据地援助的钱物就高达800万元,同时,还向陕甘宁边区提供援助,党中央70%以上的经费供给来自新四军。
根据地犹如新中国的试验田,新四军精心耕耘这片红色沃土,大力培育“上马打江山、下马治天下”的贤才良将,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提前储备了数量可观的人才队伍
既把根据地作为家来建设,又把它当作新中国的试验田,新四军不惜投入精兵强将,努力实现巩固壮大抗日根据地和快速催生大批复合型人才的双重效益。
新四军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创新之举,受到了老百姓的由衷拥戴。红色政权星罗棋布,成为锻造人才的广阔天地,为新中国培养了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1942年初,组织上安排新四军女战士、清华大学毕业的孙兰到苏北根据地工作,不久年仅32岁的孙兰又被推上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重要岗位。在党组织的精心指导下,她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反“扫荡”、写文章、作演讲、审汉奸、修水利,样样走在前列。她常穿一件红色上衣走基层、访农户,和群众吃住在一起,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红衣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先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赢得了广泛赞誉。1964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时,拉着孙兰的手向大家介绍说:“你们上海的孙兰,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淮安的父母官哩!”
新四军注重以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法制建设为平台,努力锻造人民拥护、治国需要的政法铁军。从健全立法机构,到完备司法体系;从探索民主诉讼制度,到加强审判调解;从出台《人权保障条例》,到建立土地、经济、劳动、刑事、婚姻等系列法规,在抗日民主政府运作中,新四军始终重视一手抓法律法规建设,一手抓法制人才培养。1944年4月,曾在新四军军部担任执法队队长的洪沛霖,被派遣到淮南津浦路东行政公署所属的竹镇组建了人民公安史上的第一个派出所。当时,竹镇派出所的办公条件简陋、工作艰苦、环境险恶,洪沛霖不畏艰难险阻,带领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洪沛霖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领导,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江苏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他以当年领衔“第一派出所”的劲头,出色地完成了负责主审江青的任务。
新四军以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为平台,倾力培养一心为公、精通业务的财经骨干。皖南事变后,各抗日根据地陷入了财政拮据的困境。新四军在党中央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指引下迎难而上,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目标,引导各根据地在坚持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制定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不断推进根据地经济发展。1941年,日军向根据地大量输入伪造的法币、抗币以换取物资,企图“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为此,在新四军得力指挥下,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与敌伪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货币战、经济战。重建军部不到3个月,在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决策支持下,江淮银行就在盐城横空出世,使得盐城成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济和金融中心。1945年,华中银行的创建,标志着华中抗日根据地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财经战场最高峰。那时候的根据地,“二五”减租、军民大生产、反封锁与对敌贸易斗争、工商税收、根据地银行,成了老百姓口中的热词。李先念晚年时曾经为之感慨:根据地的财经建设不仅改善了民生,促进了抗战,也加速了党的经济管理人才的迅速成长。
新四军以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为平台,不断增强文化工作为敌后抗战当先锋的意识,提前培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领军人物。回望当年,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如火如荼,新闻出版、文学创作、体育运动、兴教办学,那可是百花盛开,争艳斗丽。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苏北抗日根据地期间,在阜宁卖饭曹村设立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村,成了来自上海、香港、重庆等地文化人的汇集地。当时住在文化村的文化人有阿英、扬帆、范长江、胡考、孙冶方等人,住在附近的军部鲁迅艺术工作团的贺绿汀、行政学院的车载、抗大华中总分校的薛暮桥、《盐阜大众报》的王阑西以及沈其震、骆耕漠、孙克定等一批文化人,经常会聚在文化村尽情挥毫泼墨、赋诗唱和,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名流和爱国乡绅、社会贤达,在你来我往中,结成了最广泛的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化建设运动,深深影响了投奔新四军的文化人的思想和理念,将他们的创作引领到更广阔的天地。皖南事变后,贺绿汀来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和鲁艺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育工作。这一时期,他与《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黄桥烧饼歌》的曲作者章枚等人一起,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的歌曲,在华中敌后广为传唱。同时,贺绿汀还将大量精力用在培养音乐人才上,为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文艺干部。
人民铭记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有着新四军背景的数以万计的杰出人才,奋斗在治国治军第一线,为人民共和国不断走向繁荣书写了铁军辉煌的崭新篇章。历史告诉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用凝聚着听党指挥的新四军精神的磅礴力量推进新时代人才建设重大工程,其意义与作用重大而深远。
(责任编辑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