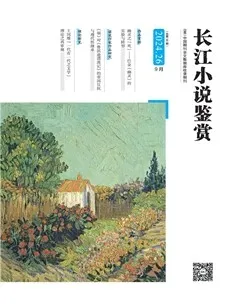规训与反抗:《天之娇女》中女性身体叙事解读
[摘 要] 《天之娇女》是英国著名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的代表作,围绕六位女性讲述各自的女性体验而展开,其中身体成为叙述的焦点。身体叙事在该剧中不仅影射女性个体的生存体验,更是窥探父权社会中女性群体生存状况的晴雨表。本文从身体叙事入手,探究女性身体对父权制范式的表征,以及女性性别身份建构的困境,同时解析女性为延展其生存空间做出的努力,以及对实现其身体体验主体化途径的探索。丘吉尔对女性身体体验的书写,展现了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从服从规训到奋起反抗的历史,表达了她对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 《天之娇女》 身体 规训 性别身份 女性空间
《天之娇女》是英国剧坛举足轻重的女剧作家卡里尔·丘吉尔的作品。剧中的第一幕聚会由20世纪80年代的成功女性马琳主持,她邀请五位来自不同历史时空的女性朋友来参加她的升职宴会,分别是:维多利亚时期环游世界的伊莎贝拉·伯德;13世纪失宠于天皇而出家为尼,并徒步穿越日本的尼州;勃鲁盖尔画作中为子复仇、与恶魔搏斗的道尔·格莱特;生于9世纪,天资聪颖却必须扮成男人才能追求梦想的教皇琼安;《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无条件服从丈夫的格丽泽尔达。
目前学界对丘吉尔戏剧的研究逐渐丰富,主要集中于丘吉尔对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丘吉尔戏剧对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革新,在其戏剧的主题研究方面,女性主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鉴于丘吉尔明确对外声称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许多学者从此角度来关注她的戏剧创作,也有学者从历史主义、存在主义等角度分析丘吉尔戏剧中的女性主义。但目前学界对丘吉尔戏剧中女性身体的关注度还不够高,国外部分学者例如艾琳·戴蒙德关注了丘吉尔戏剧表演中的身体[1],国内鲜有人研究丘吉尔戏剧中女性身体的作用,仅有刘雨婷从后人类角度分析了丘吉尔戏剧中的三种后人类身体。彼得·布鲁克斯指出,意义的躯体化伴随着身体的符号化,“身体必定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2],女性身体是女性言说自我的媒介。因此,本文围绕女性身体探究《天之娇女》中的女性如何被父权社会规训,导致女性个体悲剧和女性群体长期处于受压迫的状态,以及女性如何对此做出反抗,以获得身体自由和主体性。
身体这一概念从柏拉图开始就一直被认为是灵魂或意识的对立面。在身体-意识这一二元对立概念中,身体始终居于次要地位,直到尼采喊出“要以肉体为准绳”[3],身体才冲破意识的压制,正式进入到哲学视野中。福柯论述中身体的概念正是源于尼采。福柯认为,身体一方面具有历史性,即作为客观事物,身体成为历史对象卷入某种政治领域,不断被权力关系标记、训练、折磨,“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4]。因此,这样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受到权力的规训和约束,不断被控制、改造,进而走向规范化。由于谱系学“将通常认为属于人的不朽之物都置于一个发展过程之中”[5],因此谱系学充当了身体与历史的连接地带,“而在这个连接地带中,身体刻写了历史的印记,而历史则在摧毁和塑造身体”[6]。因此,福柯认为,身体具有被动铭写性,成了历史的焦点。另一方面,受权力规训的身体不仅带有过去的印记,而且将不断被改造,这说明身体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即具有可变性。身体的可变性恰恰表明其内在蕴含一股颠覆性力量,能够不断反抗权力规训。正如福柯所言,反抗不是一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其所反对的权力,而是与权力共生、同时存在的[7],这说明在权力对身体规训的同时,身体会做出反抗,规训与反抗同时作用于身体,身体具有历史性和可变性。正是身体的可变性赋予了主体能动性,使其在不断被规训的同时,积极反抗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针对身体的“微观权力”。因此,规训的身体存在于一个历史进程中、存在于各种权力演变中。
正是在这样的权力规训下,《天之娇女》中的女性分别言说了不同时代父权规训下的女性身体,一方面向观众展示了历史上女性身体是如何被规训的;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女性的反抗策略,由此获得身体的主体性。
一、父权规训下的女性身体
在逻各斯体系下的二元对立性别中,男性“在场”,是第一性;而女性则“不在场”,被认为是第二性,永远低男性一等。男性是拥有规训权力的主体,女性则是被规训的客体。因此,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化一方面成为女性建立主体性的他者,另一方面也是女性建立性别身份的他者。前者的结果是女性不断认同并内化父权制的范式,而后者,由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和文化意义上的性属(gender)两者概念上的差异,使依靠父权文化建立的女性性别身份变得含混。《天之娇女》以女性身体为媒介,揭示了女性是如何内化父权制的范式的,展现了女性性别身份的困境。
1.内化父权制范式的女性身体
诚如福柯所言,“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4]。父权社会中的女性身体是权力的作用对象,女性的主体性也由父权文化塑造。同时,身体的被动铭写性使女性身体成为父权文化的隐喻,因此女性身体表征父权文化。以父权文化为他者建构主体性导致女性用男性的目光进行自我审视,不断认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在这个过程中,父权社会的一切话语都是权力用来规训女性的工具,女性被卷入由父权主导的话语体系,无意识地接受并内化了这套话语体系,进一步使父权规训合理化,同时也强化了规训权力。《天之娇女》中以格丽泽尔达和尼州为代表,透过女性身体的父权文化表征,揭示了女性内化父权制的范式。
乔叟笔下的格丽泽尔达性格温顺、青春年少,她的身体是父权社会规训出的“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4]。格丽泽尔达的驯顺性可以从她的出场、点餐、对男性的无条件服从中看出来。首先,相比其他几位人物的高调出场,格丽泽尔达的出场毫不惹眼,在聊天间隙马琳才注意到她的到来。接着,马琳邀请她点餐,她坚持为自己的迟到道歉,并在未用餐的情况下拒绝了马琳的点餐邀请。马琳连忙建议她点布丁,格丽泽尔达表明自己从不吃布丁。然而,在马琳的敦促下,格丽泽尔达说:“要是大家都吃的话,我也来一点吧。”[8]这一系列行为说明了格丽泽尔达谨小慎微、不擅长拒绝、喜欢从众的性格,并且不喜欢,甚至害怕麻烦别人,在热闹的宴会选择当一个局外人。父权社会中,男性永远站在聚光灯下,享受瞩目、喝彩,女性则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中,不断被打压、规训,久而久之,女性习惯了男性处于中心而女性处于边缘的状态,即使在没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男性凝视也并没有消失,因为格丽泽尔达主动用男性的目光审查自我,所以出场时她选择默默坐下,在被马琳询问的时候,她表现得怯懦和局促不安。格丽泽尔达始终无条件服于男性,不论这个男性是她的父亲还是丈夫。在与侯爵成婚前,格丽泽尔达事事顺从父亲,即使侯爵完全不顾及格丽泽尔达的意愿,直接与其父亲商谈婚事,她对此也并无异议。侯爵虽表明“这不是命令”,格丽泽尔达可以拒绝,但如果答应,就“必须事事服从他”[8]。婚后,格丽泽尔达的确将丈夫的话奉为圭臬。对此,马琳则一语道破:“方圆几里的人都是他的臣民,他绝对是主宰着生与死的王。”[8]格丽泽尔达作为贫穷的农家女不敢说不,她自己也认为“妻子当然应该服从丈夫”[8]。婚后侯爵不断“测试”格丽泽尔达,先是迫于舆论压力假装杀了他们的孩子,实则将其送走,后又声称要娶其他人,假装要将格丽泽尔达也送走。从始至终,格丽泽尔达都对丈夫绝对服从。据格丽泽尔达所言,侯爵考验她是因为他不相信格丽泽尔达会无条件服从他,但拥有权力地位的侯爵为何怀疑一个天真无知的农家少女对他的忠诚?侯爵的言论仅是他用所拥有的权力创造出的“真理”,其真实目的是规训女性,让女性任由男性玩弄。这正体现出福柯所说的权力具有生产性。“规训权力应该生产,而不是消灭。”[9]代表父权的侯爵说婚后必须对他言听计从,这正是权力产生的“真理”,而格丽泽尔达则被此规训,人生完全由侯爵支配。格丽泽尔达已经完全内化了女性应该服从于男性的规训,因此,她代表了男性为女性建构的理想化性别身份[10]。格丽泽尔达实际上是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的典型代表。另外,格丽泽尔达的实用性体现在她正值花季,能够为侯爵提供生育价值。事实上,侯爵娶格丽泽尔达只因为“大家都希望他结婚,这样他去世后就会有继承人来照看他的臣民”[8],这说明生下继承人是侯爵结婚的首要目的,所以对侯爵来说,格丽泽尔达仅仅是能够完成这个目的的工具。福柯认为,纪律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为顺从而变得更有用”[4],对格丽泽尔达而言,纪律是来自父权社会的规训,这样的规训让她身体的实用性和驯顺性相辅相成,从而能够任侯爵摆布,为他孕育继承人。因此,格丽泽尔达实际上是传统父权制规训下的“顶尖女孩”[10]。
天皇的妾室尼州也深陷父权规训的牢笼。尼州小时候,父亲就将其作为天皇的妾室培养,她学习如何讨好、迎合,并服侍天皇。尼州第一次被宠幸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只顾哭泣”,那“单薄的睡袍被撕得稀碎”,但是当马琳说这是强奸时,尼州马上否认,辩解道:“不,当然不是,马琳,我属于他,这是我从小被养大的目的。”[8]这说明尼州已经完全内化了父权社会对她的规训。女性在不断内化父权社会规训的同时,也在不断复刻父权文化,成为父权制的继承人,而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约束由此得到延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尼州认为自己的私生女也会和她一样做天皇的小妾,“她正被精心呵护着长大,这样她以后就能像我一样被送进皇宫”[8],这体现了父权社会规训下,女性身体都免不了沦为男性玩物的悲哀,也揭示了女性内化父权制范式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父权社会中,权力、规训、知识三者互相强化、互为要求,格丽泽尔达和尼州内化父权制的范式,让她们的女性身体成为生育的工具和男性的玩物。丘吉尔通过让人物言说自己的经历,表达对女性群体的观照。
2.女性性别身份的含混
性别是天生的,而性属是由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从性别到性属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人们意识到社会文化对性别身份的建构作用。但父权社会中的两性性别身份并不平等。父权社会中,男性天然地“在场”,男性的身体成为标准;与之相反,“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1],女性身体代表缺失和不完美。由于身体在西方哲学中时常与精神对立,被看作是无意义的领域,为恢复其意义,身体被打上标记或符号,成为能指[2],成为能指的身体则具有表意功能。父权社会中的男性身体作为能指,其对应的所指是权力和地位,同时,因为男性身体成为度量女性的规范,所以衡量女性的目光带有“阳具崇拜”的色彩,而这恰恰是女性身体所缺失的,因而女性身体就意味着残缺、被剥夺和否认。在这样的父权凝视下,女性在建立性别身份的过程中会极力掩盖自身女性身体特征、规避女性身体的“缺陷”,在自我异化的同时不断与男性群体进行身份认同,以达到男女平等的状态。但这只是父权社会女性对男女不平等这一状态的想象性解决,最终现实还是会打破暂时的平衡。同时,由于这种想象性的解决是女性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否认和对男性身体的认同达成的,这就造成了父权社会女性性别身份的含混——性别(sex)属于女性,而性属(gender)属于男性——女性性别身份是悖论式的。
父权社会中,只有男性才能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同时,身处高位的男性所拥有的权力具有生产性,其生产出的知识反过来又产生和强化权力。因此不论女性如何聪明、出众,都不能直接与男性相比,只有通过在身体上或行为上同化男性,女性才能赢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天之娇女》中琼安同化男性、跻身只属于男性的职业领域,造成了自身女性性别身份的暧昧,从而导致她的悲惨结局,也挤压了女性群体的生存空间。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迫使渴求知识的琼安掩盖其女性身体特征,与男性身体同化。尽管“琼安是个神童”[8],但在当时的父权社会中,“女性没有权利进入图书馆”[8],这是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拒斥,对女性追求成功的权利的剥夺。为追求真理、获取知识,琼安十二岁就“摒弃”女性身体,女扮男装离家求学。在求学过程中,琼安逐渐习惯假扮男性身体,不断与女性群体异化。一方面,琼安假扮男性使她获得了与男性群体平等竞争的权利,所以聪明的琼安很快晋升为教皇;另一方面,琼安的异化造成琼安对女性身体的无知,最终于游行途中惨死。琼安身怀有孕,而自己却全然不知;孩子一天天长大,她误以为是自己变胖,在分娩时刚好碰上游行,最终,孩子和琼安都被乱石砸死。因分娩暴露的女性身体导致了琼安的不幸。另外,琼安悖论式的性别身份的揭露也让女性在父权社会生存的空间萎缩。在琼安的女性身体暴露后,主教们用带洞的椅子来检验即将当选的教皇是否是男性,此时男性身体成为选择教皇的终极标准。如果说琼安出现之前,男性身体只是父权社会的隐性标准,那么琼安的结局则导致了男性身体成为父权社会的显性标准,女性不能再通过伪装来想象性地解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琼安的悲剧“很快就变成一个关于僭越性别限制的警示性故事”[12],她对男性领域的僭越让父权规训更加有力,规训权力渗透得更广泛,从而进一步压缩女性的生存空间。实际上这也体现了丘吉尔本人对自由女性主义的批判,琼安挪用父权意识形态,暂时性地享有男女平等的地位,却并没有改变女性群体整体的处境。
二、获得主体性的女性身体
福柯认为:“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7]身体作为权力的对象,并非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而是可以做出反抗的。身体的被动铭写性和可变性让“女性的身体既是女性受压迫的焦点,又是女性利用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来赋权于自己的空间”[13],被父权规训的女性恰恰是通过与作用于其身体的权力博弈来获得主体性的。《天之娇女》中的女性虽然都受到父权社会的规训,除一直执迷不悟的格丽泽尔达外,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反抗,包括对生存空间的探索和个性化的母性体验,她们由此获得了主体化的女性身体经验。
1. 出走的“家中天使”
父权社会中,女性不允许抛头露面,家庭几乎是女性唯一的生存空间,同时,家庭空间集中体现来自家庭自身的制度规则和来自社会的制度规则[14]。然而,家庭和社会的制度规则体现的是男性的利益。所以,男性的生存空间比女性广泛,从权力分配上来说,男性生存空间占主导地位,两性生存空间呈现极不平衡的现象。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与身体较量的场所,在父权社会,家庭则成为规训权力与女性身体争斗的处所。“家中天使”看似是维多利亚时期男性对女性的“美誉”,实则是父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镣铐。一方面,女性被禁锢在家庭空间里,这是对女性身体上的束缚;另一方面,女性被看作是“天使”,表明父权社会中的女性性格温顺,可以任人摆布,这是对女性心理上的束缚。《天之娇女》中伊莎贝拉、琼安和尼州都曾陷入“家中天使”的圈套,然而,她们面对父权规训时敢于用被束缚、被限制的身体反抗,勇于探索女性生存空间,做出走的“家中天使”。
根据福柯所言,来自父权社会的规训权力是“对控制活动和支配实践中的一种时间性的、单一性的、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向度整合”[4],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将女性圈在狭小的家庭空间之中,对其进行操练,将女性的活动限制成重复而单一的家务活。然而,伊莎贝拉、琼安和尼州都不满足于此。伊莎贝拉曾试着听父亲的话,“尽力去当好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做针线活、学习音乐,并坚持行善”[8],父亲教她拉丁语,但这些活动都是她父亲强加给她的,伊莎贝拉的身体被束缚在家庭空间之中。最终,伊莎贝拉通过周游世界,打破了维多利亚时期“家中天使”的女性形象。通过旅行,伊莎贝拉拓宽了女性的生存空间,让女性身体从狭仄的家庭空间解放,两性生存空间不平等的现象得到缓解;同时,她“总是以淑女形象旅行”[8],由此破除了女性不适合长途旅行的刻板印象,提升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的认知。琼安对女性空间的探索和她的性别身份一样颇具悖论色彩。通过易装,琼安作为女性进入图书馆等专为男性开放的领域,之后当选教皇。在暴露身份前,琼安拓宽的仅仅是她本人作为女性个体的生存空间,而身份的暴露则导致女性群体生存空间被压缩。尽管如此,琼安对父权规训的不屈精神对处于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仍然有一定启示。因失宠而出家为尼的尼州,因不满足寺庙内的生活,选择徒步穿越日本,这为女性群体探索生存空间提供了范式。
不论家庭还是寺庙,都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空间权力规训,对此,伊莎贝拉、琼安和尼州都以身体为武器做出了反抗,获得了身体上的自由,延展了女性身体活动的空间。同时,她们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探索也各有其特点,展现了不同身份的女性群体对生存空间探索的可能性。
2. 主体化的母性体验
母性是作为母亲的女性所具备的特性。艾德丽安·里奇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中指明了母性的两层含义:一是每个女人与她生育能力以及孩子的潜在关系;二是社会习俗,这种习俗以保证所有女人都被男人控制为目的[15]。可以看出,第一层含义是母性这个词的概念意义,而第二层含义带有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该词的主观情感,是其内涵意义。内涵意义相对不稳定且无限开放,它跟随社会文化和历史时期等发生改变[16]。里奇对母性第二层含义的界定反映了父权社会权力对女性的规训,将母性归为社会习俗,母性变成父权社会给女性的枷锁,“压抑和削弱了女性的潜能”[15]。而女性则通过摆脱父权社会习俗对女性生育的控制,实现母性经验的主体化。
《天之娇女》中,尼州、格莱特和马琳分别采取不同的身体政治策略来改写父权社会对母性内涵的定义,获得主体化母性体验。首先,尼州反抗了父权社会习俗中的生育迷信,实现了生育自由。在满月仪式上,尼州和其他小妾被用棍子打击腹部,因为这样“就能生儿子,而不是女儿”[8],父权社会对生育的迷信让女性的“母性的体验与性别特性的经验都受到男性趣味的引导”[15],从而实现对女性的控制。然而,尼州并没有服从父权规训,她与天皇的其他妾室合谋反抗天皇。此外,尼州还与多位男性建立情人关系,共育儿女。尼州怀有身孕的事实即将暴露时,她谎称自己生病,需要离宫休养,实则产下了与其情人的私生子。将怀孕的身体伪装成生病的身体逃离皇宫,尼州反抗了空间权力规训,同时,尼州的私生子中既有儿子也有女儿,这是对生育迷信的回击,由此尼州的母性体验实现了主体化。勃鲁盖尔油画中的道尔·格莱特的母性体验激发了其女性身体的内在潜力,并使其拥有“女版史诗英雄的形象”[17],从而升华了格莱特的母性特质。道尔·格莱特的名字实际上体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母性体验的妖魔化。“道尔”在16世纪有两层含义,一为“疯癫的”,二为“愚蠢的”,而“格莱特”在北欧是“玛格丽特”的变体之一,其作为女性名字也传达出愚蠢的含义[18]。勃鲁盖尔之所以为其画作如此命名,是因为格莱特生有十个孩子,他们纷纷在战争中惨死,格莱特因此拿起武器带领妇女战斗。育有十个孩子在当时的社会看来显得愚昧,而女性的英勇被看作是“疯癫的”,所以格莱特的母性体验是对父权社会传统的反叛。作为母亲的女性总会“为爱和暴力这两种感情热血沸腾”[15],格莱特揭竿而战展现出的暴力正是出于其对孩子的爱,父权社会只接受天使般温柔而服从的女性,格莱特的形象因此被父权社会妖魔化。格莱特史诗英雄般的形象是其母性的升华。因此,格莱特的母性体验是其作为母亲的自我意志和主体性的体现。生活在20世纪的马琳通过将养育责任委托于人,获得了主体化的母性体验。马琳年少时曾陷入意外怀孕的困境,她将孩子生下来交给姐姐抚养,独自离家闯荡。布里福将母性功能界定为怀孕、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15],马琳对其女儿只生而不养不教,没有完成传统意义上的母性功能,她逃离了男性用生育为女性所设的囚牢,选择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成功颠覆了父权社会语境下的母性。
三、结语
《天之娇女》通过女性身体叙事,揭露了父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权力规训,同时也展现了历史上女性不断通过身体反抗规训权力,一步步取得进步的过程。女性身体书写着女性被规训和反抗规训的历史,丘吉尔通过女性身体叙事既书写了被规训女性的悲惨遭遇,也呼吁女性勇于反抗权力规训,表达了她对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
[1] Diamond E.(In)Visible Bodies in Churchill’s Theatre[J].Theatre journal,1988 (2).
[2] 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3]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5] 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 第四辑[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6] 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J].外国文学,2004 (1).
[7]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 Churchill C.Top Girls[M].London:Bloomsbury,2013.
[9] 汪民安.权力[J].外国文学,2002 (2).
[10] Godiwala D.Breaking the Bounds:British Feminist Dramatists Writing in the Mainstream Since 1980[M].New York:Peter Lang,2003.
[11]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12] Sarker S.Gender,Class,and Politics in Caryl Churchill’s Top Girls[D].Dhaka:Brac University,2022.
[13] 苏红军,柏棣.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4] 戴烽.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J].青海社会科学,2007(6).
[15] 里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M].毛路,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6] Yunira S,et al.Re-Visits the grand theory of Geoffrey Leech:Seven types of meaning[J].Journal of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Language,2019 (3).
[17] Sengupta M.Of the Glory and its Price:Re-Reading the Culture/Identity Interface in Caryl Churchill’s Top Girls[J].Journal of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2016 (12).
[18] Sullivan M A.Madness and folly:Peter Bruegel the elder’s Dulle Griet[J].The Art Bulletin,1977(1).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谢清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研究方向为英语小说。
陈 栩,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小说和西方文论。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新时代高校英语文学“课程思政”创新模式研究(SGH23Y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