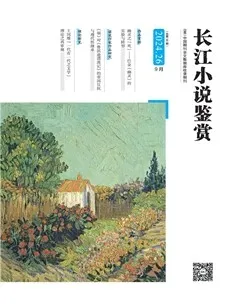浅析《午后曳航》中的“自我对抗”思想
[摘 要]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战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作品以高雅洗练的文笔与独特的唯美主义而闻名。国内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美学思想,所涉及的作品多集中于《金阁寺》《潮骚》《丰饶之海》等代表作。实际上,三岛由纪夫也曾提及陀斯妥耶夫基的相关思想,并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应用于小说创作中,由此形成的“自我对抗”主题,是三岛由纪夫创作生涯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多部作品中都有所涉及,如《禁色》《镜子之家》等。本文将以《午后曳航》为例,具体分析三岛由纪夫在创作中是如何实践这种“自我对抗”主题的,并指出他对此的理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理解上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三岛由纪夫独具特色的“自我对抗”思想。
[关键词] 三岛由纪夫 《午后曳航》 自我对抗
一、引言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战后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创作领域覆盖小说、戏剧等,成就斐然。三岛由纪夫曾论述过,“现代小说的基本命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正是直接表达人类内心的对抗性态度”,以及“让自己内在的矛盾和成为对立物的两个‘我’互相对话”[1]。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们不仅是作者话语的客体,也是自身话语之主体,他们在思想上是权威而独立的,并非作者的传声筒,体现了多样意识之间的平等交流[2]。
三岛由纪夫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启发形成的“自我对抗”思想,是其创作的典型主题之一,在许多小说中都有所体现。但三岛由纪夫所实践的对立的两个“我”之间的互相对话,与巴赫金所阐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多样意识间的平等交流,是否存在差异呢?针对这一点,国内研究很少涉及。
《禁色》《镜子之家》等作品,均是三岛由纪夫“自我对抗”思想的实践。作品内的主要人物多为三岛由纪夫不同矛盾侧面的化身,如《禁色》中的美丽青年与老丑作家、《镜子之家》的四个主人公。斯托克斯曾评价《镜子之家》,指出“四个主人公都暗示了三岛个性中被掩藏起来,而终究在60年代爆发出来的部分”[1]。1960年出版的《午后曳航》,某种意义上来说位于前两部作品的延长线上,这部作品继承了“自我对抗”的主题,但较之前两部,因作者写作阅历的增加而有着更成熟的构思布局。
因此,本文将以《午后曳航》为例,具体分析三岛由纪夫是如何在文本中体现“自我对抗”的主题的,进而参考巴赫金的阐释,通过比较三岛由纪夫所实践的“让自己内在的矛盾和成为对立物的两个‘我’互相对话”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理解和诠释上的差异,揭示三岛由纪夫独具特色的“自我对抗”思想。
二、“曳航”的比喻——龙二与登的同一性
关于《午后曳航》的标题,约翰·内森在其书中有如下注释,该标题“着重于一个无法翻译的同音异义词‘eiko’,日语可写作‘栄光’或‘曳航’,分别表示‘荣誉’和‘拖曳’”[3]。约翰·内森作为该作品英译本的译者,在询问三岛由纪夫的意见后,最终定下“The Sailor Who Fell from Grace with the Sea(失去大海恩宠的水手)”的英文译名。结合英译本译名,从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二副冢崎龙二有关渴望“荣耀”的发言,如“二十岁时的他曾经心潮澎湃地在心中嗫喏:‘荣耀!荣耀!荣耀!我生来就只配得到它!’”[4]以及龙二最终决定放弃航海生涯而被失望的登与伙伴们杀害的结局来看,该标题毫无疑问代指了主人公冢崎龙二。
据日本《大辞林》注解,“曳航”意为“船只用牵索拖曳着其他的船只、货物等航行”。书名“曳航”涉及的喻体为船只,且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前方拖拽的拖轮,二是其后被拖拽的船只。那么龙二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呢?
放学后,在登与其他五名伙伴哄骗龙二去往意图毒杀对方之地的途中,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龙二眼里,作为当今时代的少年,六个人都显得身材矮小。看上去就仿佛是六艘拖轮在拖曳着一艘货船前行,却又不知道怎样曳航才好。”[4]
这段描写,不论时间或是事件,都正好契合标题《午后曳航》的含义。作者在此处将龙二比喻为被拖曳的船只,而包括登在内的少年则是前方拖拽的拖轮。
冢崎龙二与船只的关联是很紧密的。龙二在战后失去了最后的亲人,后作为“洛阳”号的二副常年航行海上。他对陆地抱有负面记忆,从心底渴望在海洋中寻找独属于他的荣耀。但同时他也知道,航行的尽头不存在所谓荣耀,只有日复一日的乏味日常。在矛盾的思绪里,他结识了登的母亲房子,逐渐对陆地有所依恋而决心放弃二副的身份,回归陆地的家庭生活。
黑田登作为少年团中的一员,如前文所述被作者比喻为前方拖曳的拖轮之一。十三岁的登沉迷于轮船知识,向往海洋,而被他视为海洋化身的二副龙二则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眼见龙二跟自己的母亲愈发亲近,甚至打算放弃航海生涯时,如遭背叛的登与伙伴们一起制定计划,最终毒杀了龙二以阻止他的堕落。
由此可见,冢崎龙二与黑田登在小说中的形象化身均为船只。虽然其余伙伴也被比喻作拖船,但纵观整部作品,涉及登与轮船以及大海之间紧密关系的描写占据了绝大部分,且故事情节的主要纠葛在龙二与登之间,因此标题“曳航”的比喻,一方面代指冢崎龙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代指黑田登。龙二与登的形象化身均为船只,他们本质上具有某种同一性。
因此,作品的“自我对抗”就集中体现在龙二与登这两个具有同一性本质的“我”的矛盾冲突上。
三、“汽笛声”——冲突产生的标志
最初龙二与登代表的立场相一致,共同象征着海洋。龙二对海洋深处荣耀的渴求,以及登对龙二的崇拜,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我”的化身还未走向对立面,那自我内在矛盾产生在什么时候呢?
纵观整部作品,着重提到汽笛声的情节大约有三次,每一次都对应了龙二不同阶段的心理。第一处描写,登通过抽屉的孔洞窥视龙二与母亲相遇时龙二的模样。
“突然,从广袤的天空传来了汽笛声。那汽笛声从敞开的窗口蜂拥挤入,溢满微暗的房间。来自大海本身的呐喊声渐渐响彻耳畔。……二副冷峻地转过身躯,把目光投向大海的方向……”[4]
龙二被汽笛声吸引,毫无留恋地转身将目光朝向大海的画面,让登觉得自己“邂逅了一个毫无遗憾的奇迹瞬间”,汽笛声成为“决定性的一笔”,将眼前的一切联系在一起,“他与妈妈,妈妈与男人,男人与大海,大海与登”[4]构成了一个圆环,于是登决心守护这个神圣的链条,不惜做出任何残忍之事。
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登的母亲房子作为与海洋对立的陆地的象征,扮演了引诱龙二回归陆地的角色;二是龙二在面对房子的引诱时,所采取的对陆地毫无留恋的态度。
房子经营着一家洋货店,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着登。她被龙二吸引,是由于对方身上有着一种安全特性,即“他那质朴的心灵不为梦境和幻想所左右”[4]。与充满变化的海洋相比,房子追求的稳定象征着不变的陆地,即海洋的对立面。房子这个外在因素的出现,使得象征海洋的“自我”具备了内部矛盾发生的可能性。但此时,龙二毫无留恋的反应无疑是一种初次对抗的胜利。
汽笛声再次响起,是“洛阳”号即将出港的前一夜,龙二与房子温存时:
“就在这时,从新港码头方向远远地传来了隐隐可闻的汽笛声。……接吻正酣之际,这种想法令他倏然醒来。他认为那汽笛声正在唤醒他体内尚无人通晓的‘大义’。”[4]
此时的龙二沉迷于与房子相处的时光,汽笛声犹如警笛使他“倏然醒来”,又唤起了他心中所追逐的荣耀。此后,意识到即将分离的两人潸然泪下。虽然龙二最终在房子与登的目送之中顺利出港,但较之前,龙二的落泪显示出了态度的转变。
另一方面,作为“自我”内部的另一个“我”的化身,登在纸上写下了对龙二的控诉。这无疑是“我”的自我批判,是“自我”内在矛盾的发展。
汽笛声最后一次响起,龙二已经决定放弃航海生涯了。出海归来后,他向房子求婚,面对是否还会马上上船的半带胁迫性的提问,龙二选择了妥协。
“龙二那忐忑不安的眼睛,已经不能直视辉煌渐增的太阳。汽笛声响彻云霄……‘不马上上船。或者说,已经……’龙二欲言又止。”[4]
似乎是与此对应,文本后续再无鸣响汽笛声的情节。被三岛由纪夫首肯的英译本译名,在此得到印证。龙二背离了大海,“自我”的内部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龙二与登这两个“我”的化身走向彻底的对立。为了重新回归“自我”的统一,消解“自我对抗”的局面,只有通过特定的方式。
四、“猫”——自我对抗的消解
在少年团头领的带领下,登杀死了一只仔猫。
杀死仔猫的行为,为登提供了一条途径,即认识到通过特定的手段,可以让生命摆脱表象,回归纯粹,重新获得连接感。
小说结尾处,登与伙伴们哄骗龙二喝下了放有大量安眠药的红茶。根据此前商量行动计划时头领的发言:“要领嘛,以前我们已经拿猫练习过了。一样的。”[4]以及带着龙二前往目的地时,头领与龙二的对话:“‘我们在这里对那些破旧的船只进行修理,或者解体后重新修造。’‘是吗?把船拖到这种地方来很不容易呀!’‘很简单。轻而易举!’”[4]由此得知,杀死仔猫的步骤暗示了龙二被杀害的过程。
如前文所述,龙二被房子吸引而背弃大海,自此他与登这两个“我”的化身逐步走向彻底的对立。为了消解“自我对抗”的局面,登决定通过杀死龙二的方式阻止其堕落,让龙二的生命回归纯粹,并重新在这两个“我”之间建立连接感,回归统一的“自我”。
五、龙二的结局——“我”的自杀
龙二的结局是一场谋杀,也是“自我”内部出现矛盾对立时,“我”的自杀。龙二与登是具有同一性本质“自我”的两个化身,起初立场一致,随后由于外部因素(房子)的干扰,出现对立,为了消除这种矛盾,作为登的“我”杀死了作为龙二的“我”,使“自我”回归统一。令人深思的是,走到如此结局:龙二背离大海,登杀害龙二,真的是迫于外在因素影响下的无奈之举吗?还是说,这本就是“自我”主动追求的结果?
登在第一次偷窥龙二与母亲时,龙二被汽笛声吸引转过身面向大海,登在震撼之余,脑海形成了一个神圣的链条,即“他与妈妈,妈妈与男人,男人与大海,大海与登”连接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之环”[4]。
为什么房子作为海洋对立面的陆地的象征,作为一个外在干扰因素,能够被纳入这个所谓神圣的链条之中呢?或者说,这个圆环之所以能达到神圣,正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房子这个干扰因素。
龙二与房子交谈时,一段内心独白提到了他脑海中理想的爱的形式,即“与人生中只可邂逅一次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理想女人之间,必定会有死亡介入其间”[4]。此外,他也曾提到过:“在梦幻里,荣耀、死亡和女人总是三位一体。”[4]不约而同,登与龙二各自有关神圣的幻想中,都包含着女人的身影。
房子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结合登的幻想以及龙二所渴望的爱的形式,我们可以整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因为有女人充当干扰因素,才有滑向堕落的可能,此时死亡介入,才会使堕落重新转化为真正的纯粹,即有堕落的存在,与之对立的荣耀才得以存在、能被获得。
龙二常年在海上航行追寻所谓的荣耀,甚至于到了有些厌倦懈怠的地步,得到的结果却是“他渴望暴风骤雨,然而船上的生活,却只不过告诉了他井然有序的自然法则和摇摆不定的世界的复原力而已”[4]。但当他在结尾喝下放了大量安眠药的红茶,感觉苦不堪言时,脑中瞬间想到的却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荣耀的味道是苦的”[4]。放弃航海准备走入婚姻的他,在死亡降临时,却尝到了苦求不得的荣耀的味道。这种为了寻求荣耀,潜意识里主动去创造对立条件的逻辑链条,其中无可置疑地存在着一种极其讽刺的意味。
由此可知,三岛由纪夫宣称的所谓现代小说应当“直接表达人类内心的对抗性态度”,“让自己内在的矛盾和成为对立物的两个‘我’互相对话”的“自我对抗”主题带有极强的个人特征,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让不同的矛盾思想化作小说人物,进行平等对话。归根结底,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作者本人的传声筒,自导自演了一场内在矛盾的“戏剧”,只是为了在跨越刻意制造的困难之后,能沉醉于心中幻想出来的荣耀里面而已。
六、结语
三岛由纪夫笔下的“自我对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性有着本质差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体,他们不受作者支配,彼此间是不相混合的平等关系。而三岛由纪夫的矛盾自我,都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意识,甚至于所谓的“矛盾”都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戏剧。刻意追求矛盾的原因,是为了让幻想中“荣耀”的实现更具困难性、波折性,以满足自我陶醉式的感动。
三岛由纪夫笔下的“自我对抗”主题,在多部作品中均有涉及,本文只以《午后曳航》为例进行了分析,今后的研究将着眼于作家其他作品中有关该主题的表现,以丰富完善三岛由纪夫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斯托克斯.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传[M].于是,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2]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3] 内森.三岛由纪夫传[M].常永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4] 三岛由纪夫.午后曳航[M].帅松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罗 芳)
作者简介:周童欣,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