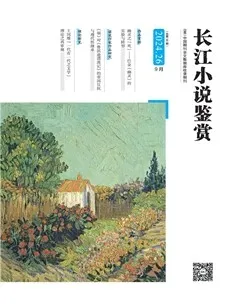幽灵之“死”
[摘 要] 《幽灵》是巴金短篇小说中一个较为独特的文本。“死亡”是巴金持续关注的话题,从革命浪漫主义的单纯幻想到理想破灭后的思想沉淀,早期的巴金试图在其中创造一种超越性视角,用这唯一一部以幽灵作为主角的作品,延续自己对这一终极问题的思考。小说将戏剧反讽与作家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结合,构建了两个生者与死者相互隔离的空间,一方面折射出小市民真实痛苦的生活体验,揭露了死亡的矛盾和虚幻;另一方面,幽灵的旁观者视点既增强了客观性,又不失人性关怀的光辉。通过这种介于奇幻与现实之间的书写实验,巴金逐渐摆脱了早期的创作缺陷,从对青春激情和理想主义的呼唤转向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入探究。这不仅显示着他在时代转折中的思想复杂性,也是他的创作经由一系列探索后,从情感呼号转向文学性叙事的一种预兆。
[关键词] 巴金 《幽灵》 短篇小说 创作转型
“像斯芬克司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1]“死亡”是巴金小说中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线索,但以人死后的幽灵作为主角的,只有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的短篇小说《幽灵》。巴金在创作早期钟爱革命与牺牲主题,而《幽灵》却一反常态,通过一个小公务员惨死在车轮下,复活成为幽灵回到家中,得知妻儿因为自己的死亡陷入贫困、受人欺压,自己却无能为力,只能默默离开的故事,揭露了“死亡”的残酷真相。相较于其中长篇小说来说,巴金的短篇小说一向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幽灵》这类作品往往被简单地纳入“小人物”书写或笼统的社会批判的范围被讨论。然而深入考察这一风格迥异的作品,会发现它在巴金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中实际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它是作者在时代转折中思想矛盾的真情流露,另一方面,《幽灵》在此基础上又抛弃了单纯的情感呼号,通过大胆的文体形式实验,体现出对文学叙事本身的重视。这不仅展现了作家对“死亡”的全新思考,对其创作转型更是有着重要作用。
一、死亡的矛盾与探索
鲁迅的《野草》中描写人死后情形的篇目《死后》中写:“假使一个人的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那就比全死了更可怕。”[2]巴金在20世纪20年代就熟读了鲁迅的作品,这句话或许正是《幽灵》这篇小说的灵感来源。表面上看,《幽灵》与《光明》中的《狗》一样,是一个以奇幻笔法透视下层社会现实的文本。小说中,一个因车祸意外死亡的小公务员作为幽灵复活了。离奇的是,他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的事实,而是继续以活人的方式在世间行走、观察,并目睹了马路上呻吟流血的人头、电车中拥挤冷漠的人群等种种怪异的景象,直到回到家中发现妻儿对自己也视若无睹,他们受到房东太太的侮辱,自己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做出牺牲,这才终于确证了自己的死亡。比起幽灵对世间悲惨景象的回望和批判,小说更像是借着死者之口,对“死亡”这一事实带来的后果进行直观展现。
不过,与鲁迅常用荒诞手法影射现实的创作方式不同,巴金并非一个长于使用现代主义式象征的作家。《幽灵》之所以会采用这样介于奇幻和现实之间的书写方式,与其长期以来对“死亡”的思考和探索有关。
“死亡”是巴金作品中的永恒话题。巴金从幼时起就目睹无数亲友在困顿和痛苦中死亡,敬爱的大哥在1931年自杀,曾给他极大的精神打击,加之自己也曾饱受疾病困扰,他深知死亡的残酷性。然而由于青年对世界抱有极大热情,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对死亡的描写常常显示出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关于死后重生的美丽想象。“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新生,那时这个‘我’渗透了全宇宙和其他的一切东西。”[4]《灭亡》中的杜大心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毅然决然以自己的生命向不合理的制度发出了挑战。他的死虽然是一种以卵击石的行为,但也深深地鼓舞了《新生》中李冷这样的后来者,将他的精神永远传递下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1]这种想象内化为一种与革命、光明和希望紧紧相连的信仰,不仅鼓舞了《死去的太阳》中的革命者,也激励了《海底梦》《还乡》中普通的民众,他们坚信死后的自己会以更强大的方式在生者的精神中“复生”。
巴金钟爱塑造这类殉道者的形象,并认为他们“崇高的人格,血和泪结晶的心情,谁也不能不承认是人间最优美的”[4]。这种想象毕竟是在强烈的激情和特定的信仰中形成的,一旦回到现实,就连他也无法否认其中固有的矛盾性:个人英雄主义的力量始终难以与整个社会的顽疾抗衡,在实现理想的现实道路上,这样的牺牲无异于螳臂当车,死者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无能为力。在小说的文本内部,这种矛盾性不断通过情节的设置和情感的冲突浮现出来,人物牺牲前勇猛和畏缩交织的矛盾心理的爆发往往成为小说的高潮,而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失败的,是一种有力的讽刺和针砭。这一矛盾来源于他青年时期对革命形势认识的欠缺,同样也来源于热血和理想与乐生恶死的现实经验之间产生的必然冲突。在杜大心腐烂的头颅面前,死亡的神秘和恐惧依然持续困扰着他。“我有时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毕竟太美丽了。……我想到‘死’的时候,从没有联想到这一个死法。”[1]
“人死后究竟怎样?”这是巴金的创作生涯中无法逃避的一个话题。在充满热血和理想的青年时代,他用激情压抑了对死亡的恐惧,然而在激情消散之后,这种想象的虚幻和苍白会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出来。大革命失败后,巴金的革命事业理想几近破灭,这让巴金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当中。而巴金改造旧社会、改造旧制度的“叛逆精神”在诞生之初就“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交织在一起”[5],在这种“内心矛盾的挣扎、痛苦的战斗呐喊和不可克服的忧郁性”[6]并存的状态下,他不满足于空洞的理想呼号,而是要深入生活的每一方面,以检验自己理想的意义。
《煤坑》等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中,巴金用相当一部分篇幅描写了矿工的反抗行动,矿工以自杀换取抚恤金的行为,初步展现出他对死亡的灾难性认识。《幽灵》的书写方式则更为直接,作者再次将目光聚焦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并不得不创造性地通过“一个死去的人回来告诉我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1]的方式,将对死亡的探索直观而又残酷地延续下去:当新生的幽灵回到人群中时,它们面临的不是光明和希望的永存,而是一个自己的力量完全无法穿透的世界。“人死了还会回来”在这里变成了哄骗孩子的话,“我还站在这里,我的心还知道爱人”[7]。虽能证明“我”对家人的真挚情感,却也如同“我”对生的幻想一样,只是一种痴狂和执念,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灵魂永存对没有宗教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只是一种安慰剂,有时甚至因为太过夸大而让读者产生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态度[8]。当脱离了理想主义的语境,这种信仰的“谎言”就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方式被揭穿了:既不能以“保佑”的方式免除生者的痛苦,又不能以“转世”的方式加强生者的力量,甚至连存在记忆中都会增加生者的负担。因此“我”在知道自己对妻儿的悲剧无能为力后,最终选择了默默离开,“不要妨害他人的幸福”[8]。
二、幽灵的反讽与旁观
为了完成对死亡的深入探索,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让幽灵处在一个生与死之间的叠加状态。他必须具有活人的感官和思想,才能将死后世界的样子完整地传达出来;但也必须丧失活人的形体和行动能力,以维持他人眼中死亡的状态。这让小说中的主角不得不处在一个戏剧反讽式的荒谬处境,为小说增添了复杂性。
小说一开头,主角就用一种平静而矛盾的口吻否认着死亡这一事实的存在。“我从地上爬了起来,没有一点创痛。我记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在地上躺了许久。”[7]“我”无伤无痛,能自主运动和感知外界,甚至能看到马路上冲过来的汽车,还能“敏捷地躲开”,这明显不是一个死者的反应。“我”又冷又饿,想要回家,这样平常的生理和心理欲望压倒了一切,导致“我”把马路中央有人在舔舐血迹、没有一个行人与自己相撞这样活人不该遇见的异象也忽略了。相比1933年发表的版本,巴金后来在修改《幽灵》时还在开头加上了“我仿佛记得先前是给一辆汽车撞倒了的”[9]一语,这说明他认识到这里的表述是含混的,“我”无法通过这些模糊的迹象确认自己的死亡,而与透过小说标题就得知了全部真相的读者相比,这是一种有意营造的无知,以至于“我”的存在本身就带有了戏剧反讽的意味。
《牛津文学术语词典》将反讽定义为:“观众比剧中人更了解剧中人的处境,其预见的结果与剧中人所期望的结果形成对照。”[10]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知晓主角是一个死者,而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却聚焦在“我”如何在生与死的认识之间挣扎,与这种无知作斗争。直到从妻子与儿子的对话中得知了自己已经死亡的消息,“我”依然感到难以置信,并不断地喊话、拥抱、触碰,试图向妻儿表明自己的存在,当“我”察觉自己无法安慰悲伤的家人时,才第一次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我不能够给她帮一点忙。我这样抚慰她,她一点也不觉得。原来我死了。我尽力答应她的呼唤,她却丝毫也听不见。”[7]房东太太上楼来当面辱骂“我”是一个穷死鬼,要妻子去出卖自己时,“我”既心痛又愤怒,用力叫骂,然而既不能赶走侮辱妻儿的房东,也不能拿到生存必需的钱财,连让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去都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做出牺牲。直到这时,“我”的希望才完全毁灭了,通过这种深刻的无力感,“我”完全确认了自己的死亡,“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我的地方了”[7]。
不难看出,这一悲剧的核心是死者与生者之间的隔膜。通过幽灵这一媒介,本可以达成一种对死亡的超越,但“我”的痛苦正是来自这种在生死之间的徘徊,来自死者对生的无能和渴望。“我”虽然已经死去,但并未忘记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向往着温暖的家庭生活,同情着道路上无助的冤魂,面对黑暗的现实悲愤交加却又无能为力,这些描写都基于现实,是生者对死者普遍的希望和认识,介入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因为认知差异导致的戏剧反讽效果,又让读者被迫从小说的情境中抽离出来,死者和生者之间天然的隔膜让读者的视角在“我”和其他生者之间游移,从代入自身的认同转变为带有旁观意味的审视。当读者随着“我”在街道上奔走,看“我”呼唤妻儿,感受到的是小人物面对压抑冷漠的社会环境时的无力,而当“我”已死亡的事实从妻子的口中说出时,幽灵虚幻的在场又与家人对死者没有结果的期盼形成对比,读者站在生者的角度等待奇迹的出现,然而即使到了小说的最后,“我”都没能回到家人的眼前,只能默默地离开。这一从探求最终回到迷茫和虚无的举动,既能够引起同情,又在一种更高的观察层面上显示出荒谬与悲哀。
这个形象鲜明地体现出作家在转型期进行形式实验的痕迹。与巴金的大部分短篇小说一样,《幽灵》采用的是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巴金曾解释过自己频繁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一是便于倾吐和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11]二是一种扬长避短的艺术手段:“因为自己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12]因此,他短篇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大致呈现出两种效果,一是将作者的自我意志和情感投射在小说人物的身上,自述热情洋溢的“我”的故事,以早期的《复仇》为代表;二是利用“我”讲述他人故事的方式,拉大叙述者与事件的距离,呈现出一种相对冷淡疏离的态度,以后期的《小人小事》为代表。而《幽灵》恰巧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文本,一方面,“我”作为限知叙述者,小说中所有的事件和场景都是通过“我”的叙述呈现出来的。“我”保留着活人的情感和记忆,并不断地试图介入活人的生活,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与生者处于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中;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叙述中的主要事件都排斥“我”的进入,无论是对路边痛苦的魂魄、冷漠的人群,还是家中妻儿的孤独、迫在眉睫的贫困,“我”都有心无力。不同于早期《复仇》《狮子》中那样积极的行动主体,也不同于后期《兄与弟》《憩园》中,人物那样若即若离的冷静旁观者,《幽灵》中,人物探求的热情被现实的冷酷逐渐冲淡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死亡、生命及生活之意义的别样反思。
三、转型中的文学重建
从某种程度上看,幽灵的处境也是巴金在创作转型期对自己社会角色的一种期待。尽管一再申辩自己并非专业的文学家,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由于《灭亡》和《激流》在青年读者群中的极大影响力,巴金作为“五卅之后最主要的作家之一”[13]的文化身份得到了公认。1931年后的两三年间,他的创作数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除了要每日连载的长篇小说《激流》,他还交替进行着《爱情三部曲》的写作,接连不断地写了数十个短篇,然而正如陈思和所言,巴金走的是“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的文学道路”,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文学创作实际上是在弥补他在革命事业中的无能为力,他一面发挥着这种“积极的战斗性”[6],在文学作品中倾吐自己的情感,企图用自己的热情感染读者,一面又由于自身政治信仰的尴尬处境,在实际斗争中被迫“缺位”,因此对自己消耗在“这些无用文字上”的生命产生怀疑,甚至经常出现自暴自弃的消极心理。“说那纸笔当为武器来攻击我所恨的,保护我所爱的人,而结果我所恨的依然高踞在那些巍峨的宫殿里,我的笔一点也不能够动摇他们,至于我所爱的,从我这里他们也只能得到更多的不幸,这样我就完全浪费了我的生命。”[6]
接踵而至的,是大量针对他作品的流言和指责。尽管其中夹杂着许多粗暴的政治攻击,巴金也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对其进行回应。胡风、施蛰存等人指出其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缺陷,局限于对理想和教条的描写,而对真正的社会现实“缺乏独到的体验与观察”[14],他大致是同意这些批评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艺术上不成熟、但里面却充满着我的热情的作品”[1]的发表其实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其“倾吐情感”的个人要求。在回应施蛰存对《复仇》的批评时,巴金提到自己这段时间的“多产”是各界友人向他约稿而他不忍回绝之故,《幽灵》最初发表于1933年创办的《新中华》创刊号,这是一本背靠上海中华书局、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巴金的作品仅在该刊上发表过一次,可见这也是一篇为《新中华》创刊号“造势”之用的约稿文章。在如此高强度的写作中,巴金要满足热情的编者和读者、与自己矛盾痛苦的心境作斗争,仅靠灵感和一腔热情的写作方式是不足够的,当众多批评家指出他的瓶颈时,他自然也需要摆脱早期的创作缺陷,通过不断的探索实现自我突破。
巴金为了改进自己的创作方式,不断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寻求革新,写作简便灵活的短篇小说就成了其突破自我的最佳形式,这使得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呈现出与《家》《海底梦》等同时期中长篇的“激流”式作品截然不同的丰富面貌。这一时期写作的短篇小说大多被收入《光明》《将军》《沉默》等小说集中,除了继续创作早年已经得心应手的革命者形象和外国人物故事外,小说的描写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还乡》《煤坑》涉及底层工农生活;《杨嫂》《母亲》以自己的童年回忆为蓝本表现劳动女性的爱与痛苦;《父与子》揭示亲子关系的复杂性;《电话》用少见的速写风格体现出对知识阶级的讽刺。在捕捉这些多样的生活横断面时,巴金采用的叙事手法不再是单一的个人经验纪实和心理描写,也逸出了一般研究者所认为的“第一人称”与“书信体”的惯例[15],虽然大多数尝试都是昙花一现,但也体现出了巴金在这一时期在个人思想的矛盾和外部环境“高压”下迸发出的思维活跃性。
《幽灵》作为其中突出的一例,用奇幻的幽灵来透视死亡的现实真相,作者的笔触游离于生与死、虚幻与现实之间,不仅对底层人民的如幽灵一般渺小痛苦的生存境遇发出了控诉,也作为巴金思想转变的重要一环,揭露了革命理想主义话语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作家开始将自己的角色从小说中抽离出来,通过一种想象性的情景创造了一个更高的叙述角度,不再处处将自己的悲欢爱憎乃至心中的种种矛盾和斗争都完全投射在小说人物“我”的身上,也不再时刻呼唤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三位一体的认同,而是注意到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展现这一复杂性。与之相似的《狗》同样以非人的荒诞视角显示出冷酷社会中个体的生命力量;《五十多个》通过群像和速写式的描写刻画出民众的痛苦与坚忍;《将军》将他擅长的域外人物书写与中国社会观察结合,从而在其被编入《草鞋脚》时,被评价为终于摆脱了浮泛的“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16]。这些对生活剖面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描写,不仅得益于巴金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沉淀和转向,也与他持续不断的艺术探索息息相关。通过对真实个体生存状态的深入观察,作家的笔调由粗疏趋向细腻,由批判和控诉转向冷静的审视和重估,这一创作转向逐渐在《小人小事》等小说集中显示出来,并在后期的《憩园》《寒夜》等作品中臻于成熟。
四、结语
在讨论巴金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创作转型时,常被研究者关注的是其思想上的沉淀和转向,这不仅因为巴金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特例,他的“另一条道路”始终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性,或许还因为巴金一再表示自己“不是作家”,称自己为文坛的“闯入者”,以及强调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从而导致他在小说技术上做出的探索和努力常常隐蔽于思想的“激流”之后。然而,在作家的成长历程中,思想的变化与艺术形式的更新总是两条不断纠缠的线索,作家写作艺术日渐成熟的过程中也并不仅仅只有思想转向的参与。青年时期的巴金对革命的强烈热情和对人道主义的推崇,促使他在文学中走上了青春赞歌和社会革命的道路,从这个角度上看,《幽灵》确实再次参与了他以小人物为中心对黑暗现实做出的批判。不过,小说叙事形式上的更新容纳了更多曲折和裂隙,不仅使他幽微的思考和生命体验得以表达,也参与了作家从夸大空泛的“公式化”描写走向“现实人生气息和形象饱满的风采”[5]的漫长探索历程。从中不仅可以透视巴金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关怀,对“人对于人是至高的存在”[3]的坚持,也能重新发现其思想和艺术轨迹的深度与广度。
参考文献
[1] 巴金.死[J].丛,1937(1—4).
[2]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巴金.巴金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4] 芾甘.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覆同志的一封信[J].民钟,1927(6—7).
[5] 艾晓明.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6] 陈思和,李辉.论巴金的文艺思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4).
[7] 巴金.幽灵[J].新中华,1933(1).
[8] 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兼论近日小说的特性与价值[J].国闻周报,1936(11).
[9] 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0] Baldick C.牛津文学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1] 巴金.作者的自剖[J].现代,1932(1—6).
[12] 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J].人民文学,1958(6).
[13] 李奎德.现代中国文坛鸟瞰[J].细流,1934(3).
[14] 施蛰存.复仇[J].现代(上海1932),1932(1—6).
[15] 袁振声.试论巴金的短篇小说[J].天津师大学报,1984(4).
[16] 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 “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特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刘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