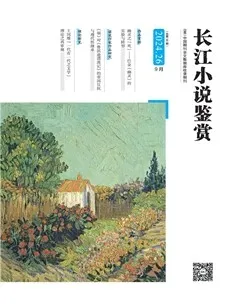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界限消失”:逃逸与生成中的那不勒斯人物图景
[摘 要] “界限消失”是“那不勒斯四部曲”中莉拉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费兰特整部小说遍布着边界的书写与人物跨越边界的行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同样提出了有关边界的产生与边界消失的几个“线”的概念:克分子线切分出边界,构建出辖域;分子线则在边界上进行相对解辖域运动;逃逸线则是绝对的解辖域化运动,它打破能指的白墙,冲破主体性的黑洞,携带着破坏性的能量生成全新的意义。生成具有多元性,是一种居间性,根茎也是一种生成,根茎是一种“反-谱系”的哲学,它是一种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的多元体,作品即一个根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作品批评视角。
[关键词] “那不勒斯四部曲” 德勒兹 根茎 逃逸线 生成
一、作为根茎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根茎理论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导论里阐述的概念,即千高原中的第一座高原。根茎理论在辩证法和主客体的二元对立模式之外强调一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不寻求统一与永恒,而是强调多元性的根茎特点。符号链作为根茎,有着连接性的原则,并在此之中是异质的:“在根茎之中,任意点之间皆可连接,而且应该被连接。”[1]各类特征的符号链能够与各种复杂的编码方式(如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结合,从而触发各种不同的符号机制和事物状态。在这个符号链之中凝聚着语言的、知觉的、模仿的等行为,德勒兹否认语言自身的存在,而强调言语的集聚[1]。根茎是一个多元体(multiplicité),它不具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多元体由抽象线、逃逸线或解域所界定,它们在与其他多元体建立连接时不断改变着自身性质,因而根茎是一种生成(devenir),它永远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作为根茎,文本世界与真实世界并未形成二元对立,两者具有差异性和相似性,文本位于根茎中朝向不同的方向生成意义,将根茎转化为根和胚根。作者埃莱娜·费兰特隐藏自己的个人信息,从不公开露面宣传自己的作品,当众人纷纷质疑她是否真的存在时,她回复自己并没有隐藏自己,也没有制造什么神秘感,而是存在于小说里。读者可以找到作者的唯一空间是在作品之中[2]。小说的女主人公之一的“我”是埃莱娜·格雷科,故事发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城区,且以回忆的姿态进行叙事,读者下意识认为书中的埃莱娜和作者埃莱娜是同一个人,作者是在叙述真实发生的故事,增加了文本真实,文本世界与真实世界反而由于无法二元分化达到了高度的同一性。
在根茎中,任意两点可进行连接而且应该被连接。“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本世界与真实世界任意两点之间可进行连接,但同时文本世界与真实世界又是异质的,语言的符号链亦可与当时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等进行连接,如堂·阿奇勒与高利贷的牟利模式进行连接,帕斯卡莱形象与他父亲被捕进行连接,索拉拉兄弟与资本主义进行连接。文本世界形成了一个机器性配置,由表述的集体性配置直接运作。文本世界之内,任意两点也可进行连接,埃莱娜的行动与莉拉的言语连接生成一个新的行动。《我的天才女友》中,当埃莱娜由于身体发育而遭受男孩们的嘲笑与骚扰时,埃莱娜与莉拉的形象进行了连接,她恶狠狠地对吉诺的打赌进行了回应,用莉拉的方式在骚扰中赚了十里拉。莉拉的行动同样与埃莱娜的行动进行连接,后来《新名字的故事》中,莉拉告诉埃莱娜,她再也无法画出新的鞋子设计图,因为几年前,她能在鞋匠铺子里画出鞋子设计图都是因为埃莱娜,除了两位女主人公的连接外,城区的暴力事件、男人与女人的失控、死亡等种种事件都能够任意在根茎中与主人公之间进行连接。
小说中的故事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它作为根茎、一个多元体,同时可与读者、作者等其他多元体进行连接,作品在与作者或不同的读者即不同的多元体进行连接时会不断改变自身性质,多元体在不同的逃逸线作用下经过解域再建域后生成不同的意义。“那不勒斯四部曲”在不同的文学批评中不断生成着全新的意义,如女性身份认同、读者接受研究、叙事研究等。
二、界限消失:逃逸线的显现
“界限消失”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指一种事物会打破原来的界限,改变形状[3]。莉拉第一次感到界限消失所带来的周遭世界的陌生感是在旧城区的跨年夜,几家人一起在斯特凡诺家里的天台上与索拉拉兄弟比赛放烟火时,烟火对阵中,处于弱势中的索拉拉兄弟朝他们开枪,莉拉的哥哥里诺愤怒地嘶吼大叫,那时莉拉感受到了界限消失:“她看到里诺在移动,他周围扩散开来的物质也在移动,他身体的界限在消失。她自己身体的界限也越来越柔软、易碎。” [3]
如果说莉拉所经历的第一次界限消失是人的界限溶解于环境中,被情绪支配着的人显露出丑陋面容,那么第二次界限消失则是世界边界的消失。莉拉和莱农(埃莱娜)怀孕期间,地震使原本坚实的地面晃动裂开,马尔切洛开车从她们身旁驶过,她感到车的界限在消失,那些熟悉的事物和人都在往外喷东西,金属和人的血肉搅成一团,这并非意识流的写法,也不是荒诞叙事,对莉拉而言,人和东西的界限很脆弱,会像棉线一样容易断裂,而且那些东西的边缘会发生剧烈而痛苦的变形。
人和东西之间的界限会断裂消失,这两次界限消失亦可被称为解辖域化运动,莉拉敏感地捕捉到了分子之间的相互运动,克分子线和分子线被引爆后,逃逸线清晰地显现在了莉拉的眼前,逃逸线是绝对的解辖域运动,它能打破能指的白墙,冲破主体性的黑洞,具有前所未有的能量和创造性。但逃逸线也可能是危险有害的,从莉拉的叙述中读者可知它带来的恐惧、虚无与绝望已经深刻影响到了莉拉。
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阐述了三种线:克分子线(molar line)、分子线(molecular line)和逃逸线(Lines of flight)。克分子线是稳定的辖域化运动,以二元对立或权力机制切分出界域。分子线是相对的解辖域化运动,以分子为单位进行抵抗克分子线的僵化辖域。逃逸线是绝对的解辖域化运动,引爆克分子线与分子线后,逃逸线冲向无限可能的域外。三条线相互诠释,有着内在的交互性,正如德勒兹无法将它们分离:“三条线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交互性,我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将它们分离开来。”[1]
在那不勒斯,任何身份都是界限分明的,那不勒斯与外界、儿童与成人、丈夫与妻子、男人与女人、庶民与上层阶级,空间、性别与阶级像被一条线生硬地切开,相应身份的人物仅在自己所属的辖域中活动。这条固定切分线就叫作克分子线(molarline),又被称为坚硬线,克分子线规定着界域与编码,以二元对立的机制划分出男人/女人、儿童/成人、青年/老年、自我/他者等,克分子划分下的辖域是稳定而同质的,一片辖域之中人们具有同质性的价值、道德、宗教等,这样的世界具有稳定性,但同时阻碍了多元化的生成,“这种二元机制阻碍了多元化的世界”[4]。在旧城区,女性就应当承担生育和家务之责,任何如多纳托·萨拉托雷般帮助自己妻子减轻负担而去买东西,用小车推孩子出去散步的男人则被视作想要做女人的男人;儿童理应服从于成人,他们的父母可对其进行肆意打骂,决定他们能否继续上学;女孩由儿童走向成年的克分子之线是经血,由此女孩们变为成人,开始受到男孩们的骚扰;在家庭的克分子线的切割下,莉拉和埃莱娜走向不同的命运,莉拉留在鞋铺,埃莱娜能够继续在学校读书,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分明。
分子线又名柔顺的节段化之线、破裂线,分子作为最小单位产生崩溃,在这条线上进行一种相对性的解辖域化运动。解辖域化运动即一种边界的消解运动,分子线以解辖域化的方式不断冲撞克分子线切分出的世界,两条线不停地相互干扰、相互作用,彼此将一股柔顺之流或一个僵化之点引入到对方之中[1]。最初的解辖域化运动是埃莱娜和莉拉小时候相约逃课去看海的过程,在路途中,两人身上皆发生了解辖域化运动,空间由旧城区的辖域扩展至其外。小学毕业考试补习时,奥利维耶罗老师问埃莱娜知不知道什么是庶民,终于在中学时莉拉婚礼上的众生相令她更加清楚地明白了什么是庶民,她们自己就是庶民。教育就是一条分子线,受教育的过程就是解辖域运动,解辖域过程中埃莱娜终于意识到了被克分子之线切分出的阶层差异,旧城区的人与学校里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差距同时也是埃莱娜和莉拉的分子线,是莉拉的另一种可能人生,因而当埃莱娜在时,莉拉能够不被固定在一片身份辖域之中,尽管这条线并不稳定,莉拉还是会时常被自己的身份辖域拉回。如果说埃莱娜是处于分子线上对莉拉进行相对的解辖域化运动,那么与尼诺之间爱的激情则是一条逃逸线,对莉拉进行着绝对的解辖域化。
尼诺作为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两段高潮情节中二人与之均有一个逃逸的动作,莉拉和埃莱娜被困于不幸的婚姻时,婚姻作为一条克分子线对之进行了辖域化,尽管二者的分子线都促使其不断反抗着这种辖域化,但这种反抗是相对的,与尼诺之间爱的激情成为一条绝对解辖域化运动的逃逸线。逃逸线又被称为抽象线、创造线,是生成的关键,它完全摆脱克分子线和分子线,避开二元组织,抹去任何断片或辖域,摆脱编码,追求完全的解放与自由[5]。绝对的解辖域化运动是两条线引爆后在逃逸线上发生的,这并不意味着逃逸线存在于克分子线与分子线之后,相反,作为一条原初的线,逃逸线一开始就存在于多元体中。逃逸线破除规矩、打破惯例,力图使生命逃脱社会的压制,朝向不同的方向生成。尼诺的出场给了处于婚姻的辖域中的两个女人以生命的不同方向的可能性,他肯定莉拉和埃莱娜的才华,鼓励她们继续读书、创作、发表自己的作品,因而在对尼诺爱的激情中,莉拉和埃莱娜的逃逸线上发生了绝对的解辖域化运动。但逃逸线也是最危险的一条线,逃逸线上存在着解辖域化失败的可能性,也很有可能在一个陷阱之中落入另一个陷阱,再次被克分子线切割。莉拉和埃莱娜在经历婚姻的解辖域后,很快和尼诺的爱也迎来了逃逸线上的解辖域化运动,有所不同的是,莉拉所处逃逸线上的解辖域过程迅速而剧烈,因而再建域后的一切皆易于崩坍;埃莱娜与尼诺间逃逸线上的解域化运动是缓慢的,再建域过程是坚实而牢固的。
三、布娃娃的隐喻:生成-女人
玩具娃娃的消失与出现成为线索贯穿在莉拉与埃莱娜的友情中,两人的友情开始于地下室历险,娃娃被丢到地下室后,二人携手敲响了堂·阿奇勒家的门,两人的分子线介入了彼此的生命,在小说的结尾,历经半个世纪后,二人童年时期丢失的娃娃被邮递到了埃莱娜家门前的信箱里,埃莱娜决定放弃寻找消失了的莉拉[6]。“莉拉已然清楚地浮现在作品中”,莉拉尽管在现实中仍旧下落不明,但作为多元体的莉拉已经清晰地生成在埃莱娜的作品中。
生成是逃逸线后的分子性超越,分子性的生成意味主体、客体及其形式的消解,作为对二元机制的摧毁,生成总是在中间,具有一种居间性,它是一种永远不断增殖的多元性。德勒兹与加塔利主要论述的几个概念为“生成-女人”“生成-动物”与“生成-不可感知”,女人、动物或分子永远拥有一种逃逸成分,并由此趋避了自己的形式化[7]。埃莱娜·费兰特在书写女性困境时,女性身上的逃逸线接连显现,在作品中也不断进行着“生成-女人”。
除了女性中的“生成-女人”外,作品中另外一位男性人物也在“生成-女人”。作为同性恋的阿方索在莉拉的帮助下确认了自己的性取向,并不断模仿着莉拉,他身上的男性气质不断减退,最后与莉拉相似的女性气质占据了他的身体。莉拉用布娃娃形容阿方索身上的变化:“把他缝在一起的棉线正要裂开 。”[6]在莉拉的叙述中,人成为布娃娃的形式,由线头缝起来的边界将内部材料包裹住,而阿方索的变化则是边界的破裂,同性恋是材料与材料的混合,这是“生成-女人”的具象表达,莉拉发觉了阿方索身上的逃逸成分,激发了其逃逸线,经过“解域-再建域”的过程后,阿方索完成了“生成-女人”。尽管阿方索受莉拉影响而模仿莉拉,但生成本质上并不是模仿、类比或等同,生成是相互的。德勒兹举了自然界中的兰花与黄蜂的例子:在同一时刻,黄蜂成为兰花繁殖系统的一部分,兰花也成为黄蜂的性器官,因而存在着兰花的“黄蜂-生成”和一种黄蜂的“兰花-生成”的双重生成[1]。同理,在“生成-阿方索”与“生成-莉拉”之间也是一种双重生成,同时,莉拉作为一个多元体,在生成时不仅与阿方索相互生成,还与埃莱娜之间发生双重生成,并在最终的作品中完成多元体的生成。
四、结语
作为根茎的“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出现的一系列符号链连接起那不勒斯的真实图景与小说中的那不勒斯生活状态,故事在根茎之中朝向不同的方向生成,小说整体是可以从多角度解读的多元体。在费兰特笔下,德勒兹和加塔利阐述的克分子线、分子线以及逃逸线都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克分子线下划分出的城区与外界、男人与女人、成人与儿童的界限分明,带着对个人生活轨迹的明确划分与规训,使世界秩序稳定而至僵化;分子线则不断冲撞着僵化的辖域与空间,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与生机,但这种相对的解辖域化运动并不彻底,会时常退回到解辖域化运动之前,直至克分子线与分子线都被引爆后,逃逸线带来了彻底的解辖域化运动,它打破能指的白墙,冲出主体性的黑洞,寻求全新的意义,逃逸线带来的能量是巨大的,对生成有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小说中的莉拉常常对于界限消失、逃逸线的显现感到恐惧,这是由于绝对的解辖域化运动之后带来的混沌与黑暗是令人绝望的,如果再建域失败,那么人可能还会踏入虚无之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展现了生成的过程:“生成-女人”“生成-莉拉”“生成-埃莱娜”,阿方索作为“生成-女人”的一个具象实例,也是城区中的“少数族”,与莉拉相互生成,同时埃莱娜与莉拉也是相互生成的,作品也与莉拉和埃莱娜相互生成,所以费兰特在结尾处才会说莉拉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就读者看来,埃莱娜的形象也已经在作品之中生成了。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根茎、逃逸与生成的理论能够令我们看到“那不勒斯四部曲”这个作为根茎的多元体的新芽,这些理论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个有力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 费兰特.碎片[M].陈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3] 费兰特.我的天才女友[M].陈英,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 Deleuze G,Guattari F.Mille plateaux[M]. Paris: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80.
[5] 董树宝.西方文论关键词逃逸线[J].外国文学,2020(4).
[6] 费兰特.失踪的孩子[M].陈英,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7] 周雪松.西方文论关键词解辖域化[J].外国文学,2018(6).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巩雨晨,上海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