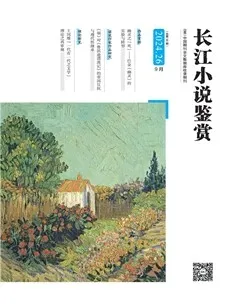晚明心学视野下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的人物论
[摘 要] 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批评鲁达形象为:佛、活佛、真、妙、趣、奇。与金圣叹评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中的鲁达形象批评相比,二者具有相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但在批评内容、批评形式、批评者在文本中扮演的角色三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晚明时期心学思潮的重要命题、情感色彩及其“狂禅”之气在容与堂刊本《水浒传》鲁达形象批评中均有体现。
[关键词] 容与堂刊本《水浒传》 鲁达 批评 晚明心学
鲁智深,本名鲁达,绰号花和尚,是《水浒传》的经典角色,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以下简称“容刊本《水浒传》”)是一百回《水浒传》批评本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个版本。此版本对鲁达形象的批评极具特色,多强调其“佛性”(活佛、圣人、菩萨、罗汉、真佛、真菩萨、真阿罗汉等)、“真性”与“趣味性”(妙、趣、奇)。其中“佛”在《水浒传》第三至第六回中出现次数高达60次。可鲁达杀人放火、喝酒吃肉,形象与一般遵守佛家戒律的僧人不符。在晚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容评本中的鲁达形象批评展现了心学的最高定理:“我佛一体。”容刊本《水浒传》注重内心品质而非外在行为的观念,更能体现出该时期追求个性的思潮与心学思潮交织下的社会观念,以及该观念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
1.“佛”
容与堂刊本《水浒传》评鲁达为“佛”“活佛”,认为其行为突出了内心的佛性,而不注重形式上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水浒传》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为金翠莲出头,评语曰:“佛。”[1]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鲁达睡醒了“在佛殿后撒尿撒屎”,对佛门重地不敬,评语却仍是:“佛。”鲁达酩酊大醉打坏了菩萨塑像,评语又曰:“佛。”[1]第九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锦还乡”中,宋江劝鲁达还俗未果,又劝他去当“名山大刹”的住持,鲁达坚定地拒绝此类身外“俗”物:“都不要,要多也无用。”评语曰:“佛”;鲁达正待“圆寂”之时,所问“如何唤作圆寂”,看似愚,实是大智,他“从此心中忽然大悟”[1],再不用任何言语,立地成真佛。
鲁达行为放肆,随心而起,任性而为,不在意外力约束。《水浒传》第四回尾批所言: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1]。
2.“真”
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不仅凸显了鲁达的“活佛”本质,还凸显了他的“真”。
第三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为弱者出头,评语曰:“真忠义”;他心思缜密,自掏腰包助金氏父女逃离,评语曰:“真男子,大丈夫”;与李忠极其扭捏的行为比较,鲁达的行为可称“真爽利”[1]。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中,鲁达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林冲,评语曰:“真忠义。”[1]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鲁达为防董超、薛霸在流放途中将林冲杀害,便亲自护送林冲,评语曰:“真佛、真菩萨、真阿罗汉。”[1]
3.“妙”“趣”“奇”
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的评论多提及“妙”“趣”“奇”,指出其行为和言语具有极强的传奇色彩,营造了有趣的氛围。
以第三回“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情节为例,容刊本评鲁达融之以赤子之心,发之为文,以为“妙”,以为“趣”,以为“奇”。鲁达以买肉为由,实为有意设计,惹郑屠先动手,好让他为金氏父女出头。评语曰:“虽然是寻事,实是有趣。”[1]二人交手,鲁达三拳就打死郑屠,评语曰:“妙。”[1]鲁达未曾想过将郑屠打死,害怕自己吃官司,便打算逃走。他灵光一闪,佯装骂郑屠诈死,以“慢慢理会”为借口,大踏步离开事发现场。评语又曰:“妙。”[1]
二、容刊本《水浒传》与《第五才子书水浒传》鲁达形象批评比较
晚明时期的《水浒传》众多批评本中,除容刊本外,最有特点、成就最大的当数贯华堂刊金圣叹评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以下简称“金评本《水浒传》”)。金圣叹生于明末清初,他性情孤高、率性而为,追求个性自由。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等著作的批评独到、专业且易懂,对这些著作的传播及相关评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容刊本《水浒传》与金评本《水浒传》中的鲁达形象批评具有相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但在批评内容的侧重点、批评形式、批评者所扮演的角色三个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1.相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取向
容刊本《水浒传》评鲁达为 “活佛”“真菩萨”,赞美其“真”的境界。而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透露了作者对此文学形象极高的赞美。第二回“史大郎夜走华阴县,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鲁达、史进、李忠三人一同吃酒,酒保的常规询问惹得鲁达心情不悦,嫌弃“这厮只顾来聒噪”,表达了鲁达的豪爽不羁,金圣叹评曰:“妙哉此公,令人神往。”[2]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鲁达两度醉酒,打坏金刚,大扰佛门,而鲁达大闹一番后竟“扑倒头便睡”,金圣叹评曰:“是大修行人,大自在法。”“菩萨,英雄也。”[2]容刊本与金评本《水浒传》中对鲁达形象的批评,均反复出现“佛”“奇”“妙人”等评语,都体现了对鲁达文学形象强烈的欣赏与赞美态度。
2.内容侧重点、批评形式、批评者所扮演角色的不同
2.1批评内容侧重点不同
容刊本与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批评的内容侧重点不同。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多立足于阅读与文学形象生成,从不同角度对其形象构成要素进行探讨。
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突破了形象塑造层面,从创作论角度,多以“妙笔”“写来偏妙”“神妙之笔”之语揭示作者如何塑造鲁达形象,并点出“《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2],立足于《水浒传》创作笔法分析,是自觉的文学批评。
同时,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具有高度总结性,这是容刊本《水浒传》不具备的。容刊本《水浒传》中,对鲁达形象的总结式批评多在回目的结尾后,以“李和尚曰”作为总评。而金评本《水浒传》每一回正文前均有承前启后的总结,行文过程中的评语也具有总结性。金评本《水浒传》第四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开头,金圣叹点明本回中作者如何塑造鲁达形象,并就鲁达形象在全书中的地位与武松进行对比,揭示小说中鲁达、武松的情节为“遥遥相对”,对读者的阅读有指导意义。同时,金圣叹的评点也让已深入人心的鲁达形象更为深刻,对尚未出场的武松人物形象起到了预示作用。鲁达从“小霸王”周通手上救下刘太公之女,金圣叹评曰:“鲁达凡三事,都是妇女身上起。第一为了金老女儿,做了和尚;第二既做和尚,又为刘老女儿;第三为了林冲娘子,和尚都做不得。然又三处都是酒后,特写豪杰亲酒远色,感慨世人不少。”[2]如此点评,贯通前后,能帮助读者整体把握鲁智深这一文学形象。由此可见,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批评的全面性和总结性高于容刊本《水浒传》。
2.2批评形式不同
容刊本《水浒传》中对鲁达形象的批评简洁明了,多口语化批评,如“佛”“这个和尚是活佛”“妙”“快意”“鲁智深是有用人”[1]等。而金评本《水浒传》中对鲁达形象的批评篇幅普遍较长,较有层次感。第二回中针对鲁达借钱这一情节,金圣叹将“茶钱洒家自还你”“洒家明日便还你”“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三句话联系,进行了长达一百字的详解。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简短的批评更短促,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则蕴含冷静、沉着的思虑。
2.3批评者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容刊本《水浒传》与金评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都具有强烈的认同感,但批评者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容刊本《水浒传》中,批评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已经将自己充分对象化,与批评对象鲁达的文学意象融为一体,批评者仿佛亲身体验鲁达在小说中经历的事件和情感体验,批评中蕴含着强大的心理能量。
金评本《水浒传》中,批评者则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进行自觉、有意识的文学批评。他融入文本,与容刊本《水浒传》的批评者一样置身于小说中,将自己当作鲁智深并产生了强烈情感。但当他跳出文本,又对文本进行冷静客观的创作分析,试图猜测与还原《水浒传》的作者在塑造鲁达形象时所用的笔法与心理。他自觉代入了专业文学批评者的身份,自如地融入文本、跳出文本,搭建起了一座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桥梁。
三、晚明心学思潮对容刊本《水浒传》鲁达形象批评的影响
心学从明代初期萌发,至明代中后期被王阳明发扬光大,王阳明派心学群体的庞大,使心学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能与佛、释、道三家媲美。晚明时期,王阳明派心学旁支泰州学派发展为一代显学,影响甚广。明代心学的最高定理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真理”,世间万物一切从“吾心”出发,向内探求,试图达到人的内心、精神与世间客观万物融为一体,一如庄子“万物而与我为一”的物我合一境界。
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批评凸显了强烈的晚明心学色彩,一方面体现在评语的内容、语义上,另一方面还表现在评语的形式与情感色彩上。
1.晚明心学思潮重要命题在容刊本《水浒传》鲁达形象批评中的体现
1.1吾心即佛,不假外求
容刊本《水浒传》将鲁智深定义为活佛,与晚明心学的最高定理“此心即佛,毕竟无异”“我佛一体”“我即是佛”[3]等观点如出一辙。天理、成佛之道是“不假外求”的心之本体,人自有之。人要探求天理,修炼身心,不需向外挖掘,只需向内心反省、革除内心魔障,自能成“佛”,人人都有成“佛”的潜能。鲁达这尊“真佛”,人格纯净,不掺杂外在闻见道理。他的心“无善无恶”,是心之本体,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它未经外界浸染,保持最原始的纯真状态,因而他性起而任意妄为,却最是“佛”。“无善无恶,是为至善。”[4]容刊本《水浒传》评鲁达“活佛反是完全的”[1],正是将心学命题“无善无恶心之体”强调的本性纯真推到“至”高境界,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叛和讽刺。
1.2“一知礼教,便不是佛了”
五台山众僧与无一处是“佛”而内心最是“佛”的鲁达也形成了对比。五台山众僧看鲁达浑身杀气,皆对长老“只管剃度他”不满,在背后议论讽刺。容刊本《水浒传》评众僧对鲁达的偏见为:“恨辞”[1],再评众僧人后的冷笑议论为:“要笑,不笑便不成众僧了。”[1]批评者对鲁智深与五台山众僧的褒贬态度非常明确,他对鲁智深的真“活佛”性情欣赏至极,对五台山众僧的假“佛”性则极度厌恶。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结尾处,评语道:“五台山众僧‘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1]他们虽吃斋念佛,严守佛教清规戒律,却“决无成佛之理”,此乃“外在闻见道理”使然[1]。五台山众僧“闭眼合掌”,尽守佛法不逾矩,却只是表面的“佛”,内心一团混乱,注定无法“成佛”。
1.3“人人皆能为圣人”的个性追求与“知行合一”的修炼方式
王阳明提出“人皆为尧舜”观点,在晚明发展成了“良知本体,人人具足”[5],将心学的社会功用降到了最低,而注入了“生活日用的平民意识”[3],蕴含着“人人皆能为圣人”的道理,促进了当时人们对个性思潮的追求,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在这种思想环境的影响下,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的形象批评也带有强烈的心学色彩。
容刊本《水浒传》中,鲁达的形象批评中蕴含了尚“真”取向。“尚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曾流行,《庄子》将“真”定义为:“真者,精诚之至也。”“道家美学所推崇的这种‘与道合一’‘天人一体’生命域,应该是一种本真生存方式,其所呈现出来的态势,则是如其所自,如其所本,如其所然,如其所是。”[6]晚明心学继承提倡“真”境界,与道家所追求的“通过自身的‘返璞’‘归真’还原到‘深心’的‘自我’”一致,这种境界不是后天形成的,而是与生俱来,存在于每一个体中,个体通过“格物”革除自己内心的障碍就能自然而然达到[6]。晚明心学的“尚真”取向,在李贽《童心说》中更是被提到至高地位。他所谓的“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是没有受到“外在闻见道理”浸染的“真心”。只有保持“童心”,才能不失 “真心”;不失 “真心”,才能保持“真人”;人是“真”的,才能做到“全而有初”。此“尚真”观念贯穿于容刊本《水浒传》鲁达的形象批评中,大字不识一个、不接受外在闻见道理,只坚守本心、任性而为的鲁达形象,是“真佛、真菩萨、真阿罗汉”,由此可见,“‘真’的确已成为贯穿其创作与批评全过程的一种审美标准与审美意向,从而获得其非同寻常的意义”[7] 。
2.晚明心学思潮对容刊本《水浒传》鲁达形象批评的形式、情感色彩的影响
明代心学在发展、传播、衍变的过程中,与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思想政策以及追求个性思潮的流行等因素相互交织,孕育了宽松包容、多元的社会思想环境。该时期涌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样式多种多样,不仅“语气轻松,文笔平易,顺手拈来,信笔写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8],其形式更突出的是“不拘一格,生动活泼,优游自在,长可达千言,短则一字一句”的语言风格[8]。
容刊本《水浒传》中对鲁达形象的评语则多是简短字句,如“佛”“活佛”“这个和尚是活佛”等,表达了对鲁智深这一文学形象强烈的赞赏,与其他评本相较,它形式短小精悍,评论简短却有持续的力量。
3.晚明心学思潮的“狂禅”之气在容刊本《水浒传》鲁达形象批评中的体现
晚明心学的“狂禅”之气指的是“狂禅之论(教),狂禅之解(理),更涉狂禅之行(行),狂禅之弊(证)”[3]。这是晚明心学及其所蕴含的精神对传统封建伦理的反叛,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容刊本《水浒传》对鲁达形象的评语有几处体现此点,如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的结尾,评鲁智深的行动方式为“率性而起,不拘小节,方是成佛成祖根基”[1]。正是此游刃有余、行云流水的行为方式,才使得鲁智深看似不“佛”,实际上最有“佛”性,他以“狂禅”之力追求个性的不受束缚、生命的自由,才能够“达到真力弥满、万象在旁、掉臂游行、即心即佛,进而达成顿悟人生真谛的‘本真’生命域的审美流程”[9],最后大彻大悟,立地成佛。
另一方面,容刊本《水浒传》的批评者立足文本阅读,以自身的精神融入文本,消除了文本间性,因而批评者对鲁智深身为和尚却喝酒吃肉、率性而为的行为感同身受。如此便使其批评蕴含了强烈的情感倾向,晚明心学的“狂禅”之风贯彻其中。其体现的批评标准已不再是刻板的封建社会道德准则,而是以批评者个人的审美理想来对鲁达形象进行评论,这是晚明心学思潮及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对文学批评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四、结语
容刊本《水浒传》对原著中诸多重要人物、情节皆有点评,与金圣叹评本《水浒传》相比虽略显简洁,但它是《水浒传》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就其中的鲁达形象批评而言,其透露的心学思想受晚明心学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李卓吾评本[M].李贽,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2] 施耐庵,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陈永革.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 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吴震.泰州学派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李天道,魏春艳.论道家美学之“本真自然”生存意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
[7] 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D].天津:南开大学,1995.
[8] 庄丹.试论心学对“评点”文学批评样式的内在影响[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
[9] 李天道,侯李游美.中国传统美学之生命意识与“本真”诉求[J].社会科学研究,2013(6).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郑伊琛,汕头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