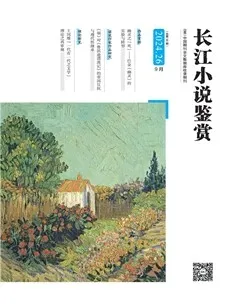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红楼梦》中本土化翻译的译者主体性
[摘 要]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先后被世界各国学者翻译出版,至今约有26部全译本。其中,由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所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自出版后,在英语国家读者中获得广泛好评。本文将原著与译本之间具有代表性的语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霍克斯在翻译时所选择的翻译策略以归化翻译为主、异化翻译为辅,并且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将具有本土化特色译本引入英语世界。
[关键词] 《红楼梦》 大卫·霍克斯 译者主体性 翻译策略
曹雪芹的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四大家族权势财富的起落过程为历史背景,以贾宝玉为主要视角,以宝、黛、钗三人的爱情悲剧为叙述主线,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百态。小说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红楼梦》中深厚文化内涵令国内外学者心驰神往,最著名的两部英译本各具特色,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汉学家大卫·霍克斯所译;A Dream of Red Mansions则是由国内翻译家杨宪益与其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杨宪益和戴乃迭与霍克斯分别基于自身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和个人语言文化背景,从不同的翻译观出发翻译该书。虽然这两部英译本都使《红楼梦》走向世界,但因译者不同,这两种译本的风格迥异。相较而言,霍克斯译本善化繁为简,将原著中复杂的表述译为简洁明了的英语,从而得到了英语世界读者的广泛接受。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其间涉及主体译者、本体内容、载体渠道、受体译文对象、目的翻译意图、环境文化及效果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等因素[1]。霍克斯在牛津大学研读中文,后到北京大学继续深造,在同仁兼挚友的吴世昌的鼓励之下,出于对中华古典文化的热爱,毅然从牛津大学辞去教职,耗费十年时间,将《红楼梦》的前80章回分为三卷译出。该译本结束了以往英语国家仅有充斥着大量错误翻译的节选本《红楼梦》的局面,打破了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本文将从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这两个方面,将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讨论和赏析。
一、翻译策略的选择
熊兵指出,作为一种宏观的翻译原则和方案,翻译策略是“翻译活动中,为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所依据的原则和所采纳的方案集合”[2]。翻译策略由此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归化策略和异化策略。汉学家霍克斯在《红楼梦》的翻译活动中,选择性采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并采用了音译、直译、意译等翻译方法以及减译、合译、转换等技巧。本文主要就其运用的两种翻译策略展开进行论述。
1.归化翻译法
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劳伦斯·韦努蒂所著的《译者的隐身》(1995年)。他在该书中认为,翻译活动是寻找文化和语言这两者之间共同点的过程,尤其要寻找相似的信息、表达形式或技巧。归化翻译法以目的语读者的接受为主要目标,要求作为中间人的译者运用读者所熟悉的语言习惯、俗语等表达原文,主张让作者接近读者。相反,异化翻译策略则维护了原著作者的地位,译者用充满异域文化的文字翻译作品,即读者主动靠近作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找到共同之处和差异之处,译者要选择是否淡化、保留异域文化,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霍克斯在翻译中所使用的语句简洁平白,直接表达原文作者所隐含的寓意和情感。他常站在目标语言受众即英语读者的视角进行翻译,多利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原著内容所传达的含蓄之美。
例1:潇湘馆、潇湘妃子[3]
译文:Naiad’s vsH7eJUE9ms6IXlX+UJtHg==House, River Queen[4]
“潇湘馆”这一名称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舜的妻子娥皇和女英听闻其死讯后悲痛欲绝,泪洒于竹子上形成点状斑痕。后两人自尽于湘江,故后人称为湘妃。林黛玉父母早逝,常因身世悲惨而啜泣落泪。大观园成立海棠诗社,贾探春因林黛玉所居的潇湘馆中多竹林,且时常感时伤物而落泪,便给她起了恰如其分的“潇湘妃子”这一别号,同时这个名字也隐含了黛玉泪尽而终的悲惨结局。霍克斯虽然通晓中国文化,但西方文化中并未出现过这种文化意象。为了使英语读者更好地了解“潇湘馆”和“潇湘妃子”所代表的文化含蕴,于是便借用了希腊神话中相似的神形象——水泽仙女那伊阿得(Naiad)。然而西方神话体系中的水泽仙女并未有湘妃一般的悲惨遭遇,更不用说湘妃最终化为湘江神女的结局。霍克斯希望目的语读者能简单迅速地了解林黛玉别号的故事背景,便选择归化翻译法,套用英西方神话中的意象。
例2:宝钗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来了。射覆……”[3]
译文:“Cover-ups? ” said Bao -chai,laughing “Why, that’s the grandfather of them all!”[4]
原文薛宝钗所提到的“射覆”指的是古代一种娱乐活动,一名参与者用碗将某物盖好即为“覆”,其余的人猜测所盖的是何物,则为“射”。大观园内,宝钗与众人所行的酒令便是其变体之一,猜不中者要自罚饮酒,射覆是古代文人聚会中,主人与宾客的常见活动。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世界,主人设酒款待宾客时没有这种既活跃氛围,又能体现主客双方文化素养的活动。鉴于此,霍克斯在尽可能忠实《红楼梦》的基础之上,把“射覆”译为西方的猜谜游戏,此处的翻译成功将原文本中蕴含的活动氛围在目标语文本中再现。
2.异化翻译法
例3:上坟烧纸[3]
译文:burning paper-money[4]
“上坟烧纸”是中国人祭拜先祖的方式之一,是孝文化的体现。这一文化负载词是中国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之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独特性。但在英语国家中,霍克斯不能找到关于祭祀亡灵的类似习俗,只能退而求其次,抓住“上坟烧纸”这一文化意象所表现出的具体动作场景——焚烧冥币。霍克斯通过应用异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传神地表达出了目标语言所不具备的文化负载词。中国的“纸钱”其实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中已经传入欧美,部分美国青年仿效当地的华侨祭祀其祖先,并称“纸钱”为“ancestor money”或“ancest blessing money”。相较于“paper money”,部分美国人接受的“ancestor money”一词运用了“意译+直译”的方法,把纸钱的指向对象清楚地意译了出来,即“去世后的祖先所用的钱”或“给祖先的钱,以求得他们的庇护、保佑”,尽可能地保留了汉语的文化特征,体现了纸钱在中国文化中的完整信息和实际用途,也避免了误解,较高层次地达到了忠实性原则的要求。
例4:稽首[3]
译文:first clasped his hands and knocked them against his forehead [4]
“稽首”本是中国古代的跪拜礼仪,为九拜中最为隆重的一种。原文中柳湘莲受到尤三姐自刎身亡的刺激,梦中哭醒后身处完全陌生的破庙,显得不知所措。于是在发现“瘸腿道人”后,便立马求救并询问自己身处何处。“稽首”这一动词表现出了柳湘莲的极度惊慌,他见人便拜。霍克斯在此处使用异化翻译法,以西方读者为中心,将“稽首”的跪拜流程用英文解释出来,便于读者理解这种中国跪拜礼仪,进而更流畅地理解《红楼梦》。
在对《红楼梦》进行翻译时,霍克斯应用了归化翻译策略,使翻译内容适应目的语言的习惯表达。尽管这种翻译使部分中国文化负载词无法同时达到忠实原文和“达意”的要求,但他也灵活运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保留了部分中国文化元素。因此,整体上霍克斯从目的语译文的可接受性出发,翻译时主要采用了归化策略,同时以异化策略作为补充。
二、译者主体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研究学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共同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的要求。翻译研究学派提倡面向目的语所处的文化,由此外国翻译理论学者逐渐将研究的重要方向从翻译的根源——语言投向更为广阔、深邃的文化历史领域——语言产生和发展之处。
翻译界传统的翻译观念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一个“隐形人”,让译文“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5]。作为语言活动中的信息传递者,译者常常面临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不能平衡地传递给双方对等信息的窘境。译者所翻译的译文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自身所处文化环境的“气息”。因此,完全没有译者主观性的译著是不存在的。
与此同时,译者也不能保证对原著的理解绝对忠实,翻译的最终目标是译文要同时表达出作者所述的表层文字意思与更深层的含义。然而,不同语言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因此,关于译者主体性的讨论和衡量就变得十分必要。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翻译观遮蔽了翻译的主体——译者的话语,导致了译者地位的边缘化,也造成了历来的翻译研究不够重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因此,只有重新认识翻译的性质和文化功能,才能将翻译主体从文化遮蔽状态中彰显出来,才能将翻译主体提到翻译研究的重要日程上来[6]。
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不甘只做作者或读者的“仆人”,而是彰显了自己作为译者的主体性,其最终的翻译目标是向目的语读者尽可能还原作者原本的意图,使译文读者稍稍感觉到译者读原著时所感受到的快乐。因此在翻译该书时,霍克斯基于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以一个英语世界的读者的视角去表述阅读该书时的所见所想,因此其译作更符合读者母语的表达习惯。霍克斯将自己代入读者视角,与读者的地位几乎是平等的,因此霍克斯的译本在英语国家备受赞誉。
例5:癞蛤蟆想吃天鹅肉[3]
译文: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4]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本是中国民间流传的俗语,常用来比喻某人没有自知之明,意为必然不可能得到某物。汉语通过将“癞蛤蟆”与“天鹅”这两种长相上相差甚远的动物进行对比,直白地表达了贾瑞觊觎王熙凤时痴心妄想般的自信。在英语国家中,虽然上述两种动物并不具备相应的汉语寓意,但霍克斯却最大程度地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化用了已存在已久的“a wild-goose chase”(荒谬的追求),将“swan”替换为“goose”,并且在整句翻译中巧妙运用“天上地下”的对比——“on the ground”和“in the sky”,更加凸显了两者的巨大差异性,令西方读者阅读时可以立刻心领神会。
例6:仙师[3]
译文:holy one[4]
霍克斯的译本中,其将原文中的“仙师”一词替换成基督教里指代“上帝”的“Holy one”。他作为一名英国翻译家,接受的是西方宗教文明。汉语世界和英语世界的信仰体系不同,这种替换的做法毫无疑问使译文对原文的忠实性打了折扣,使西方读者失去了一次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这是其翻译局限性的体现。
三、结语
霍克斯根据自己早年翻译《楚辞》的实践经验,基于目的语读者视角,灵活巧妙地运用归化翻译策略,辅之异化翻译策略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使英语国家读者有了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机会。究其原因,在于霍克斯的译本主动打破了原本横亘在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主仆关系”的锁链,充分释放了译者对原著文本理解的主动性。同时,该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彼时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边缘性地位有着很大的联系。
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将位于世界另一端的陌生精妙的东方文化传播进英国,其翻译时的指导思想以及译本对我国翻译工作者建立起受世界读者欢迎的翻译观,并推动中国由“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转变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吕俊,侯向群.元翻译学的思考与翻译的多元性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9(5).
[2] 熊兵.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J].中国翻译,2014(3).
[3]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曹雪芹.红楼梦[M].Hawkes D,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5] 许均.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6]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苟婷,南充科技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