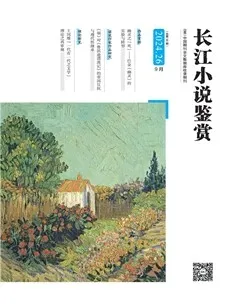空间视角下《寄物柜婴儿》主题探究
[摘 要] 《寄物柜婴儿》是村上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材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频发的寄物柜遗弃事件,借由书写“弃儿”主人公成年后在东京的悲剧经历,剖析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弊端。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分析“寄物柜”空间所隐喻的日本现代社会精神困境,通过解析阿桥、阿菊、阿莲莫莲三位主人公的空间实践,探究青少年对抗现代社会病理、构建真实自我的成长之路。对青少年自我构建路径的描写体现了村上龙对青年人精神需求的敏锐观照,在展现作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人文精神的同时,也为读者如何摆脱精神的空虚感、压抑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寄物柜婴儿》 村上龙 空间
1976年,村上龙发表描绘年轻人颓废青春的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凭借其主题的先锋性和独特的艺术性获得第19届《群像》新人文学奖、第75届芥川文学奖,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自出道以来,村上龙凭借敏锐的问题意识,用文字直击青少年犯罪、援交、自闭等社会问题。他曾直言,“我的作品是怀着对‘日本体系’的厌恶写下的”[1]。换言之,用敏锐笔触揭露日本社会病理是村上龙创作的原动力。
《寄物柜婴儿》是村上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材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频发的寄物柜遗弃事件,借由书写“弃儿”主人公成年后在东京的悲剧经历,剖析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弊端。对意象的敏锐捕捉和细致描绘是村上龙小说的艺术特点,交错纷繁的意象构建了一个生动可感的艺术世界。从主人公被遗弃的“寄物柜”到成年后来到的“更大寄物柜”药岛、东京,“寄物柜”这一空间意象多次出现,无疑具有丰富的隐喻含义。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对村上龙小说的研究多以“亚文化”“人物形象分析”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对象聚集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69》等作品上,针对《寄物柜婴儿》的解析尚少。
日本方面,武田信明考察了“寄物柜”“便当盒”“铅盒”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点明了密闭空间中“内”“外”的反转和对立是小说的重要结构[2]。菊田均研究了作家的人物塑造,将“细节描写的写实化”和“人物塑造的非人化”视为作家的创作特色[3]。住吉雅子从作品的时代批判性出发,揭示了作品映射的是“统一价值评判体系的缺失”这一社会问题[4]。而从空间视角对《寄物柜婴儿》进行考察的较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现代社会城市的空间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起,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了空间转向。空间和时间在社会历史研究中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空间不是抽象的自然物质,而是社会关系的交织与具体化,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控制、主宰和权力的手段”[5]。他把空间视为强有力的社会生产形式和认知行为,而不是被动地容纳各种社会关系的静态容器。空间不再是时间的附属品,而是一种文化实体,是融合文化、地理的综合产物。在文艺批评领域,“空间”这一概念也备受关注,但目前中国从空间视角进行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作品上,聚焦日本文学的研究较少。本文尝试从空间的角度,分析“寄物柜”这一空间隐喻的现代日本社会精神困境,并从阿桥、阿菊、阿莲莫莲三位主人公的空间实践出发,探究青少年对抗现代社会病理、构建真实自我的成长之路。
一、“寄物柜”:边缘化的封闭空间
《寄物柜婴儿》出版于1980年,如书名所示,男主人公阿菊和阿桥都是被遗弃在寄物柜里的孤儿。根据小说设定,1969年到1975年间,以同样的方式被遗弃的婴儿有68名,只有阿菊和阿桥活了下来,后被樱野圣母育婴院领养。作为仅存的两名“寄物柜婴儿”,即便在孤儿院中,二人也是边缘人中的边缘人。
小说中,男主人公的设定取材于20世纪70年代日本频发的寄物柜婴儿遗弃事件。回顾历史,寄物柜在日本的普及过程,也是日本都市快速发展的过程。寄物柜诞生于美国,1964年最先被应用于日本新宿站,此后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在日本逐渐普及。1970年2月,第一起寄物柜婴儿遗弃事件发生在东京都涉谷区的东急百货西馆一楼,此后,1971年发生了三起类似的事件,1972年八起,1973年更是激增到四十六起[6]。寄物柜成为日本都市中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隐喻性质的特殊空间,投射出快速现代化后,失去统一价值观念、背弃伦理的日本社会的病态。村上龙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社会问题,他认为高速发展的日本失去了一些东西,失去的并非传统文化,而是“实现近代化这一目标”,换言之,当时的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种“丧失感”[7]。从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开始,“丧失感”一直是村上龙创作的重要主题。日本社会在快速发展中,空间表征崩坏、社会价值观瓦解、群体秩序失衡,男主人公阿桥、阿菊被遗弃的寄物柜可谓是这一现象的空间呈现。
寄物柜这一空间投射到阿桥、阿菊身上,引发了二人幼年时的一系列精神问题和成年后的身份焦虑。在孤儿院时,阿桥和阿菊分别被精神病医生诊断为因遗弃导致的“丰富性自闭”和“匮乏性自闭”。阿桥的症状为热衷于一种奇怪的过家家游戏,他将塑料玩具碗、锅、洗衣机、冰箱之类的东西整齐地摆放在地上,不允许别人挪动。如果有谁改变了玩具的位置或不小心踩坏了玩具,他便疯了似的发火。阿菊则害怕静止,喜欢急剧的空间移动,他时常被幻觉所控制,感到在自己的周围有个东西正在高速旋转,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并准备飞向远方。处于这种环境之中,他无法让自己静止不动,于是他数次乘车偷偷离开孤儿院。设定为“双生子”的阿桥和阿菊拥有“一体两面”的性格特征,阿桥性格敏感而阿菊粗犷,其不同的自闭症状实为创伤体验在相反性格上的差异化表现。经过心理专家的精神治疗,二人症状暂时好转,得以重归正常生活。
此后,故事发生的舞台从孤儿院转到养父养母家,又因二人离家出走转到东京,场景不断变化,但寄物柜的影响并未消失,具有相似性的各类特殊空间在他们的生活中接连出现。例如被二人作为游乐园的废弃矿岛、边缘社区药岛、少年犯监狱、精神病院等。这些空间延续了寄物柜封闭的特征,尤其是东京中心的封闭空间药岛,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
离家出走后,阿桥和阿菊先后在药岛中生活。药岛实为一块被有毒物质污染的土地,为了保证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卫生局疏散了居民,用铁丝网封锁了这片区域,同时派警卫队在周围巡逻。但由于警力有限,各地的流浪汉、娼妓、通缉犯等人群逐步聚集到这一被主流排斥的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地下社会。讽刺的是,由于罪犯聚居在药岛,反而降低了其他区域的犯罪发生率。离家出走后,阿桥无处可去,最终来到药岛,他的经历是部分社会边缘人的缩影:无法融入大众,只能在与主流隔离的特定空间中生活。
对阿桥与阿菊而言,药岛实为一个更大的寄物柜。药岛和城市间二元对立的空间规划,是边缘与主流社会秩序的地理呈现。在此类空间生活的过程中,居住者边缘人的身份属性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受社会阶层属性的投射,困于边缘空间的阿桥和阿菊进一步在自我认知上将社会观点内化,他们认为自己是“弃子”,是“不被需要的废品”。
二、“天王星”:都市青年的热带幻想
村上龙的小说中,主要人物虽为都市青年,却未能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尤其是混血儿,心中存在着“归乡情结”,这里的家乡不是籍贯的归属,更多的是青年人的精神标记和身份原点[8]。《寄物柜婴儿》中,阿菊在药岛认识的流浪者达雄的父母是菲律宾人,虽然生长于日本,达雄却本能般地向往热带地区,每当“看到宿务岛的照片,总觉得那里很美”[9],他向阿桥吐露自己的心声:“我的心里本来应该充满南方岛国温暖的阳光,但现在却十分冰冷,结成了坚硬的冰,坚冰形成了手枪的形状,它说我没用,没有人需要我。”[9]换言之,在菲律宾和日本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中,达雄一直未能在东京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未能形成“日本人”这一身份认同,菲律宾才是他的向往之地。
作为在《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悲伤的热带》等村上龙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区域,热带地区显然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都市人心中失落的故土。在都市中无法找到自我归宿的现代人,由于归属感的缺失,心向更原始、更热情的热带地区。这一点在《寄物柜婴儿》女主人公阿莲莫莲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与达雄不同,阿莲莫莲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但她曾多次幻想将东京变为热带沼泽。在她的想象里,钢筋水泥的都市东京无聊得令人生厌,成为热带王国后的东京,则呈现出一种浪漫化的野性之美。她曾向朋友幸子这样描述:“积云总有一天会撒下大颗的雨点……水洼的积水会不断扩散……不过,我等待的是不久的将来,雨过天晴,膨胀数十倍的太阳再次出现时,我在那塔楼屋顶上和伽俐巴一起生活,周围布满了沼泽、妖艳的花朵、热带的丛林,还有流淌的汗水、染上热病的人群,其他则没有任何奢望。”[9]
阿莲莫莲所说的“伽俐巴”是她饲养的鳄鱼。阿莲莫莲喜欢鳄鱼,自称为“鳄之国”的大使。为了让热带物种能在东京生活,她专门准备了一个特殊房间,房间里设置了八个加湿器,天花板上安装了十二个红外线灯,鳄鱼的水池各处遍植水草。经过一番装饰,这一城市空间有了热带丛林的气息,明明是由混凝土、玻璃、塑料环绕的水泥房间,空气里却充满了鲜花和水果的气味,周边环绕的却是珊瑚礁、水藻、椰子树叶。阿莲莫莲将这个房间取名为“天王星”。
从东京的沼泽幻想到布置热带空间“天王星”这一空间实践,阿莲莫莲为自己、为伽俐巴构建了一个都市中的“异托邦”。少女在房间创造热带雨林环境,饲养鳄鱼,这一略显离奇的设定,在故事中却别有深意。表面上看,女主人公是都市中的成功者。她的父亲是公司经理,母亲曾是儿童歌星,家境富裕。阿莲莫莲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可爱”,因容貌过于精致,所有的人都会夸她“可爱”。凭借外貌和家世,她在高中时就成为模特,出演过2arg1hqUE0TzRULBhsUzgavkX7Z3D+NFrAn/1h1KtqA=电影。但生活优渥、外貌出众的阿莲莫莲却选择了与家庭决裂,辍学独自生活,直接原因是父母混乱的婚姻关系。父母互相默许对方在外面有年轻的情人,在家里却表现得相亲相爱,这并不是在装模作样,而是他们并不在意婚姻中的忠诚。家庭错乱的价值观和混乱的男女关系令阿莲莫莲痛苦迷茫。父母不但对她的情绪置之不理,反教育她不该对婚姻关系过于天真。阿莲莫莲看似拥有幸福优渥的家庭环境,精神世界和父母却并无连接,在东京这一都市中也未找到自己生活的锚点。因此,阿莲莫莲希望通过“热带王国”的回归幻想来摆脱城市带给她的空虚感。“天王星”是一个浪漫化的自然空间,女主人公想通过唤醒本性、回归自然的方式消解都市人精神困境。
阿莲莫莲的幻想稚嫩而天真,终将只是幻想。尽管全力营造热带的氛围,伽俐巴还是每月发狂一次,不吃食物,一边低声呻吟一边用尾巴拍打墙壁。这是伽俐巴身体里的热带血液在抗拒伪造的热带空间。最终鳄鱼在搬家途中因车祸死去。“鳄鱼之死”代表阿莲莫莲热带幻想的彻底破灭。
小说结尾,越狱成功的阿菊与阿莲莫莲再度回到东京,当被问起身份时,阿菊不假思索地说:“我们是寄物柜婴儿。”[9]借男主人公之口,阿莲莫莲的身份实现了再定义,富裕家庭带给她的是道德观崩坏后的空虚,精神层面的她同男友阿菊一样,是被遗弃在寄物柜里的婴儿。
纵观阿莲莫莲故事的脉络,女主人公从家庭空间中的“可爱孩童”到热带空间中的“鳄鱼大使”再到寄物柜空间中的“婴儿”,空间的流转描绘着她认知变化的路径。虽然最终未能形成健全、独立的自我认知,但她的故事却有着特别的意义。与精神存在问题、身负多重边缘身份的二位男主人公相比,女主人公的设定更大众化,她将故事的主体由边缘人引入了遭受价值观崩坏之苦的普通年轻人。主体的延展扩大了主题的适用性,体现了作家村上龙对都市青年精神困境的敏锐观照。
三、“寻亲”:双生弃儿的自我追逐
村上龙曾在访谈中表示,“他者”是纯文学的重要课题,只有“通过他者才能确定自身”[10]。对孩子而言,父母无疑是生活中最先接触、最重要的他者,孩子通过和父母的相处,逐步确立自我意识。但对身为孤儿的阿桥及阿菊来说,由于缺乏和父母的互动,如何确立健康、完整的自我成为他们面临的问题。“弃儿”的身份扭曲了二人的自我认知,他们都曾数次对周围人吐露心声,表明自己是“不被需要的”“被抛弃的”。
自我认知的缺失促使二人开始身份追逐之旅。阿桥的故事以“寻母”为主线。离开孤儿院来到养父母家所在的海岛后,他不自觉地在生活中寻找着“亲生母亲”的替代品,因而对一名乞丐婆婆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老妇人常年在海岛的废矿区中游荡,通过乞讨和偷窃维持生活。阿桥一看到婆婆就感到心痛,总觉得她是自己的生母。这是他对母亲抛弃自己的恨意在作祟,潜意识里认定遗弃孩子的女人定会流浪他乡,但他又控制不住地想要抱住可怜的妇人,喊她“妈妈”。阿桥将对生母的情绪投射到流浪婆婆身上,这种杂糅了爱与恨的复杂感情,恰恰反映了他渴求母爱而不得的痛苦挣扎。
进入中学后,受青少年更为迫切的身份认同需求的驱使,为了找到生母,阿桥离开海岛,流浪东京。在东京的“封闭空间”药岛中,他结识了音乐制作人D先生,成为一名歌手。凭借出众的唱歌技术和引人注目的悲惨身世,阿桥很快声名鹊起,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但他只是听从D的指示,扮演“身世离奇的怪才歌手”这一角色,甚至在访谈和节目中,都只回答D为其设定好的标准答案,以维持人设。
在外界规训对自我的蚕食中,阿桥看似成功,其实是在通过伪造“虚假自我”逃避自我,他的真实心理状态退行到了幼年的自闭状态。在封闭的心理空间中,他深受“自我缺失”的折磨,这进一步引发了他对自身存在的思索,开始反复叩问内心“我是谁”,决定由东京回到海岛探亲。从海岛到东京再回到海岛,人物情感的转变和空间的变迁相互推进,而其主轴是青年的自我构建渴求。
随着歌手事业愈发繁忙,阿桥的精神问题也愈发严重。他的心理空间在社会空间的挤压中濒临崩溃,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在“真我”与“假我”的拉扯下,他因捅伤妻子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这体现了他竭力构建完整自我的强烈渴望。
与阿桥不同,阿菊的自我构建之路以“寻父”为主轴。“寻母”背后是敏感内向的阿桥对亲密关系的期冀,他试图从与母体的链接中修复被遗弃的伤痛,整合破损的自我。而阿菊则通过追寻“父性权威”、重塑价值观来重建自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从宏观层面而言,处于一个失去现代化旧目标,且新目标尚未建立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丧失感”。从家庭层面而言,体现为传统的父权制失去支配力量,新的权威却仍未建立。
受社会环境和孤儿身份的双重影响,阿菊从孤儿院起,就对“父亲”这一角色充满向往。阿菊所了解的第一个男性形象是教堂壁画中长满胡须、双手托举羔羊的基督形象,之后他不自觉地将画像和生活中见到的男性对比,试图找到现实中的“基督父亲”。第一个被用来对比的人物就是养父桑山。但初次见到桑山,他却十分失望,因为桑山身材瘦小、畏畏缩缩,和基督毫无共同之处。真正将阿菊基督幻想现实化的是废矿中的年轻男子伽泽尔。废矿是海岛中一处被抛弃的空间,其间的景色和阿菊幼年因被母亲抛弃而产生的神经质幻想十分相似,是他潜意识中对外界恐惧的现实投影。伽泽尔在这一空间中骑着摩托车登场,先是解救了被野狗围攻的阿菊,后指引阿菊去寻找毒药“曼陀罗”,他的形象和壁画上的基督就此重合,化为阿菊一直追寻的理想父亲。
来到东京后,阿菊因误杀亲生母亲,被关入少年犯监狱。杀母的痛苦,令他一度颓废,但他仍未忘记伽泽尔的指引,循着“曼陀罗”的线索,和阿莲莫莲一起来到小笠原群岛,找到了能毁灭整个东京的毒药。在文学语境下,阿菊对东京的“破坏”具有象征意义,其背后隐含的是“重生”,他期望通过逾越性的空间实践彻底打破都市空间表征,重塑价值观。
结尾处,东京因毒气而全面瘫痪,阿桥趁乱逃出精神病院。由于中毒,他处于失控的狂躁状态,试图毁掉周边的一切事物。但在路边,他看到一名孕妇,联想到自己的母亲后,阿桥努力寻回了理智,放声歌唱。作者以阿桥的歌声结束全书,并强调这是真正属于阿桥自己的、全新的歌。这首歌预示着村上龙对青年终会找回自身的主体性,构建完整自我的乐观期待。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起,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开始了空间转向,促使文艺批评将目光由小说的“时间”转到“空间”上。村上龙通过描绘寄物柜等封闭空间,映射了日本社会快速发展下,空间表征的崩坏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瓦解。面对价值观的失序,阿桥、阿菊、阿莲莫莲三位主人公分别通过“回归自然空间”“寻父”“寻母”这些个性化、逾越性的空间实践,在空间的流转中,逐步尝试构建自我,勾勒出一条条边缘青少年的成长之路。对青少年自我构建之旅的描写体现了村上龙对青年人精神需求的敏锐观照,在展现作家深刻的社会洞察力和人文精神的同时,也为读者如何摆脱精神的空虚感、压抑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村上龍.村上龍文学的エッセイ集[M].東京:シングルカット社,2006.
[2] 武田信明.「コインロッカー·ベイビーズ」-柔らかい箱の群れ[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93.
[3] 菊田均.自閉する「私」ー村上龍「コインロッカー·ベイビーズ」[J].文芸,1981(8).
[4] 住吉雅子.都市と病:村上龍「コインロッカー·ベイビーズ」論[J].奈良教育大学国文:研究と教育,2016(39).
[5]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Wiley-Blackwell,1991.
[6] 大倉守夫.コインロッカーの実態と防犯対策[J].警察公論,1948(8).
[7] 村上龙.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M].张唯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8] 徐明真.村上龙青少年主人公作品研究——以主体性的确立克服危机[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9] 村上龙.寄物柜婴儿[M].栾殿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0] 村上龍.純文学に関するQ&A[M].東京:講談社,1991.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吴玉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