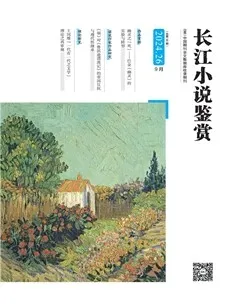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学生态与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转变
[摘 要] 端木蕻良1942—1944年客居桂林时期的经历于他而言异常重要。桂林为端木蕻良提供了较为安稳的生活环境,影响了他的精神世界与小说创作。在桂林结识的文坛新朋友缓解了端木蕻良丧妻的痛苦,缓和了与东北作家群逐渐疏离造成的孤独感。桂林多元的文学生态为端木蕻良转变小说创作的题材、内容与主题提供了现实条件,并间接推动了其小说风格由刚健到阴柔的转变。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转变既体现了作家精神空间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又体现了城市对文学的塑形能力。同时,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时期的小说创作转变,扩展了“桂林文化城”的文学格调。
[关键词] 文学生态 端木蕻良 小说创作转变 桂林
端木蕻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体裁是小说。早期对端木蕻良的研究中,其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萧红离世后的创作极少被人关注[1]。随着对端木蕻良研究的深入,其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创作也逐渐进入研究视野。21世纪以来,部分学者指出,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时期的心态与此前截然不同,心态变化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此类文章一般将端木蕻良创作转变的原因归结于境遇变化与萧红的离世,并将转变情况大致概括为由豪放到柔美的文风变化,鲜少有学者从地理空间的改变上分析转变的表现、原因及意义。桂林如何影响了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尤其是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学生态对其小说创作的变化发挥了什么作用?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转变又具有什么意义?
一、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
抗日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演进的步伐,形成了独特的抗战文化。抗战时期,中国形成了多个文学中心。1938—1944年,桂林因文化的繁荣引起全国各地的关注,被赞誉为“桂林文化城”[2]。抗战时期在桂林居住的文艺工作者达1000多名,茅盾、巴金、柳亚子、欧阳予倩、钟敬文等知名文人都曾在桂林生活过。他们在桂林积极地开展各项文化活动,歌咏会、诗歌朗诵会、街头诗画展等活动种类繁多。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出版事业生机勃勃,书籍印数“占全国出版总量的80%”[3]。这一时期文艺发展整体形成了“北有延安,南有桂林”[4]的格局。
1938—1944年,桂林的文化发展重心是抗日文化。进步文人的大部分文化活动都与抗日救亡运动息息相关,他们通过传播抗日思想的方式塑造民族共同体意识,或以诗歌会等形式直接弘扬民族自信和爱国主义精神;或以《救亡日报》等报刊为阵地,创造抗日文化的宣传空间。
文化与文学的发展一直联系紧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极大程度源于中华文化的特性。同时,文学也具有一定相对独立性并能够反哺文化。以抗日文化为主的桂林文坛并不只有抗战文学,它呈现出多元的文学发展格局。抗战时期的桂林,纯文学期刊众多,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在桂林得到深化发展,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也在桂林兴盛起来。这一时期,桂林文坛最突出的特点是文学取向灵活多样。呼唤救亡的战斗文学、揭露大后方黑暗现实的暴露文学、关注底层命运与阶级压迫的左翼文学等都是桂林文坛的成果。客居桂林的作家的思想倾向不一,可见,抗战时期桂林文学的发展趋势多元。
端木蕻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是作家本人的情绪投射。客居桂林时期,端木蕻良处于萧红离世带来的痛苦与长达十余年的流亡生活带来的精神困境中,不再意气风发。他这个时候沉迷于研究《红楼梦》,在文学创作之外寻求精神寄托。在文学创作方面,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时期创作出《早春》《女神》《饥饿》等小说,也创作了《哀李满红》等散文。除此之外,他客居桂林时期还接触了自己以前从未涉足的戏剧创作,著有《林黛玉》《红拂传》等剧本。
二、多元化文学生态与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转变
1.小说题材由实转虚
东北作家群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脱离左翼文学的发展而单独阐释[5],端木蕻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高度就充分体现了左翼文学的发展进程。《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等小说重视故事的真实性,端木蕻良认为,“有了真人真事做底子,容易计划,容易统一”[6]。从端木蕻良客居桂林之前的小说作品看,抗日意识、阶级矛盾直接存在于叙事表层,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思潮吻合。《科尔沁旗草原》反思家族社会在时代变动中的命运,是一部展现草原文化的史诗;《鴜鹭湖的忧郁》《母亲》《雪夜》等述说底层人民生存的艰难与困境,指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浑河的激流》《萝卜窖》等则歌颂抗战中的英雄人物,希望以此实现文艺报国的社会抱负;《新都花絮》《大地的海》等作品则描绘战争背景下的人生百态。左翼色彩与时代背景使端木蕻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呈现出现实主义风格,而他客居桂林时期的部分作品则表现出梦境般的虚幻色彩。这与桂林的文学生态有直接关系,桂林既是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又是多样化文学创作形式汇集的场域。王鲁彦的《文艺杂志》、熊佛西的《文学创作》等文艺期刊都体现出对文艺本身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在坚定文艺报国的同时并不排斥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作品。包括左翼文人主编的《大公报·文艺》等文艺报刊也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倾向表达了欢迎,在当时的桂林文坛,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并不只有现实题材。
不排斥多样化文艺思潮的文学空间与生态为端木蕻良转变自己的创作题材提供了条件,使他能够有动力与信心进行文学创新,并能够将这些作品发表出来,《初吻》就发表在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上。《初吻》《早春》以儿童视角叙事,表现出与20世纪30年代“出走加回顾”式家族书写的巨大差异,以儿童的眼光回忆故土的温馨。同时,端木蕻良又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忧郁、悸痛与悲哀,以儿童视角承载成人的感伤情绪。《海港》《红夜》写于1942年,这两篇小说的现实主义色彩较少,均淡化了时空,模糊了时代背景,叙事主体的身份也不明确。除了儿童视角、模糊时间与空间,端木蕻良这个时期还通过神话改编逃离现实语境。《蝴蝶梦》《女神》《琴》是三篇根据古希腊神话创作的短篇小说。神话介入小说,增强了小说的唯美感,通过梦幻般的意境与故事淡化现实色彩。“过去死了,菠茜珂才从梦境里走到现实。”[7]端木蕻良通过小说创作远离现实,传递自己渴望走出过去、实现新生的愿望。
2.小说表现内容由外部转为内心
伴随小说创作题材发生变化的,是端木蕻良创作内容的改变。端木蕻良客居桂林之前的小说大部分用浓重笔墨描绘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表现东北民间强健的生命力。同时他以游子的身份,带着失去家园的伤痛审视东北,观察东北的社会问题。在地域文化、原始生命力、社会环境、阶级矛盾的融合之下,端木蕻良的早期小说表现出独特性,同时也体现出外倾的写作倾向。文学与作家的生命体验、情感状态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苦闷、痛苦等内心情感状态是作家创作的强大驱动力。端木蕻良前期的创作冲动来自外部世界的各种问题与现实状况,他以满腔抱负将它们诉诸笔端。
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时期的作品,实现了从关注外部环境,到关注个人生命体验构成的转变。《海上》是端木蕻良用第一人称视角完成的作品,全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散文化的笔法更像叙述者本人的情感剖析。“我”看到她划着奇异的船向“我”而来,她顾盼地向“我”一笑。海面如同沟通阴阳两界的媒介,使端木蕻良与亡妻再聚,小说以诡异又美好的氛围传达了端木蕻良对萧红的思念。《饥饿》同样以第一人称视角完成,可以看作端木蕻良对自我精神状态的揭露。小说多次提及自己在寻找自我,提到物质满足并不能代替精神丰富。这篇小说以意识流的笔法,表达了端木蕻良寻找精神动力的渴望。
早期人类的神话、巫术等已经具有了情感宣泄的功能,文学创作“制造虚拟情境宣泄释放内在心理能量”[8],以发挥精神疗愈作用。如果说端木蕻良在“左联”时期,因为孤僻与自由气息[9]而游离于左翼阵营的边缘,那么,他在抗战时期,尤其1942年之后就游离于东北作家群之外了。在端木蕻良与萧红结合之初,骆宾基、萧军等人就为此愤怒不已,写了一些文章表达不满。直至1942年,端木蕻良由于萧红的离世与东北作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骆宾基1942年出版的《鹦鹉和燕子》中写鹦鹉和燕子本来是挚友,分离之后鹦鹉最终被黑猫咬死。这篇小说情节生动,行文颇有影射之意。幸运的是,桂林开放的文学生态与文化空间使端木蕻良结识了一些知识分子。陈迩东、熊佛西、朱荫龙等与端木蕻良相交甚好,端木蕻良后来回忆人情的暖流使他重获生机、重燃创作激情,许多终身挚友就在这一时期结识[10]。抗战时期桂林较为稳定的局势,使端木蕻良能够暂时安定下来,并多了很多V6ULHGOnI6S/uNH5PSuq6Lfs/DorblNwsB4dhkp3AFY=时间思考。桂林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一方面使端木蕻良能够探索新的文学创作模式,以坦然的心态寻找新的叙事方式;另一方面,又为端木蕻良融入新的群体、安抚自己的伤痛、直面人生苦难提供了现实条件。
3.小说主题由表现转为反思
抗战初期的文学洋溢着高昂的旋律。之后,这些作家逐渐意识到抗战不会迅速结束,初期的激昂精神逐渐转变为对抗战的深度思考。1941年前后,连续出现了一批反思知识分子身份的小说。不同于王西彦的《家鸽》、司马文森的《雨季》等反思知识分子害怕投身战场的小说,也不同于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描写了战时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空虚,端木蕻良这个时期的反思作品呈现出反思自我的趋向,而不是反思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他的反思是完完全全地对自我的剖析,以近乎自虐的反思寻求灵魂的解脱。《初吻》《早春》等都体现出端木蕻良这个时期的忏悔意识与反思倾向,他一次又一次追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痛苦,为什么我这样凄凉。”[11]所以有学者认为,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时期,过度沉浸于自己的悲伤之中,以至于失去了创作激情、昂扬气魄与社会责任感[1]。
实际上,一方面端木蕻良的反思的确与萧红的离世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与当时桂林比较突出的“反思思潮”有关;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端木蕻良的某些篇目中也体现了其对自身境遇的超越,对普遍问题的观照。客居桂林时期,端木蕻良开始思考人性的普遍问题。
《雕鹗堡》极富象征主义,现实感的减弱与动物叙事使小说拥有极强的可阐释性,并超越时代语境的局限。从叙事表层上看,小说以石龙象征端木蕻良,以代代象征萧红,以石龙与代代之间的感情象征自己与萧红备受争议的爱情。小说在更深层次上呈现出端木蕻良对人性的思考。雕鹗掌握着整个村子的命运,每天盘旋在天空监看居民的一举一动。人们早已习惯雕鹗的行为,并待在舒适圈内。雕鹗堡的居民蒙昧、麻木,只会嘲笑意图挑战雕鹗的石龙。石龙失败之后,“人们好像又恢复了往常的命运的统治,觉得心安而满意”[12]。这部小说已经不单指向当时的国民性问题,而是指向了人类的普遍问题。大部分人习惯墨守成规,如果出现一个人意图打破原有秩序,即使这个秩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他也将面对多数人的反对甚至嘲讽。
4.小说风格由刚健转向阴柔
端木蕻良的小说在题材、内容等方面产生明显变化的同时,其小说的风格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端木蕻良初登文坛时的小说作品与东北农民生活以及东北地域景观有着无法斩断的关系。此时期的端木蕻良坚信东北农民顽强的性格,他致力于发掘关东草原的生命力与变迁史[13]。端木蕻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充斥着对东北雄奇壮丽景观的再现,客居桂林之后,端木蕻良笔下的自然景观转变为柔和秀丽,他的整体小说风格也由刚健变为阴柔。同样是以关内文化与生活为背景的《风陵渡》和《江南风景》,小说中的阴柔特征却不明显。
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期间的小说风格变化,与他所采用意象的变化存在明显联系,而这则受桂林自然景观的影响。端木蕻良小说风格的改变与题材等的变化密切相连,是桂林文学生态多元化的间接结果,这一现象与桂林的自然景观存在更直接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危机意识唤起了中国作家的土地意识,土地意象开始大范围地出现在中国文学之中。土地意象在端木蕻良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中占比极大,黑土地孕育的生命力是端木蕻良笔下农民的精神力量源泉。客居桂林时期,端木蕻良小说中的土地意象几乎消失,代之以与水有关的河流、湖泊、海洋等意象。同时,山意象也频繁出现在小说中。“山崖下面是垂杨柳树林,沿着山脚像四月里过黄色的麦田……一道燕翎水在流沙上缓缓地流过。”[12]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期间住在三多路,现属桂林市秀峰区,这里山水相依。在无意识间,端木蕻良将对桂林山水的感觉投射在其文学作品中。初登文坛之时的雄浑刚健气息逐渐减弱,蕴藏在他气质中的柔弱纤细成分被桂林的山水气质充分激发。
“许多朋友因为不适合于雨季的潮湿气候,纷纷地离开去了。”[14]司马文森回忆客居桂林的往事时,提及不少文人因为无法适应气候潮湿的桂林,选择离开。对东北作家而言,开阔明朗的东北平原与潮湿的桂林山水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异,他们不自觉地对比两者,出于对故乡的眷念,桂林异于故土的气候成为他们作品中重要的象征元素。
在骆宾基的笔下,潮湿环境增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李辉英的《神父之死》开篇就用久雨烘托沉郁骇人的气氛,善良的神父出现之时则风和日丽。桂林雨季的阴冷潮湿加重了端木蕻良的感伤、痛苦与思乡之情,原本是生命之源的水在部分小说中成为罪恶与毁灭的象征。《海港》中,幽深的水加重了阴森氛围;《红灯》中,山东人无法进入东北,只能在海上漂泊,最终被海水吞没;《步飞烟》几次出现水的意象,从象征欲望之水到成为将死之人的渴求,水在小说中指向贪念与死亡。
三、端木蕻良小说创作转变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端木蕻良先后客居上海、武汉、重庆、香港与桂林,日复一日的漂泊消磨了他早期昂扬的斗志。关内文化的长期浸润,使端木蕻良小说原有的关外特色变得模糊朦胧。《早春》中,东北大地的野性被南方的温和空灵底蕴覆盖,东北的空气变得“空漉漉的,空得好像有声音藏在里面”[11]。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漂泊、与漂泊相伴而生的孤独感加重了其作品的感伤色彩,形成挥之不去的苍凉底色。不少学者从文学的社会功用角度指出,端木蕻良客居桂林期间一味沉浸于哀伤,忘掉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作品缺失了现实意义。然而,结合当时桂林的实际情况,端木蕻良并没有变得完全消极,他此时期的创作也呈现出别样的价值。
端木蕻良于1942年春季离开香港抵达桂林,尽管当时桂林的文化艺术已经比较繁荣,但并不似表面风平浪静。《文艺生活》1942年初发表了文章《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这篇文章是田汉、邵荃麟、艾芜等人的座谈会记录。文章指出,虽然1941年桂林的各项文艺活动仍然在进行,但相较于1940年,面临了政治形势、商业文化入侵等多种问题,盗版现象猖獗。桂林文艺界为应对危机,采取了开办专栏、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措施。端木蕻良在受到桂林多元化文化生态影响的同时,其作品又促进了桂林文艺的多元化。端木蕻良抵达桂林初期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迅速参与到桂林的文艺建设中。他积极参与桂林文协分会的活动,并当选第4届候补理事。端木蕻良以其小说创作融入桂林文坛,增强了抵制市侩主义文学观的力量。
端木蕻良生长于东北,东北文化基因并不会因为其漂泊他乡而被遗忘。“地域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15],原生地域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品性、审美等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存在于端木蕻良小说叙事习惯中的东北文化渗透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并不时地发挥主体作用。
《科尔沁旗草原》写求雨场景以及丁老先生跳神治病的故事,《大地的海》描写了萨满跳神场面和神松的故事,《大江》则着重刻画了全村民众都喜欢看九姑娘跳大神。客居桂林期间,他有意识地去挖掘桂林本地的民俗文化。他客居桂林时期的部分作品,体现出东北意识与以桂林为代表的广西地域文化的融合。在东北神奇的土地上,充斥着“追求自由与漂泊的鸟图腾精神”[16]。《雕鹗堡》的故事发生地是南方色彩鲜明的小山村,当地以鸟为神,化用了中国东北的鸟图腾崇拜文化。
《红夜》根据广西民间传说改编,故事发生在桂林阳朔的芙蓉峰山脚下。小说情节沿着两条叙事线索发展,通过明线暗线并行的方式塑造爱情悲剧。明线是婆婆与草姑,由婆婆给草姑讲石人传说展开,接着叙述草姑去看跳神途中的事件,以及跳神当时的事情。暗线是姐姐与龙宝的来往,小说并没有直接刻画。姐姐与龙宝的爱情通过草姑的回忆慢慢展现,并最终通过跳神的场景完全呈现。姐姐与龙宝在跳神的地方谈情说爱被发现,两人的行为被视为渎神,影射神权对人性的压抑。与满族类似,壮族也有自己的神职人员,主要负责沟通人神两界[17]。端木蕻良在写跳神之时,将场景设置在山洞,融入了广西地域色彩,突出了山洞阴暗环境造成的诡秘气氛。与之前的文化态度一致,端木蕻良尊重地域的文化习俗,同时指出习俗的不合理之处。自然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不同区域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不同,又直接创造了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俗与伦理道德等精神层面的内容。端木蕻良以东北式的民族文化意识挖掘广西的民族文化底蕴,为其他作家提供了借鉴,扩展了桂林文坛的小说创作题材。
四、结语
东北作家、“左联”成员、乡土写作、抗战文学等是阐释端木蕻良的经典视角,单独研究1942—1944年其客居桂林时期作品的文章极少。实际上,客居桂林时期的经历对端木蕻良而言至关重要。端木蕻良1942年春天刚抵达桂林之时,内心极度压抑。在桂林时,端木蕻良结识了柳亚子、陈迩东、陈芦荻、王鲁彦等人,慢慢通过新的人际关系抚平内心的伤痛。在桂林,多元化的文学生态为他提供了通过创作小说解脱自我的空间,他通过小说创作,平衡了自我与现实,实现了精神解脱。桂林不同于东北的自然景观和地域文化,则为端木蕻良提供了全新的写作素材。如果没有桂林在抗战时期独特的人文环境与它独特的自然环境,端木蕻良很难实现创作转变。同时,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转变又丰富了当时桂林文坛的文学格调。研究1942—1944年客居桂林时期的端木蕻良,对从整体上认识端木蕻良,理解他的人生选择、精神空间和文学道路,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云.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 凤子.复刊词[J].人世间,1947(1).
[3] 张文学,黎明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N].人民日报,1995-09-27.
[4] 林焕平.《桂林文化城大全》总序[M]//雷锐.桂林文化城大全·文学卷·小说分卷(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 王富仁.端木蕻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6]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J].万象,1944(5).
[7] 端木蕻良.蝴蝶梦[M]//端木蕻良文集(3).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 叶舒宪.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M]//文学与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 孔海立.端木蕻良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10] 端木蕻良.《红拂传》前前后后[M]//端木蕻良文集(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11] 端木蕻良.早春[M]//端木蕻良文集(3).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2] 端木蕻良.雕鹗堡[M]//端木蕻良文集(3).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 端木蕻良.致鲁迅[M]//端木蕻良文集(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14] 司马文森.《雨季》后记[M]//杨益群,司马小莘,陈乃刚.司马文森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15] 刘勇.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J].当代文坛,2024(2).
[16]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17] 黄桂秋.壮族社会民间信仰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兰宏君,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