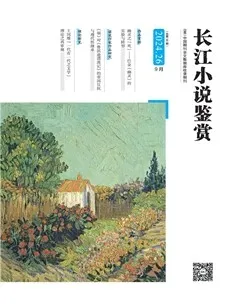论《玉米人》中狂欢化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
[摘 要] 《玉米人》是危地马拉文学巨匠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创作的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塑造出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本文主要分析小说中呈现出狂欢化特质的人物形象,帮助读者理解其蕴含的自由生命意识所带来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 《玉米人》 狂欢化人物 具体感性 自由生命意识
《玉米人》是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斯图里亚斯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印第安人经历的社会变迁,主要讲述了以传统农耕神话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明与以商品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现有研究基本围绕着《玉米人》中展现的魔幻现实世界观进行讨论,缺乏对书中人物形象的解读。本文着重分析书中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表现,从而解读具有狂欢化色彩的人物所表现出的具体感性,以及富有自由生命意识的人物的审美价值特征。
一、狂欢化人物具体感性的审美价值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基于中世纪的官方节日——狂欢节所建构的文学理论,巴赫金在他的狂欢化理论中提出了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概念,用于归纳总结古典主义时期以后民间诙谐文化的审美特征。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列举三类民间诙谐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其一,各种仪式(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诙谐的广场表演);其二,诙谐的语言作品(戏仿体作品)、口头作品、各民族语言作品;其三,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褒贬诗)[1]。从这三类表现形式孕育出了怪诞现实的人物形象的审美特性。
狂欢化人物基于民间诙谐文化的基本表现形式生成,人物形象在狂欢节的节庆活动中出现并十分活跃,以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为语言特征。“人民的这个节日组织首先是深刻的、具体的、感性的。甚至拥挤本身,肉体最物质性的接触,也获得了某种意义。个体感受到自己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巨大的人民肉体的成员。在这个整体中,个别肉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是自身了:仿佛可以相互交换肉体、更新(化妆、戴假面具)。就在这个时间里,人民感觉到了自身具体感性的物质——肉体的统一与共性。”[1]《玉米人》中的人物形象从筵席形象、外貌以及语言的表现三个层面体现出具体感性的审美价值。
1.筵席形象的具体感性
狂欢节的筵席和庆典活动在《玉米人》中呈现为印第安人的篝火晚宴、圣烛节及朝圣会,生动地展现了危地马拉人的风俗习惯。在宴会和节庆期间,在自由祥和的氛围中,人们尽情陶醉于无拘束的欢愉中。篝火晚宴上,所有人齐聚一堂,畅饮着奇恰酒(用玉米发酵制成的酒),品尝着各种以玉米为原材料制作的菜肴。这场宏大的聚餐充满夸张、喧嚣,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完美呼应了作品主题:“人是玉米做的。”[2]
在圣烛节,戴着面具的游行队伍穿行于喧闹的街市。队伍中,一位装扮成“国王”的狂欢化人物显露出“小丑”的形象,他的头上插着五彩缤纷的羽毛,嘴唇涂成银白色,眼皮涂成金黄色。狂欢化人物的诙谐形象在节庆场景中得以呈现,而队伍中的怪异对话则展现了“傻子”的人物特色。在爆竹、钟声交织的热烈氛围中,戈约·伊克与多明哥·雷沃罗里奥原本计划通过卖酒赚钱,结果却变成相互倒卖酒,最终他们将一坛酒喝光。即便在法庭上被审问,他们仍然沉醉在酒钱被盗的错觉中。这一怪诞而离奇的对话在欢快的节庆氛围中逐渐展现出狂欢化理论中“傻子”形象的特质。
狂欢化人物中的“小丑”和“傻瓜”是中世纪诙谐文化中的典型形象,具有明显的怪诞现实主义审美价值。怪诞现实主义的审美观与古典主义时期的审美观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一种欢愉和安宁的氛围。在狂欢的节庆里,以戈约·伊克与多明哥·雷沃罗里奥之间因过量饮酒而展开的断断续续的荒诞对话中,人物形象的夸张特质是为摆脱日常的礼仪规范所形成的[3]。
从饮食角度看,筵席中表现出的具体感性特质同样显著。由于中美洲印第安人以玉米为主食,根据《波波尔·乌》的记载,造物神曾用泥土、木头尝试制作人类,但最终用玉米成功创造了人。因此,《玉米人》围绕着“人是玉米做的”这一传说描写了许多玉米主题的筵席,饮食成为离奇怪诞肉体生命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从篝火晚宴的玉米筵席到朝圣会的玉米摊位,各种人物与用玉米做的食物在筵席中的联结呈现出欢愉的画面。在朝圣会上,神坛上摆满了鲜果、嫩玉米穗和烧酒,“咕嘟嘟……咕嘟嘟……他们把烧酒灌进了喉咙”[2]。人物在这个过程中与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筵席的形象直接而具体,在放纵与欢愉中展示着他们感性的狂欢激情。
2.外貌描写的具体感性
小说描写的人物中,托马斯·马丘洪具有明显的“傻子”特征。他因儿子的死而精神错乱,故而与豁嘴儿在地里看稻草人的时候,他先是对着地里稻草人一个劲地傻笑,然后又称稻草人是地里的犹大,问戴草帽的人叫什么名字。在遭到豁嘴儿的嘲讽讥笑后,作者具体描述了马丘洪的样貌:“老头子可怜巴巴的,一吸气两颊便瘪了下去,因为哭得太多,两颊被泪水腌得厉害。牙掉光了,只剩下牙床子抱着牙根儿。逢上生气或者难过的时候,嘴巴里的肉就贴在牙床上。”[2]这段对马丘洪的外貌描写充满着怪诞美,具体地描绘他的牙床,显露出他可怜的姿态。阿斯图里亚斯通过对人物形象、外貌细致入微地描写,将荒诞现实的美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使狂欢化人物拥有具体感性的审美价值。
具有夸张性怪诞外貌的人物形象以印第安人部落酋长加斯巴尔·伊龙为典型代表,阿斯图里亚斯是这样描述加斯巴尔的形象的:“加斯巴尔的皮肤跟大山榄的硬壳一样结实,他的血液像黄金一样金贵。他力大无穷,跳起舞来威武雄壮。他笑起来,牙齿好似泡沫岩;咬牙、啃东西的时候,牙齿好似燧石。他有几颗心。牙齿是嘴里的心,脚跟是脚上的心。”[2]作者采用夸张的外貌描述伊龙,是为了强调其在当地印第安人心中的地位,“怪诞现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1]。倘若作者试图表现人物精神层面崇高的地位,就要具体到强壮的肉体、超越平凡人的力量上。
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描写加斯巴尔·伊龙,描写他的强壮身体、饮食、排泄、性生活,凸显其英勇的酋长形象。而后作者在叙述伊龙喝了百草根毒酒时,也细致地描写了毒酒给他身体带来的折磨:“他面色苍白,龇牙咧嘴,砰的一声跌倒在地上,两只脚乱蹬乱踹。只见他口吐白沫,舌头泛紫,两眼发直,手指变得和月亮一样惨黄,指甲几乎变成青色。”[2]在对其饱受折磨的外貌进行描写之后,作者又描写了怪诞的人体内发生的变化:“他饱饮一顿河水,消解了毒药在腹内引起的干渴。把五脏、血液痛快地冲洗了一遍,从死神的魔掌中挣脱出来。”[2]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特别强调了内脏形象的作用,五脏六腑与人的生命状态有关。
作者对酋长怪诞的外部形象与怪诞的体内变化的描写体现了其在精神层面的对抗,他是反抗精神的化身,毒药无法杀死他,河水无法淹死他。他在中毒以后饱饮河水便超越了死亡,夸张地体现了怪诞形象中生命开端和终结的交织,对死亡的消解使加斯巴尔·伊龙成为英勇无畏的超越性形象,阿斯图里亚斯用加斯巴尔·伊龙死而复生的魔幻情节表现了印第安人对殖民者迫害的抵抗。在书写伊龙大地时,作者也同样使用了狂欢化的方式:“是啊,大地是个巨大的乳头,是个硕大无朋的乳房。”[2]这种写作方式将加斯巴尔·伊龙与伊龙大地紧紧联结在一起,展露出印第安人与土地的紧密相连、肌肤相亲。
3.语言描写的具体感性
语言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语言能够具体展现出人物的性情与思想感情。阿斯图里亚斯以大篇幅的直白语言来体现人物形象。玛丽娅·特贡是戈约·伊克的妻子,她带着两个孩子独自逃走以后,戈约边寻找边崩溃大哭,显示出狂欢节中“疯子”的角色特性。而戈约在大喊大叫时,不住地咒骂他的妻子,骂她“驴粪球”“像不会动弹的四脚蛇”“臭母猪”[2],称自己为“废物鸡”。戈约试图以医治眼睛重获光明的方式找寻妻子时,他因疼痛难忍不住地咒骂,这几处对语言的使用都显露出阿斯图里亚斯在设计角色语言时的狂欢化与荒诞不经,骂人的话语既有贬低扼杀的意味,又象征着再生和更新。戈约·伊克在咒骂中接纳妻子的离去这一事实,在咒骂中忍耐医治眼球时的疼痛,最终重见光明。
辱骂既表达憎怨又表达爱意,作者笔下的怪诞形象使用无所畏惧的、洒脱不羁和坦率直白的语言,突破了语言的禁忌、限制。这样具体且感性的语言审美给读者带来直接的震撼,引发独特快感。
二、狂欢化人物自由生命意识的审美价值
狂欢化的人物形象不是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而是现实的、生活化的。狂欢节的参与主体是人,在狂欢化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普通人的缩影,显露出来的自由生命意识代表着大众的意志。《玉米人》中的人物处在狂欢与释放的过程时,自由生命意识的审美特征体现在脱冕形象与双体性的怪诞形象。
1.脱冕形象的自由生命意识
脱冕作为揭示旧权力、垂死世界真相的象征,与狂欢化的殴打、改扮以及滑稽改编巧妙结合。狂欢节仪式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是国王的加冕与脱冕仪式,在描绘印第安人村庄淘金事件时,作者特别细致地刻画了西班牙人堂·卡苏亚利东的形象,他成为狂欢节中受封加冕然后被脱冕的国王。起初,堂·卡苏亚利东出于自身贪婪的欲望而上任为当地村庄的大主教,却出人意料地被神父谬赞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人,这是他受封加冕的瞬间。然而,当他踏入印第安人的世界时,情势发生了逆转,他因周遭环境的改变与印第安人对待他冷漠的态度而倍感寂寞。很快,他观察到印第安人对待金子的轻蔑态度。印第安人认为黄金可能导致人类毁灭,厌恶那些剥削他们的刽子手,将金子视为腐化之源。他们将黄金送往城市,认为这一行为是将邪恶送到了城市。堂·卡苏亚利东最终被这种天然纯粹的世界观所打动,将马嚼子交还给神父时,滑稽地宣称自己只配做头牲畜。他脱下了自身一直披着的虚伪外衣,承认贪欲是他一切问题的源头,实现了思想意识上的脱冕。堂·卡苏亚利东作为一位被加冕又被脱冕的国王,摆脱了刻板的教条和规范,展现出自由生命意识的变化过程。
加冕、脱冕这一仪式化的过程,是民间文化对权威化思维的解构,揭露了堂·卡苏亚利东虚伪的面貌,体现印第安人民众所代表的颠覆性自由生命意识的思想。这样新旧更迭的过程摆脱了规则和等级的束缚。究其根本,狂欢化理论的内在意义其实是辞旧迎新的积极更迭,强调的核心是人与人的自由与平等。帕姆·莫里斯认为,“狂欢化是巴赫金最有影响的概念,仅次于对话理论,它可被视为巴赫金用来反抗一元世界中心化强制的另一个具有社会离心力的术语。”巴赫金建构的狂欢化的概念,是为了将各种不同的宇宙观、各种性格迥异的人群汇总在一起,消除隔膜。民间怪诞中疯癫是对官方智慧、真理的欢快戏仿,狂欢化人物自由生命意识的审美价值在这样一种乌托邦世界得以表现出来。正如书中戈约·伊克与多明哥·雷沃罗里奥在喝酒时表述的那样:“酒一下肚就不分什么你大方,我小气;你有钱,我是穷光蛋。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酒杯一端,大家彼此彼此,人就是人。”[2]《玉米人》中,狂欢化人物的对话多次体现出自由生命意识的审美价值倾向,否定绝对性的权威,建构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的氛围。作者运用怪诞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危地马拉土著印第安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观察世界的方法,同时赋予了印第安人非中心思想的自由探讨空间。
2.双体性怪诞的自由生命意识
双体性怪诞融合了两个物种或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元素,代表着人与自然的众生平等。狂欢化人物形象中的双体性怪诞体现在书中的“纳华尔主义”中。根据印第安人的传统,纳华尔是当地人从出生起就有的动物保护神。小说中描述了纳华尔可以同人的灵魂、肉体自由转化,呈现出人与动物同体的狂欢化怪诞形象。巫医库兰德罗变成的动物是七戒梅花鹿,邮差尼丘先生变成的动物是一只野狼。人与动物之间的自然转换、一体双身性的怪诞形象,象征着印第安人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观,作为一种令当地人向往的神迹深深地根植于印第安人的心中。双体性怪诞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临界点,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模糊化,同时也是这部作品对抗理性思维权威的表现。“怪诞形象所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对时间、对形成的态度是怪诞形象必然的、确定的(起决定作用的)特征。它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必然特征是双重性:怪诞形象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体现(或显示)变化的两极即旧与新、垂死与新生、变形的始与末。”[1]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最易忽略的核心思想是重获新生,毁灭、死亡、荒诞的外壳如果脱离新生来进行讨论便失去了意义[4]。
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中,巫医库兰德罗之所以由人转换成七戒梅花鹿而后被高登修·特贡开枪打死,是因为他在死前一直强调娅卡老太太的蛐蛐病和卡利斯特罗的疯病必须用鹿眼石才能治愈。库兰德罗以荒诞性的死亡治愈了娅卡老太太的蛐蛐病和卡利斯特罗的疯病,带来了特贡家族的希望。邮差尼丘·阿吉诺转换成野狼也经过了曲折的心路历程,他在妻子特贡娜(《玉米人》中,“特贡娜”特指遗弃丈夫独自逃走的妻子)出逃以后一直郁郁寡欢,在寻找妻子踪迹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野狼的模样,无法重新变回人类。尼丘先生在萤火大法师与梅花鹿库兰德罗的引导下,明白了特贡娜事件的始末,摆脱了自己执念所带来的痛苦。随着萤火法师烧毁他送往邮政总局的信件,他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最终跑到了沿海地区小村庄的国王饭店,在店里做帮工。怪诞的双重意义在于死亡与新生,由人转向纳华尔,由走投无路的毁灭转向熠熠生辉的新生。阿斯图里亚斯凭借库兰德罗-梅花鹿与野狼-邮差的视角解开了所有事件的谜题。“此时此刻,他的人形正在海上航行。如果他们不说话,库兰德罗-梅花鹿就会化作一团白雾,而野狼—邮差就会失去兽形,完全恢复人形,和玛丽娅·特贡一起在大海上航行。”[2]他们在大雾弥漫的玛丽娅·特贡峰上行走,这神迹般的诅咒寓示着库兰德罗原本已经死亡,故而他不说话就会化作一团白雾;野狼原本是人,他不说话就会消失在湛蓝的大海中。
不论是库兰德罗还是尼丘·阿吉诺,都显示出双体性怪诞的人物形象。与现代人体规范的单一性不同,双体性怪诞的人物死亡似乎与再生浑然一体。在怪诞人体中,死亡不会使任何事物终结。怪诞人体的转变总是在一个人体转变之间的交界处发生,库兰德罗交出自己的死亡,七戒梅花鹿让出自己的诞生;邮差交出自己的死亡,野狼让出自己的诞生,他们融合在一个一体双身的形象中,“人兽合一”的纳华尔主义表现出自由生命意识的审美价值,展现出印第安人自由且蓬勃的生命力。
三、结语
《玉米人》中的傻子、疯子、国王、筵席场景、夸张性怪诞、双体性怪诞等狂欢化人物形象不仅具备具体感性的审美特征,而且蕴含着深厚的自由生命觉悟。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展现出鲜明的个性与魅力,充溢着荒诞现实所独有的审美价值。狂欢化思想以诙谐文化为代表,化解了崇高,抵御了大众面对压迫力量时的惊惧,使人们从怪诞、诙谐中获得信仰,勇敢地对抗来自权威的压迫。《玉米人》中,印第安人以古老魔幻的力量直面骑警队殖民者的野蛮压迫。狂欢化文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消解权威的崇高性,《玉米人》中体现为以狂欢化人物来抵制和消解理性思维的绝对权威[5]。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M].刘习良,笋季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
[3] 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姚珍珍.从建构到生成: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思想特质探析[J].戏剧之家,2020(11).
[5] 高尚.神奇的现实与修辞——关于阿斯图里亚斯及其长篇《玉米人》[J].世界文学,1994(3).
(责任编辑 陆晓璇)
作者简介:刘蔷,云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