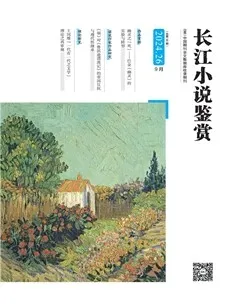浅析安吉拉·卡特《马戏团之夜》的狂欢化写作
[摘 要] 本文运用俄国学者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马戏团之夜》进行文本分析。以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参考,文学的狂欢化写作是将民间活动的狂欢式精神实质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独特形式,并具有“讽刺性描摹”“二重性本质”和“亲昵的接触”“俯就”“插科打诨”“粗鄙”这些特征。本文着重关注《马戏团之夜》的狂欢化写作,从伦敦妓院、圣彼得堡马戏团以及西伯利亚荒原这三个物理空间所展现的文学狂欢化世界着手,探究其以荒诞不经的情节、颠覆性的角色塑造和深刻的主题实现的狂欢式文学创作。狂欢化写作与现代荒诞文学具有紧密的互证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独特的表达形式和社会文化批判工具,尤其是在社会文化批判、文学手段、语言实验和哲学探讨等方面。
[关键词] 安吉拉·卡特 《马戏团之夜》 巴赫金 狂欢化写作 现代荒诞文学
一、文学的狂欢化写作
1.文学的狂欢理论及其表现
狂欢理论由俄国学者巴赫金开创,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研究》中不仅系统地介绍、对比了文学的“狂欢化”与现实民间活动的“狂欢式”的区别,还分析了狂欢活动中多种仪式和形象的二重性。同时,他以“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为重点剖析了庄谐体范畴的狂欢化,并借助塞万提斯和拉伯雷的作品阐述与论证狂欢在文学中的实践,深入探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营造的狂欢节式的大型复调对话小说。
1.1狂欢书写:民间活动的“狂欢式”与文学的“狂欢化”
狂欢书写是一种文学创作实践,它汲取民间狂欢活动的精神实质,将其独特的形式、情感、节奏和意蕴转化为文字,以此反映和再现那些超越日常生活的瞬间。一方面,狂欢书写是对狂欢场景的记录,传承了民间狂欢中一切庆贺、礼仪、形式的总和,构成了“狂欢式”;另一方面,它是对狂欢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再现,“狂欢式”的转向催生了文学的“狂欢化”。
狂欢书写的核心在于“狂欢式”的实践与体验。“狂欢式”并非文学现象,而是一种仪式性的混合游艺形式,涵盖了民间狂欢活动之精神实质,包括从复杂的大型群众性庆典到个别的小型宴会表演等所有的狂欢[1]。与由社会等级、教条和规则所主导的社会现实生活截然相反,民间狂欢以娱乐为第一原则,构建了一个反现实、反教会、反约束的自由世界。所有人都自愿地观看和参与狂欢,不仅以广场上“随便而亲昵的接触”解构了生活中的种种秩序、限制与禁令,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插科打诨、半现实半游戏的新型关系,并以冒渎不敬的姿态模仿和讥讽崇高与神圣的事物。
同时,狂欢书写也包括文学的“狂欢化”。巴赫金认为,“狂欢式”是一整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之“语言”,不仅能呈现不同时代和民族的所有狂欢形式,还凝聚了统一的狂欢节世界观[1]。该世界观可以通过“狂欢式”之抽象感性语言转化到文学语言,从而实现文学范畴的“狂欢化”。生活在狂欢之中的人们过着“反面的生活”,因而文学便遵循此种狂欢的规律呈现出这种“反面的生活”,一切被狂欢民俗和狂欢文艺活动所影响的文学都可以被称为“狂欢化”文学。
1.2文学史中的“狂欢化”传统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狂欢节的民间文艺直接影响了古代风雅戏剧以及庄谐体,例如索夫龙的歌舞剧、苏格拉底的对话、梅尼普的讽刺文学,可见文学的“狂欢化”在那时已然发端;中世纪时期,在民族传统相关的狂欢性庆典的影响下,又出现了大量由民间语言和拉丁语所著的诙谐文学和讽刺性模拟文学,以警示剧、神秘剧、讽刺闹剧所构建的戏剧游艺生活突破了中世纪严苛的社会秩序。这种潮流在文艺复兴时期则达到顶峰,宫廷节日的假面文化形成,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其二重性质、自由的语言等席卷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典型代表有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以那个时代人道主义者的视角重述了古希腊罗马的“狂欢化”理念;17世纪以后,民间狂欢生活衰落,“狂欢化”的文学最终将其取而代之,此时,“狂欢化”已经变成了文学体裁的一种传统。
安吉拉卡特的《马戏团之夜》无疑是对“狂欢化”文学的传承和发展。作者安吉拉·卡特通过荒诞不经的情节、颠覆性的角色塑造以及深刻的主题探索,将狂欢精神融入文学创作,挑战并重塑了人们对文学的认知。本文将依据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连贯地探讨作品中三个物理空间——伦敦的妓院、圣彼得堡的马戏团、西伯利亚的荒原——所展现的狂欢化元素。这些空间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狂欢化世界,揭示了文学中狂欢化写作的独特魅力。
2.文学批评范畴的狂欢理论
2.1四大基本范畴
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有四个特殊的基本范畴,分别是“亲昵的接触”“怪癖的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
首先,“亲昵的接触”直接拉近了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将人们从日常的规范和禁令等事务中彻底解放出来。根据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观点,在该过程中首先被取消的就是社会等级结构及其产物——因社会地位高低或年龄差异导致的所有形态和现象,例如恐惧、敬畏、礼貌等。于是,身处狂欢的人群彻底摒弃了日常中等级秩序的约束,在狂欢广场中以惊人的自由和坦率发生随便而亲昵的接触。
其次,从非狂欢式的普通生活的逻辑来看,从秩序结构中被解放出来的人们,其作为人的本质的潜在方面得以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被揭示和表现出来,即“插科打诨”,表现为怪癖而不得体的行为、姿态和语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既定的严肃形式转向偏游戏的娱乐形式。
比“插科打诨”更甚的是狂欢式的另一范畴“粗鄙”。“粗鄙”彻底地把狂欢式的荒诞不经和冒渎发挥到极致,人们不仅对神圣、崇高的事物进行模仿和讥讽,还会使用与人体生殖能力相关的污言秽语,呈现为最大限度降低格调的做法。
同时,与“亲昵的接触”相关的还有“俯就”这一范畴。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等级结构的消弭决定了任何其他的观念会颠覆过去肯定或否定事物的判断,并将事物的两极由对立推向统一——“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一切融为一体。
狂欢式的四大范畴塑造了文学狂欢化的相应属性:“亲昵的接触”在文学中主要体现为所描绘的内容呈亲昵化的趋势,即史诗与悲剧的距离缩短,主人公由绝对的崇高地位被降格为可接近的、富有人性的人,而作者亦对人物采取亲昵态度;“插科打诨”的新型人际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催生了等级秩序瓦解的元素,尤其体现为人际交往方面的实践;而“粗鄙”非常直观地表现为语言风格的大幅降格和所描写对象去崇高化,作者以极其戏谑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俯就”则与狂欢化书写中二重性本质紧密关联,呈现为对立相斥事物的诡谲融合、不分彼此,将狂欢的颠覆性特质贯彻到底。
2.2狂欢式形象的二重性本质
狂欢化的文学继承和运用了现实民间活动中许多狂欢式的形象,这类形象所具有的二重性本质也已经成为狂欢化文学的重要特征。在狂欢式中,一切的形象都是合二而一的,相反或相斥的事物往往成对出现并互相转化,例如死亡与新生、丑恶与美丽、愚昧与智慧,又或是“裤子套到头上,器具当头饰,家庭炊具当作武器”等,这是狂欢式形象反常规、反日常的典型表现,即利用破坏性策略颠覆原有世界观的二元逻辑,建立挑战传统秩序的新准则[1]。
加冕与脱冕就是最能代表狂欢式形象二重性特征的例子之一。一方面,加冕与脱冕的对象具有二重性。在现实生活中,加冕的对象本是王室贵族,然而,民间的狂欢盛典却将乞丐、奴隶之类的人物加冕为王。而脱冕时,人们又会剥下受冕者的王冠和服饰并讥笑、殴打他,让他从高贵的国王重新跌落到尘土中,成为万人唾弃的丑角。丑角与国王的地位天差地别,但在狂欢的世界中,任何制度、秩序、权力都具有相对性,所以丑角等同于国王、国王等同于丑角。同时,人们还会使用专门的道具和仪式来完成狂欢盛典中的加冕,使受冕者在狂欢的世界中似乎无限接近于真正的国王,而在脱冕中又通过剥去他的服饰和王冠实现对权力秩序的践踏和抛弃。因而,加冕既是高贵的册封,又是卑鄙戏谑的娱乐;脱冕既是颓唐消沉的悲剧,又是狂喜狂热的欢庆。另一方面,加冕和脱冕是合二为一、互相转化的双重仪式,加冕本身就蕴含着之后脱冕的含义,而脱冕又预示着下一次的加冕,表现出新旧交替的必然性。更深入地说,包括加冕与脱冕在内的所有狂欢式的象征物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否定的前景,或者相反。所以,加冕与脱冕时常被运用到文学之中。
除此以外,狂欢节上火的形象也具有深刻的二重性本质,它既代表毁灭世界,又代表世界的更新与新生。首先,在狂欢节结束时,一辆名为“地狱”的车会被焚毁。焚毁车子的行为直观地体现了毁灭的意象,它象征着旧秩序、旧观念的终结,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一种象征性破坏;同时,焚毁车子也意味着重生和更新,在狂欢的世界中,火被视为净化和转变的元素,焚毁旧物可以为新事物的诞生腾出空间,象征着从灰烬中重生的希望和机遇。其次,参加狂欢节的每个人都会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一边保护自己的蜡烛,一边尽力去吹熄他人的蜡烛,这种行为是直面生命无常、注定终结的命运的行为,既通过模拟死亡来弱化对死亡的恐惧,又提醒人们生命的脆弱和宝贵。当然,蜡烛的燃烧也可以看作是新生的象征,因为在一些人蜡烛被吹熄的同时,其他人手中的蜡烛仍然在燃烧,这便是毁灭与新生的共存。
另一个要提及的则是狂欢节的“笑”。狂欢的笑声一直是边缘的、非官方的,为批判官方的严肃性提供了新的不同视角,因其潜在的怪异性可在狂欢中发挥批判作用[2]。而笑的二重性本质体现为:笑涉及了交替的双方,也涉及秩序交替的过程,在取笑严肃事物的同时把被现实排斥的事物带到核心地位,正符合狂欢力图贬低高尚的东西并提升低下的事物的目的[1]。在狂欢节的笑声里,有死亡与再生的结合,否定(讥笑)与肯定(欢呼之笑)的结合——这是深刻反映着世界观的笑,是无所不包的笑,是打破传统的二元逻辑的笑。
2.3讽刺性模拟
与狂欢节的“笑”相关的是讽刺性模拟,它也是狂欢式的本质之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根据巴赫金的理论,讽刺性的模拟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意味着那个“翻了个的世界”[1]。
文学中的讽刺性模拟通过模仿和夸张的方式来嘲笑或批评某个对象、观念或社会现象。它不仅通过模仿来揭示被模仿对象的缺陷和矛盾,还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现,以夸张和扭曲的形式来揭示被模仿对象的荒谬性。具体而言,讽刺性模拟常常塑造一个与被模仿对象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形象,即讽刺性模拟型的同貌相似者,这种形象往往被剥夺了其原有的权威或尊严——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主人公,都有几个相似者,他们以不同方式模拟这个重要的主人公,在他们(指同貌相似者)身上,重要的主人公都临近死亡(指遭到否定),目的是获得新生(指变得纯洁而超越自己)[1];又或者作者创造一个颠倒的世界,即“翻了个的世界”,其中常规的秩序和价值被颠覆,从而揭示现实世界中的不合理性。
除此以外,讽刺性模拟的形式和程度可以非常不同,它可以是温和的戏谑,也可以是尖锐的讽刺,还可以从各种对立的、变形的角度作出模拟,具有荒诞的性质。
二、《马戏团之夜》狂欢化写作
《马戏团之夜》中,卡特精心构建了多个核心的狂欢空间,不仅丰富了叙事层次,也映射了多元的社会文化现象。具体而言,伦敦纳尔逊嬷嬷的妓院作为女主角飞飞的成长摇篮,是其身份认同和人生轨迹的重要起点。圣彼得堡的马戏团汇聚了各式奇幻的杂耍、魔术与动物表演,动物与人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生态。西伯利亚的女子监狱这一空间,则是弑夫但免受刑罚的伯爵夫人监视其他女性罪犯的忏悔之地,法律与道德、惩罚与救赎之间表现出强烈的张力。而西伯利亚荒原深处则是神秘的萨满教驻地,部落成员们延续着萨满教的信仰,将梦境视为现实的一部分,构建了一个独特且自成体系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了对现代文明的背离与反思。
1.伦敦纳尔逊嬷嬷的妓院:逆反的圣殿
纳尔逊嬷嬷的妓院正是讽刺性模拟理论中“翻了个的世界”的体现,以彻底对立、颠覆的形式创造性再现了被模仿对象——教堂或高档俱乐部等正派场所的荒谬性,实现了对妓院本身的彻底狂欢化。同时,妓院的焚毁也反映了狂欢式中“火”这一形象的二重性本质及意义,展现了妓院旧世界、旧秩序毁灭与诸位女性走向新人生的重生。
1.1建筑与人物的讽刺性模拟
首先,庄重典雅的建筑形态和妓院的空间功能的对比构成了一种荒谬的讽刺,颠覆了人们对这种建筑风格的传统期待。那是一幢五层楼高、风格古典素净的英式四方形红砖房,大门上方是优雅的扇贝形气窗,门廊饰有比例适中的山花壁面;窗户开得很高,且白色百叶窗总是拉下的;内部有富丽堂皇的大理石楼梯和壁炉,还有深红色的天鹅绒窗帘与晶莹的水晶吊灯;每天桌上都摆着烫平的《泰晤士报》,客厅的墙面覆盖着酒红色的大马士革提花织锦壁布,上头挂着以神话故事为主题的油画,其中有品质极高的威尼斯画派作品。这座很有年头的古老房子,隐匿在雷克利夫公路后面。这种建筑风格通常与庄严、肃穆、正统价值观联系在一起,往往是教堂、学校或是正派人家所选用的建筑风格。然而,这座房子实际上是一家妓院,每天里面都进行着赤裸的皮肉交易。建筑的形态风格和空间功能呈现两个极端,这种割裂感与颠覆性正是以妓院讽刺性模拟庄严场所的荒谬性体现。
其次,妓院本身的内部运作、妓女与顾客的品行表现又呈现出对社会上流人士和精英人士的讽刺性模仿,呈现出一个一反常态、怪诞奇异的反妓院式的世界。纳尔逊嬷嬷的妓院被视作“高档的绅士吸烟室”“入会资格最严谨的绅士俱乐部”,妓女看似是虔诚高尚、最具有美德和善心的人,一位妓女便能说服三四十个常客皈依天主教;顾客被鼓励表现出优良的男性风度,甚至最好庄重到如丧考妣的程度;妓院的所有者纳尔逊嬷嬷精心挑选皮质的扶手椅,供顾客与妓女在这里进行哲理与人生的对话;闲暇之余,妓女要么练习长笛,要么学习速记,房子里只能听见抒情的乐声和打字机敲击的声音——这里弥漫着一股正直而守礼的气氛,所有的人都是优雅识礼的正派作风。
综上所述,小说对妓女的正面描述、对卖淫的非道德界定,都是对既定秩序与规范的狂欢化颠覆。妓院庄重典雅的建筑风格、里面发生了冠冕堂皇的皮肉交易破坏了公认的卖淫概念,也打破了社会中高尚和低下的传统二元逻辑,建立起了全新的、自由的女性主义世界。
1.2妓院的焚毁与新生:“火”的二重性
在纳尔逊嬷嬷意外死于车轮之下后,一切财产落入了她冷酷古板的牧师兄长手中,妓院将按照他的正义观念被改造成堕落少女的收容所,所有妓女都被迫立刻离开此地。飞飞和她的养母们以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即刻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纵火案,将这座房子彻底摧毁。
如前文所言,狂欢式中“火”的形象,既代表毁灭世界,又代表世界的更新与新生——妓院的焚毁体现了毁灭与新生的共存,旧的生活被毁灭,而新的生活正在被创造。一方面,妓女们用火焚毁房子的行为正是一场具有终结意义的火葬,既代表着妓院核心人物的死亡、充满集体情感与回忆之处的消逝,又意味着旧世界的终结和所有人的过去身份之消亡,这种行为还是对牧师所新建的收容所秩序结构的一种象征性破坏和彻底反抗。另一方面,她们通过焚毁房子创造了更新自我和创建新秩序的机会。烧毁妓院正如同狂欢节上烧毁名为“地狱”的车子。这种纵火的行为实际上是在对旧的生活方式、旧的社会角色的道别,对即将降临的新秩序说出狂欢式的蔑视誓言,是一种大胆的反抗行为,表达了对自由和自我决定权的渴望。不论是开设旅馆、做文书工作还是经营冰激凌店,分道扬镳、另谋他业的她们最终在烈焰的灰烬中勇敢地重生,重塑了人生的走向。
2.圣彼得堡的马戏团:诡谲的欢乐场
2.1“女飞人”飞飞:边缘笑声的力量
《马戏团之夜》这部作品的开头和结尾均为女主人公飞飞的大笑,她的笑声具有强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龙卷风一般席卷世界,以边缘、非官方的视角讥笑和贬低社会公众墨守成规的科学观念和道德体系,并肯定和升格被非议和不齿的性开放、人的动物性。通过狂欢式的大笑,她实现了人与鸟、处女与妓女的二元对立逻辑的挑战与颠覆,并对周围的他人起到了引领和启发的作用,让笑成为所有人的笑、无所不包的笑。
首先,飞飞的生理特征使她处于人类与鸟类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化的身份让她具有怪异性,不仅能为批判官方的严肃性提供新的视角,还能够通过幽默和讽刺来挑战和解构权威,使她成了一个能够引发“笑”的元素——这既可以被视为对传统人类形象的否定与讥笑,又肯定了多样性和边缘化的价值,传达了欢呼之笑,而这种否定与肯定的结合反映了狂欢理论中笑的二重性本质,体现了狂欢理论中无所不包的笑。
其次,飞飞的笑反映了发生秩序交替的双方与交替的过程。一方面,飞飞的大笑涉及了人类与非人类双方秩序交替的过程,在取笑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将通常被视为低下的鸟类特征提升到与人类同等的地位,即把被现实排斥的非人类存在带到了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她的大笑也表现了妓女与处女这对二元对立事物的秩序交替,飞飞得意地自称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羽翼丰满的处女”,打破了传统贞洁观念下处女与非处女之间的界限,并以杂糅矛盾的身份直接摒弃了物化和分类女性的观念, 将被人轻蔑的妓女身份提升到与受人肯定的、高尚的处女平等的地位。以上两种秩序的交替都与狂欢理论中的秩序交替过程呼应,也符合狂欢理论中贬低高尚的东西并提升低下的事物的目的。
综上所述,《马戏团之夜》中,女主角飞飞以她独特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不仅挑战了社会固有的科学观念和道德体系,更在人与鸟、处女与妓女的二元逻辑中实现了颠覆与重构。她的笑声,象征着边缘对中心的挑战、非官方对官方的讽刺,以及多样性与单一性的对话。通过飞飞这一角色,作品深刻探讨了狂欢理论中的笑的二重性,并揭示了秩序交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飞飞的笑,不仅是个人的狂欢,更是对社会秩序、道德束缚以及传统观念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2.2小丑巷的小丑:面具下的悲喜剧
小丑是最具有狂欢色彩的一类人物。小丑以其特有的滑稽形象与观众建立了一种非正式的、亲昵的接触,其表演又充满了插科打诨的元素。通过模仿、夸张等手法,小丑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放大、制造笑料,同时不乏粗鄙的元素,他们使用夸张的语言、肢体动作,甚至是自贬的方式制造笑点,从而将观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中解放出来,带入一个充满欢笑、荒诞不经的狂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小丑将自己降格为观众的取乐对象,又体现了狂欢式中“俯就”的范畴。
小丑的形象具有深刻的二重性本质。一方面,他们是舞台上引人发笑的丑角,以夸张、怪诞的表演赢得观众的喝彩;另一方面,小丑又是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人物,他们往往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幸而通过选择扮演小丑来逃避现实。这种悲剧与喜剧并存的二重性正是小丑形象的独特魅力所在。
具体而言,这个群体选择使用小丑的身份作为伪装的面具,摒弃自己的社会身份,以自嘲乃至自暴自弃的态度和啼笑皆非的行为去直面生活中遇到的苦难与不幸,通过笑来转化和超越它们,呈现出自毁倾向的狂欢行为。而对于舞台下的观众而言,小丑永远以激发众人的大笑为目的,歇斯底里而毫无节制地狂欢,将众人一同卷入毫无底线的欢乐之中,即使观众的狂笑是基于小丑的可鄙、可悲或者丑陋。于是,痛苦、羞辱与欢乐、狂笑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小丑在台上台下都如庆祝嘉年华一样狂欢,蔑视所有痛苦,也蔑视自我。几乎每一位小丑最终都在表演的极致狂欢中消失或死去,这些正是他们以极端的乐观主义唱诵悲剧的人生观的集中体现。
除此以外,小丑的表演中充满了讽刺性模拟的元素。他们通过模仿社会上的各种人物、现象,用夸张的手法揭示其荒谬性,采用以丑为美、自我肢解和死而复生等极端的表演方式,从而达到讽刺和批判的目的。例如,尽管其形象与美的标准背道而驰,但依靠一系列夸张和扭曲的身体语言呈现极端的丑陋,从而创造出了令人捧腹的喜剧效果。这样的讽刺性模拟正是狂欢化理论中对“颠覆与解构”的最佳实践,既颠覆传统美学和解构社会秩序,又创造了属于小丑的审美价值新秩序。
同时,这种讽刺性模拟又反映了狂欢式形象“生与死、悲与喜”的二重性本质。小丑的表演中包含了大量自我肢解和死亡复生的元素,这种极端的狂欢化表演,不仅展现了小丑的悲剧性命运,更凸显了他们的顽强抗争和对自由的渴望。例如,“丑王”巴佛在表演中的死亡与复生,不仅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到了震撼,更引发了观众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刻反思。这种将悲剧与喜剧、死亡与生命紧密结合的表演方式,正是狂欢化理论中对于“生与死、悲与喜”主题的深入挖掘与呈现。
2.3反常的动物: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赋权
马戏团这个特殊的狂欢空间中,人类和动物以惊人的自由和坦率发生随便而亲昵的接触,过去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和关系随之瓦解,而相应的等级结构和秩序却得到了重塑。动物不再受限于人类设定的等级结构,不再受人类的奴役和压迫,过去长期处于边缘化位置的动物从人类至上、动物低劣的日常秩序中被解放了出来,并被赋予了中心位置,它们与人类之间的互动不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两者之间变得平等。
具体而言,马戏团中有许许多多反常的动物,它们打破了人类对动物的传统认知和对动物行为的预期,它们不再是被动的表演者,而是拥有智慧、情感和独立意志的实体。比如会用字母拼写单词、给人预言占卜的母猪西碧儿,它时常给出精准而奇妙的答案,马戏团团长不论做何决定都要听取它的建议;又或是成对的老虎舞者,它们迷恋音乐,听着华尔兹会幸福地翩翩起舞,如果失去舞伴则会为无法舞蹈流下痛苦的眼泪,或嫉妒地发狂、攻击夺走自己舞伴的人;还有黑猩猩们,它们拥有独立的语言和文化体系,一边在人类面前扮蠢、表演猴戏,一边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私下里探讨各种学术问题,例如将人类作为实验对象探究其生理构造,甚至最后成功与团长签订了狡猾的不平等协约,卷款逃离马戏团、集体乘火车去他乡开始新生活。
“亲昵的接触”导致了等级结构的消弭,事物脱离束缚,而“俯就”的范畴便推动事物的两极走向统一。被现实世界所禁止和否认的动物自主意识、反抗精神与智慧在马戏团得到了激活,被固化的人类与动物的强弱关系得到改变。作品中的母猪西碧儿、老虎舞者、黑猩猩既是动物,又展现出了通常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特质,如智慧、情感和艺术欣赏能力,推翻了过去人们对动物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人类与动物间原本的差异、矛盾被弥合,传统的二元思维被解构,因而“动物同人类”“野蛮同文明”“卑下同崇高”,一切融为一体。
3.西伯利亚的荒原:间离的世界
3.1伯爵夫人的女子监狱:囚笼中的自由颂
作品中位于西伯利亚的女子监狱是另一个反常规、反日常的狂欢空间。一方面,其创始者和主宰者伯爵夫人是一个具有二重性本质的狂欢式形象,反映了狂欢理论中的“俯就”范畴;另一方面,女囚犯与女看守以惊人的亲昵互帮互助、协作,联手打破了监狱的秩序,推翻了伯爵夫人的控制,在心照不宣的共同抵抗和冲突中,她们实现了一次集体的狂欢盛宴,并在破坏监狱旧秩序后建立了平等互助的女性主义新秩序,是狂欢精神中再生与更新的重要体现。
伯爵夫人的形象融合了种种矛盾的特质,包括执法者与犯人、忏悔者与监督者、正义与罪恶,挑战了传统世界观中的二元对立逻辑:伯爵夫人虽为上流社会的贵族,却选择终日与囚犯一同陷于囹圄之中;她虽然是律法的正统执行者,但实质上又背负着血淋淋的过往,是和女囚犯完全无异的杀夫凶手;她既是监督女囚犯忏悔的冷酷管理者,又是此地最恐惧和最脆弱的终身忏悔者;她既是秩序和牢笼世界的创立者,又是被她自己所建立的秩序和牢笼所惩罚的最卑微、最晦暗的犯人。这种身份的错乱与颠倒,也正是狂欢理论中“俯就”范畴的生动体现,伯爵夫人实际上自行解构了监狱的秩序体系,与囚犯和看守在狂欢的新世界中达到了诡异的平等。
女囚犯与女看守通过默契的协作与亲密的互助成功逃离困境,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女性群体的力量,更反映了一种狂欢的精神。她们通过经血传递信息、私下交流,在缄默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紧密而团结的联盟。这种联盟不仅打破了囚犯与看守之间的传统界限,更在无形中消解了监狱内部的等级结构。她们的共同行动,如同狂欢节中的集体舞蹈,充满了力量与节奏感,将个体的力量汇聚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由女囚犯和女看守共同掀起的狂欢并非简单的放纵与混乱,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秩序重构意义。这场狂欢,不仅使她们脱离了伯爵夫人的魔爪,更在无形中建立了一种基于平等、互助与关爱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形成,正是狂欢精神中再生与更新的重要体现。
此外,这场监狱中的狂欢盛宴还体现了对权威文化的颠覆与对个性的高度弘扬,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在伯爵夫人的控制下,监狱内部充满了压抑与沉默,女性的身体与声音被严格地管制。然而,在女囚犯与女看守的合作过程和她们深厚的情谊中,我们看到了对这种秩序的颠覆与对女性主体性的张扬。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方式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监狱文化,这种文化充满了女性的智慧与力量,是对权威文化的一种有力挑战。
3.2萨满教的驻地:自然崇拜与巫术超验的交汇
萨满教的驻地位于西伯利亚荒原上的某一森林深处,是一个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高度封闭的世界,而萨满巫术展现出对自然、神灵和生命的敬畏与崇拜。
萨满教的信徒以传统的方式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与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处于微妙的亲密接触之中,几乎抹除了一切关于族群、物种的秩序,甚至消除了现实与非现实的差距。从族群的角度而言,他们不因外来者华尔斯的不寻常外表和迥异语言而排斥他,反而认可和欣赏他因为事故造成的疯癫,接纳他为集体的一员并尊重、照顾他;而以物种角度来看,他们在祭祀传统中,会把当作祭品的熊崽真心实意地视作自己的家人,将它抚养长大、爱护它。
因此,不被种种现代社会秩序与制度束缚的这些人作出种种怪异而不得体的行为,以具体、感性的形式揭示人性本质的潜在方面,人际关系乃至与周围事物的关系都由既定的严肃形式转向偏游戏的娱乐形式,从而体现了狂欢理论中“插科打诨”的范畴。例如,他们将幻觉视为工作的一部分,将自然景观和天象作为信息的来源;在正常人眼中尿液被视为肮脏的,但在萨满教的信徒眼中,尿液是神圣的,饮用尿液甚至具有玄妙的功效;正常人眼中被视为疯癫的梦呓和胡言乱语在这里被视为智慧的表征和有意义的言论。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萨满教的信仰体系中,他们将种种对立的事物合二而一,反映了“俯就”范畴。信徒虽被外界视为一字不识的“文盲”,但他们拥有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他们不被文字所束缚,而是通过直接与自然界的对话和交流,获取了超越文字的深刻洞见。这种将“文盲”状态与深厚知识结合的特质,正是“俯就”范畴的具体体现。此外,信徒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接纳了来自外部世界的疯疯癫癫的异乡人华尔斯,进一步彰显了萨满教对事物对立统一的深刻理解——“差异”即为“相同”,怪异即为正常。他们食用血腥的食物或排泄物,来实现与神灵的交流,达到圣人之境界,反映了事物的两极——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下都被他们统一和融合。他们对梦境和现实不加区分,认为梦才是真实的世界,现实反而是虚假的,这里他们将真实与虚妄、梦境与现实融合为一体。
在“俯就”这一范畴的基础上,萨满教的信徒以熊祭祀的活动也反映了加冕与脱冕的二重性。在这种传统中,作为祭品的熊崽既是他们所珍爱和细心抚养长大的家庭成员,又是无情的祭祀对象,他们会以毫不矛盾的态度,怀着虔诚之心将成年的熊崽献祭,在哭泣之后无痛苦地食用它的骨肉、剥下它的毛皮。这也可以类比为加冕与脱冕的过程,加冕即将熊崽先置于一个特殊而崇高的地位,而献祭和食用熊崽,则类似于脱冕,即将其从崇高的地位降低,恢复为自然界中的一个普通生物,体现了加冕与脱冕的二重性,在狂欢式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性和转变的可能性。
三、狂欢书写与现代荒诞的互证及深度拓展
首先,狂欢化文学对语言的游戏性和创新使用,为表征现代荒诞的语言实验提供了灵感。《马戏团之夜》中充斥着双关语和隐喻,这些语言技巧增加了文本的多义性和深度。通过双关语,卡特能够在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之间建立联系,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作者的语言风格多变,从高雅的书面语言到粗俗的口语,再到马戏团特有的行话,这种多样性体现了狂欢化文学对语言边界的拓展。在描述马戏团表演和仪式场景时,卡特使用了一系列具有仪式感的语言,这些语言不仅营造了特定的氛围,也反映了狂欢化文学中对语言的神圣化和仪式化处理。小说角色的对话和内心独白常常不符合常规逻辑,通过这种荒诞性,卡特探讨了语言在表达人类经验时的局限性。以上种种成功展现了狂欢化文学的语言游戏和创新,不仅打破了语言的传统功能和结构,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在现代荒诞文学中,这种语言实验被用来表达人类思维的混乱和无序,通过语言的扭曲和重新组合,反映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困惑和无力感。毋庸置疑,狂欢化文学的对语言的游戏性和创新使用为现代荒诞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通过语言的创新,作家能够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探讨社会问题,挑战语言的常规用法,从而揭示语言在社会控制和个体表达中的作用。
其次,狂欢化文学通过对传统秩序的挑战和对权威结构的解构,为现代荒诞提供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文化批判工具,并且这种颠覆性也在现代荒诞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即通过揭示权威的荒谬性和不合理性,促使读者对权威的本质进行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狂欢化文学常常将社会的边缘化群体置于中心位置,赋予他们以声音和能动性,正如《马戏团之夜》中妓女、动物和小丑表演者、被审判和关押的囚犯等,这些通常被边缘化的群体在这里获得了中心地位,常规的社会秩序、等级结构被暂时搁置,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而这种等级结构的颠覆做法为现代荒诞文学提供了一种批判主流文化和社会边缘化现象的工具,同时也为被忽视的群体提供了表达和自我认同的机会。
再次,狂欢化文学解构二元对立思维的倾向为现代主义的荒诞性提供了一种批判传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新视角,揭示了这些对立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构建。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关系而言,狂欢化文学常常模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展现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复杂性,而在现代荒诞文学中,这种模糊性被用来批判那些过度简化人类经验的理性主义观点,揭示了理性背后的非理性冲动和非理性中的合理性。若以文明与野蛮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展现文明社会中的野蛮行为和野蛮状态下的文明迹象,狂欢化文学挑战了文明与野蛮的传统对立,现代荒诞文学则能利用这一点探讨文明进程中的残酷性和虚伪性,以及所谓的“野蛮”行为中可能存在的人性光辉等。总而言之,通过解构二元对立,狂欢化文学揭示了权力关系如何在社会中构建和维持这些对立,以及这些构建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现代荒诞文学继承了这一批判精神,通过展现权力结构的荒谬性和压迫性,挑战了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构建的脆弱性和人为性,揭示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异化和孤立。
第四,《马戏团之夜》蕴含着狂欢化文学背后的哲学思想,如对生命等同死亡、崇高等同卑下的反思,为现代荒诞哲学探讨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哲学思想挑战了传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现代荒诞文学中,这些哲学思想被用来探讨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通过对生命、死亡、崇高和卑下的重新定义,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和无意义。
第五,狂欢化叙事中的多样化表现形式,如讽刺性模拟和怪癖的“插科打诨”,为现代荒诞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手段。《马戏团之夜》中,这些表现形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界限,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叙事风格,呈现为混乱无序而怪诞诡谲的特征。在现代荒诞文学中,这种叙事风格被用来表达人类存在的荒谬和无意义,通过荒诞的情节和人物行为,揭示了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和混乱性。
综上所述,狂欢化文学为现代荒诞提供了相当独特的表达形式,不仅在社会文化批判、文学手段、语言实验和哲学探讨等方面为现代荒诞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且通过其内在的逻辑和深度加强了现代荒诞文学的说服力和影响力。狂欢化文学和现代荒诞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也拓展了文学的思考空间和表现范围,既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估和思考,又为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 李严合.《马戏团之夜》中狂欢化建构的女性主义世界[J].今古文创,2024(8).
[3] 卡特.马戏团之夜[M].杨雅婷,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高馨恬,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李佩仑,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卓越人才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