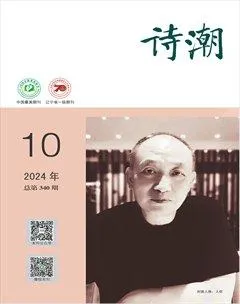随遇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而在人烟浩茫、川流不息的南粤一隅,却可寻着瀛洲(又称小洲村);也无天台一万八千丈,倒可以顺着溪流果林进入一个区别于广州闹市的幽静之处;还可以逢着闲云野鹤似的一群人儿,在其间作画、吟诗、饮茶、论道……仿佛天下熙攘往来与他们毫不相干。如果你有点儿恍惚,疑似幻境,也许还可以让一个年轻却俨然超脱的画家带你在这方水土上游走一番,与这帮“仙居”的艺术家们逐一谋面——这就是珠江水上、大隐隐于市的瀛洲;这就是在瀛洲生活得如鱼得水,兼有诗人、画家、篆刻艺术家多重身份的何继。何继自称“呕斋主人”,他的呕斋内外茂林修竹,间或长着南方普遍的小瓜树,上面结满了青色、大小不一的木瓜,小洲村中保留下来的树龄很高的龙眼树,沧桑的枝丫隔着水渠斜斜地伸到屋檐下;门扉轻合,只是竹做的篱笆,颇有古代隐居之所的味道。我曾提出疑虑:门不用锁吗?里屋有更结实的门吧?何继甩甩手走到面前去了: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些字画,要是想要就自己拿吧!好一副“积善缘、无挂碍”的洒脱样。而我也深知对于画家何继,那些字画就是他的宝贝和心血。他曾在阁楼的画室为我们展示一张十几米的长卷,是临摹唐人佚名的《八十七神仙卷》。我曾在画册上观摩过这画卷的摹本,叹为观止。在何继的画室中,八十七神仙一一下凡,被徐徐打开,我再次感受到那种震撼,观者皆如我,个个敛声静气,生怕惊扰那长卷上或低眉慈眼或安详自得或金刚怒目的神仙们。何继说,他用了十五天来完成这幅画。我小声地惊呼:十五天!八十七神仙,这该是多么耗人的创作!而我再次伏案细细观摩那被平铺的画卷时,深深明了,这贯穿一脉的气韵,仿佛一个人骨血里全部的汩汩和肺腑里深浅相和的呼吸,万钧齐发的艺术冲动,必使得这个作画者连续十五天,甚至损耗健康、精力和体力而在所不惜。是才华是耐力,更是抛开杂念和纷扰的静气——这是所有艺术表达里最为难得也最为可靠的东西。这种“出世”的东西,让我看到作为画家的何继那些深深浅浅的水墨里兀自岑寂的禅意、空灵、举重若轻的定力。
呕斋里水墨氤氲,何继的诗画高悬室内,或写意或随性。也无问询斋名的来历,七弦俱备,闲时可调。常有游人或友人前来,饮茶坐谈,酬唱对答,一派古人“春服既成……咏而归”的风范。这也许是作为“隐者”的何继的日常生活。他在小洲村侠心交友,与岛上的居民们和睦相处。他玩笑说自己是小洲村的村长,走到哪里都有人问候,“何老师,来坐啊”。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纵情诗画,惹得许多人从滚滚红尘中跑来观望。
我很好奇呕斋那种豁达的幽深,仿佛对一个烟涛微茫处所持有更深邃的期待。果然,何继捧出了他的诗歌著作《露天吧 何继诗选》。迫不及待地翻阅,竟全是现代诗!我终于看见作为诗人的何继从水墨中走下来,从他古体的韵律和扇面上走下来,以非常现代、“入世”的姿态,向世人诉说他的身世——是的,身世,在我看来,那些写给厦门、北方、小洲、寺院的诗篇已然成为何继身上的精神胎记,那些辗转、流离、安定和最终自足的心境是一个人从混沌中抵达通透之必经。而那些写给友人(其中包括写给我)的诗篇尤使我感动,何继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感受外界的美,物与人的美,不断让其与自己内心不可磨灭的自然、纯粹、灵动和感恩相呼应。美丽的灵魂总是如星辰,彼此照耀,他写给女友小娴的诗句则更让人感到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内心的温暖与光彩,让人读之会心而微笑。
我无意了解和探讨何继的诗歌与绘画在当下如此喧闹的时代到底处于何种位置,会被什么样的人去辨识。我只是由衷地感到一种可贵:这样一种人活着的状态,那种恬然自适,那种淡然自处,那种超然自得。更可贵的是,他们仿佛真的居住在远远的、被雾勾勒的瀛洲,让那些灵魂匍匐在尘埃里的人重新去审度一些有光生命的话题。“古来万事东流水”。且看吧,何继站在小洲的桥头对我们说:“把拉长的夏天分为三段/慈悲 善举 简爱。”
在本应结束此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诗人潘维曾在一篇序言里这样写道:“我们总能在文字中触到星空、家乡、绝望与梦;许多时刻,我们在身体之外到处旅行,从事生命。”我无从知道何继还将以何种方式或者更多种方式触摸生命并且从事生命,而我,对这样一个仿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他,唯有献出我的尊敬和祝福。但愿,在我们还有心探访的时辰,这样的“隐者”,还能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