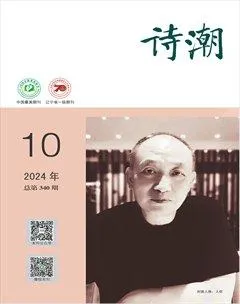幻象与现实交织而成的“深图景”
“无法安慰的悲痛使我们面孔僵冷/嚼碎呼喊 如嚼碎片片苍绿的雪/在骨头吱嘎的磨砺中/衣领 又一次缓缓竖起”(《无法安慰的悲痛》);“月影坚硬。裸露的骨肉反复扭动着/苍天在苦痛之上 野径翻越歌哭”(《面具之夜》);“月亮旧了,山墙坍了/野地里的骨头咚咚响了//姓氏多了,疼痛远了/祖宗的牌位被大风撕了”(《谣曲》)……不知大家发现没有,姚辉的诗有一个很常见的感性意象,即骨头;有一种很常见的感情要素,即疼痛。笔者认为,这个感性意象与感性要素虽说都是常见的,但是姚辉却把它们放在“异质环境”中,不管是“如嚼碎片片苍绿的雪”的异质,还是“月影坚硬”的异质,或是“山墙坍了”的异质,它们都带有“悲壮的疼”,像这种把感性意象、感情要素变成一种动态意象,变成一种情绪萌动的幻象,我们可以称之为“青春的热度”。正像姚辉写过的《骨头之舞》,那种舞动、那种萌动都是从身心内部发出来的,它搅动起来的已不是器质性的东西,而是事物组成的精神整体,这便是姚辉诗歌的基本特质:锐利如刀,温润似水。
一、宏大的激情,将诗歌写作置于某种“无穷”
如果说锐利来自思想与精神,那么温润则来自语言与性情。崇尚精神写作的姚辉断然略去一般写作者眼中恒定的自然物象,仅捕捉那种瞬间一现的诡奇心象,他常常以宏大的激情、沉醉性的史诗意识和深重的精神史大胆地进行情感节奏的推衍、生存经验的演绎、质疑精神的释放、伦理品质的淬炼。在这过程中,既有生命的鲜美与圆润,又有生命的大度与悲壮,由此交织成生命把持与人文关怀的景观:“我不敢啼哭/不敢沉默/如果所有森林于瞬间举起影子/让我也加入进去吧/母亲 在你最隐秘的角落/我 我们
凭借儿子的名义生长”(《太阳》)。这是姚辉写于1986年,最具生存经验与伦理品质的一首诗,同时,也是他在情感节奏把控上较好的一首诗。说到这首《太阳》,我惊愕于姚辉谙熟人性的生存经验、伦理信息与精神脉冲。在那个年代,一个真正的诗人,能置于个人与群体、与社会、与时代的交错,坚守种种繁复的情感伦理,基于这种写作态势,他把像“太阳”这样的词语调到最适合内心生活的境地,这无疑是将诗歌写作置于某种“无穷”。的确,碌碌尘世里,过眼烟云的往事并不鲜见,所匮乏的应是一种适合情感储存、情感冲动与情感释放的往事:“鸟啼如一页页雕花的窗/半掩着/风以人类无从察觉的方式/呼喊火苗”(《夜》)。是呀,“又到凭一盏油灯彼此温暖的时刻了/影子们行走在墙上/那些生锈的钉子/已无法再使它们感受到丝毫痛苦”(《夜》),从“雕花的窗”到“风”再到“火苗”,从“一盏油灯”到“影子”到“墙”再到“钉子”,此时此刻,呼唤火苗的“风”,把人的情感一步步推向极致。就姚辉的《夜》而言,不管是情感的境地,还是思想的境界,意象环环相扣,情感步步紧跟,这样的情感节奏,这样的形声效果,就是一种以情感作用于精神的语言效果,是一种对精神的特殊审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姚辉的《夜》称为创造性语言的“情感波段”,因为诗的语言是高度造型化的,并不是一种美化过的论述。因此,姚辉的“情感波段”从科学的立场与生活的立场上看似一种幻觉。不过,这种创造出来的幻象可以令人联想到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地方,就像历史性小说或是描写某一地区风貌的小说可以令人回忆起往事一样,令人历历在目。的确,处于云贵高原的姚辉,从他提笔写作开始,就注定与这个特定的区域息息相关,一脉相承。
身处云贵高原的姚辉,同样面对的还有一座诗歌高原,他把石漠、暴风雨、山峦、天体或整个宇宙视为大自然大生命的显现。面对繁复与简单、驳杂与单纯、幻觉与现实、盛大与细小、荒诞与庄重、澎湃与肃静、历史与现实交织而成的“深图景”,姚辉把它们全都上升到史诗般的提高形式。他的这种提高形式,不是那种高蹈抒情的式样,而是充分借助汉字的形式结构——韵律、节奏、气息、音阶等句行,借助有规则的语言的元音、重音,赋予语言一种神秘的、几乎是魔术性的特点,从直觉向幻觉扩展,从感性向理性提升。是的,随着一步步的情感节奏,一程程的理性速度,姚辉完全凭着对万事万物最初的直觉去写诗,以纯粹的诗心营造出纯粹的诗意与诗境:在隐与显、显与隐的语境中,形成高远而辽阔的精神气象:“秋天就要结束/我们扔向天空的所有石子/已开始/错落有致地/飞翔”(《关于鸟》);“可能有一片圆形叶会唱歌/会表演一个众所周知的保留节目/而池塘会抬起身来/凑向微斜的荷秆/——这是推测之一”(《关于天气的预测》)。姚辉追求的境界是宏阔的,这不,秋天,本是尘埃落定、万物归顺的时节,而当姚辉“扔向天空的所有石子/已开始/错落有致地/飞翔”的时候,也许落定的不该是尘埃,归顺的只是一个时机。一向有着质疑精神的姚辉,在他的心目中,就连那些坚硬的石头也想“飞”,这预示着他并不满足于早已恒定的世界。是的,姚辉深知,像他这样60后的诗人,大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法则与怡养心性,而这恰恰是与生俱来的财富,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平添了个性表达的气息与气场。一直以来,姚辉善于把语言变成一种事业,把和谐音籁带进诗界,在情感与思想的行进中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呼应。姚辉在赋予语言以情感节奏和韵律的同时,不断去加强它的情感频率。在姚辉看来,诗歌的节奏与韵律其目的是延长冥想,让读者保持一种可称作是真正的出神状态。具体地说,姚辉常常利用集体幻象中已具成形的情感个案加以节奏化与客观化,极力避免“集体无意识”,体现出当年的姚辉的诗歌作为。同时,他的想象早已超出群体感情经验的那些词汇,并具有召唤的力量。从形式的角度来看,他的情感节奏不断传递出情感信息与思想密度。当姚辉的诗歌从语言的外部表现——韵律、比喻、说明、结构上升到经验、理想和命运的那一刹那,读者无疑进入了他的生存经验领域。以姚辉的《无法安慰的悲痛》为例:“把手藏在世界之外/把麻木的战栗藏在手之外/把所有的倾诉藏在战栗之外/把最后的欲望藏在倾诉之外/但无法藏起痛苦/我们的痛苦/已多少次/被粉刷得毫无意义”。“之外,之外,之外……”在这里,姚辉按文字叠加层层推进情感节奏,对生存状况进行大胆而奇诡的反思。是的,一系列的“藏”,却无法藏住痛苦,这是生存的悖论,也是生命的悖论:手如何“藏”在世界之外?战栗如何“藏”在手之外?欲望如何“藏”在倾诉之外?这一系列悖论式的问号,这一系列“被想象”出的生存状况应该理解为一种命运和世相,理应折射出某个时代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局,理应呈现现实秩序与命运驱动的真实境遇。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的确需要在更沉、更重、更密的剿杀中,创造出新的人生环境,进而大胆地呈现出淋漓尽致的“心灵现场”:“酒滴浩荡 山峦被半片毛羽覆盖/这是面具之夜 苗女翩然的姓氏深入骨髓/一把旧瓢 舀响火势之源/所有可能出现的怀念开始燃烧 呐喊之星/正自大片黧黑的脊梁上 缓缓升起”(《面具之夜——乡野傩舞之夜侧记》)。这看似一场“面具”之舞,但其中所包含的生命之舞、民族之魂又是那么雄浑与大度。的确,一系列地域元象对姚辉而言,如同一次次扪摸生命心脉,如同一回回展示生存经验——声音、形象、思想、感情,哪怕有时只是一次想象性的生存经验,对每一个读者来说,也是那么神秘,令人神往。应该说,在姚辉的诗中,那些和我们相遇的事物,它们植根于历史或人们的心灵,并在那里萌发出茂盛的新芽。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是理想人格的塑造者和把持者。
二、对生命、情感与意识的符号性表现
当我们感受到姚辉诗歌的生存经验、伦理品质与质疑精神是在合理的想象与恒定的精神状态下实施的,对诗歌而言,这是多么真实的瞬间。我们惊愕,读者有时难以表达的感觉,姚辉的诗歌却是那么鲜明炫目,不容置疑。特别是读者一时难以分解的思绪,姚辉总能引领读者朝着想象力的顶峰攀登,而不是陷入神秘主义。特别是他具有觉察主要趋向和细枝末节的眼力,能够完满地把词语和形象转化为诗行。在姚辉看来,有节奏的情感是诗意表达的基础。有时,姚辉也运用一种玄虚、深远和无常的表象,不过,他与先锋诗人不同,哪怕运用了玄虚的表象,也从来不为“玄虚”而高蹈。恰恰相反,他常常将这种意象通过文字上的几个响亮的音区与节奏喷发或渗透出来,比如他的《雨》:“一场雨开始降落。它等候了多久?/悬在高处的雨,甚至/与骨节中燃烧的疼痛无关。二十年前/或者一年之前,一场雨会让我思考/让我惊异:‘它袭击了我!’我似乎有些骄傲/——在雨中,我正经得像一团焰火/那么重要的雨,改变了我的经历”。按理说,雨,本来不玄虚。然而,“在雨中,我正经得像一团焰火/那么重要的雨,改变了我的经历”,这就玄虚了!不过,姚辉很少在玄虚道上绕来绕去,即使雨像一团燃烧的“火”,他也从容应对。在这里,看似玄虚的雨,在他宏大激情的作用下,叮当作响,响声有痛,也有激越,这是多元情绪与生存经验交汇的结果。的确,姚辉的诗歌好就好在,哪怕是诗歌里的玄虚,他也不急于去表现一切新的可能的情节,而在于“虚位以待”,能把现实中不可思议的东西同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就是生存经验联系起来。比如,他的《旷野上的鼓声》:“父亲 那远远地敲打骨头的会是谁呢?/整座旷野 已布满/你黝黑的名字//我带着夏天前来 面对一朵野花/我想安排好蜂蝶纷飞的秩序/而鼓声在远方响起/背对夏天的人/画下 旷野倾斜的痕迹……”不得不承认,姚辉的生存经验与伦理品质是紧密相依的,这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充分地显现出来。在他看来,诗歌的最高典范是伦理品质,而伦理品质的真谛恰在生活之中。的确,他的《旷野上的鼓声》所表现的伦理品相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首诗,既有像旷野那样沧桑的一面,又有蜂蝶纷飞温润的一面,由此可见,无论是可亲的人物,还是可感的时空,无论是倔强的生命,还是辽阔的山野,《旷野上的鼓声》作为有分量有质量的伦理品相,早已为读者所赏识。
应该说,姚辉的诗,不管是运用情感节奏,还是生存经验,不管是提倡质疑精神,还是追求伦理品相,他的诗有它自己的完整世界,其中包含的每一个成分都是为加强它的符号性表现——对生命、情感和意识的符号性表现而存在。同样,姚辉的诗,不管是短诗还是长诗或是散文诗,由于他有着超强的组织经验的能力,在一般情况下,那些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万事万物,总能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值得一提的是,他所构筑的诗歌之“美”是一个完整的、合成的延续体,有着可感的宏伟,那种9eqUEBf3EqIObgQBP8oDZcVG5Tu0LgGYNQkjyjc1esk=“可感的宏伟”总能把我们带到自我极限中去,与读者形成一一对应的“感觉类比”。比如《拔草记》,“有一些四月的草需要/选择性拔除——//麻木的。哄抢天穹的。嗡嗡/诅咒的。用黑铁之肩压榨/风声的。总将茫茫露珠逼至/绝处的。以狗吠代理金色/太阳的。念头像旧刀片的。/散发谎言暗影的。光阴与梦的/霸占者。致使春色反复/荒芜与变质的。”在这里,一系列的类比,不管是情状——“麻木的”,还是共愤——“诅咒的”;不管是决绝——“绝处的”,还是高处——“太阳的”,或专制——“霸占者”,这些“极限式”的类比,形成巨大的冲击力与反冲力,姚辉正是在这种“差别化”的极限里,给人不容置疑的选择。正是这种决绝的碰撞,才能撞击出精神的火花,才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这种快感实质上是各种不同思想的碰撞,神奇般扩展了或激发了人们的阅读潜能。由此可见,“有一些四月的草需要/选择性拔除”所引发的“类比”,体现出姚辉的诗歌修辞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呼应,蕴含着强烈的类比更新、质疑精神以及修辞潜能,并且与历史、生存的明暗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异的结合,揭示了浪漫主义的诗学定位与现代社会、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
纵观姚辉的诗歌创作,读者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在姚辉的身上有着可贵的写作伦理,即质疑之后的疼痛感。这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道德立场,也是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或以他者为中心的伪抒情的一种超越。同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姚辉把生存经验回归到感官水平,其目的就是维护好生命感受的原初状态。特别是他经常把感知的触角伸向幽远、宏阔甚至是史诗般的境地,使他的诗歌有一种阔大深远、傲然不屈的品质。同时,在他质疑精神的深处,他面对的不管是现实,还是梦幻;不管是直觉,还是现状,都从容地使自然的时间变成一种“被经验”了的时间,一种经验化的符号存在,正如他的《农历五月初五日的水》所呈现的那样:“而这是一千种时代的水声/那人走着 芳草仍将枯萎/典籍与身影修改沉浮 那人走着/只是一滴无辜的水啊 为什么/就这样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痛苦的习惯!”是的,“一千种时代的水声”所激发的诗歌“内在韵律”,这不仅取决于“一千种时代”的情绪与精神,也取决于姚辉从“另一个世界的反光中”寻找到政治的、情感的、现实的“伦理”,由此交织而成生命把持与人文关怀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