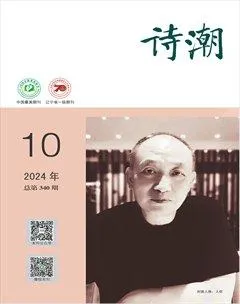韩东写作的会心会意
一
“写得跟真的一样。”
新购韩东两本小说集,《狼踪》一点一点读完了;《幽暗》推荐给儿子,以为他不读,结果开学时他塞进行李箱,拿走了。寒假回来,问他读了没有,说是读了。问他感觉咋样,他给我说了开头这一句。
对于没经过文学作品阅读和写作熏陶因而缺乏经验的儿子来说,这一句,也许最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感受。
小说,本是虚构,韩东的小说,似更不以我们常说的“故事”见长,那么这“真”,也许就是一种近乎直觉的评价。
而此前,以一个资深读者的身份,我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韩东的小说、散文、诗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同、相近的细节或情节。这与博尔赫斯的互文有所不同。这些相同或相近,不断强化读者对韩东写作“真实性”的印象。尤其当这些细节、情节在他的小说中出现,认知中小说原本应有的虚构性,没有减弱,反而强化了“真实性”。这很奇怪,又很迷人。读着读着,会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无论哪种文体,无论如何变化,用以支撑的精神底色和生命质地,始终是一样的。而这,也可能“控制”并在经意不经意间形成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
两相对照,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惊异感。或者说,这是韩东创造的另一种《奇迹》?
不要来反驳我,说此真非彼真。“真”在韩东这儿,与我们艺术中讨论的“真与假”,真实与虚构,有相同又有不同。个人约略理解,是一种综合性的但又无须分析的感觉。有时,我们站在艺术的角度,有时站在现实的角度,有时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在两者之间不停切换或把两者有意无意进行混同,生出一种我们所谓的“真”。但韩东对“真”,不是在概念中推演,而是在语言和生命构成的作品中体现、呈现和表现。不错,韩东的“真”,始终未离开艺术的场域,未离开生命和艺术给我们创造的“真”本身。
真,在韩东这儿,是他创造出的一种至高艺术境界。
二
不同文体之间,在重复吗?材料的单一,或貌似匮乏,以及不断的出现、闪回,都有可能给人带来这样的印象。或许这一点,在比较昌耀和佩索阿时,我早已解除了心结。而不断的阅读,让我意识到,看似“纤弱”的韩东,始终在“挺进”,坚韧不拔,靠近自己心目中“艺术的样子”。作家就是“匠人”,艺术就是手艺。的确,他和一直画圣维克多山的塞尚,有得一比。由此,像不主张艺术的“进步”一样,他也不执着于新的题材会带来“新的意义”这样的思维定势,而是似乎在消除题材本身所谓固定意义强加的影响;所有的题材,在他这儿,每一个都不会轻易放弃,而是试图“写透”,正如诗歌《白色的他》;同时,又暗中悄悄打通,各个题材像生命、时间、生活、存在等中“活着”的一部分,一种整体写作框架和情感(情绪)框架逐步形成,互为焦点与背景,互为主角与配角,互为演员与观众。这殊为不易,且很难得。
韩东的写作,展示了一个作家创造的全过程。克服貌似重复带来的单调乏味,进入并专注于写作本身,艰难而又喜悦,充满挑战而又奇迹不断,生命与语言、与作品体现出来的质地奇妙合一,合体。
有朋友说,韩东的诗,可以作为“榜样”;我知道,他说的并非仅仅是外在的一种样式,而是一种极少数作家才可修得的写作精神。
三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小说《兔死狐悲》临近结尾时,当送走张殿后,隔天“我”来到曾经生活多年的地方,“我”看见“换了打扮”的何嫂,骑着她刚刚逝去的丈夫张殿的摩托、后座带着他们穿上短裙的女儿画画,“轻快无比地”远去时,不禁问:
离开这里已经很多年,一般我是不来的。统共来过两次,一次碰见张殿,一次碰见何嫂和张画画,这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说,走在人群中,“我流泪了”,“那滴本该由张画画流出的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这是“兔死狐悲”的本意吗?是仅仅在写类似于“兔死狐悲”这样一个故事,还是在写我们共同的“命运”“结局”?也或者,还有更深的,对生命本身的感受和理解?韩东的诗和小说,看起来都很朴素,很简单,但始终意味“深厚”,一言难尽。
“我没有家乡故土,或者文学上的精神家园,死者和离去的人所空出的位置是我所谓的情感源泉,也是写作所需要的根据。”
当读到《五万言》里的这句话时,我停了下来,觉得这句话,也许可以基本概括韩东的写作。
“死者和离去的人所空出的位置是我所谓的情感源泉”,让我震撼。翻动阅读记忆,想想,无论是长篇小说知青三部曲,还是他新近的中短篇,无论是诗集《重新做人》《他们》《奇迹》,还是四十年诗选《悲伤或永生》,韩东确乎是在“空出的位置”开始他的写作,是填补某种写作的空白,更是“生命的扎根”“情感的扎根”。
四
那么语言呢,根是否也扎了进去?
西蒙娜·薇依曾说,“话语是用来表达事物关系的”(《重负与神恩》)。如果我们承认,薇依所说的“话语”某种意义上就是语言的话,那么,韩东所说的“诗到语言为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诗就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语言,是用来表达这种关系的。
语言如同另一种事物,当它面对这种关系,其实就构成、生成了它与这些事物之间的一种或多种新的关系。而要与这些事物、事物的关系,处于一个恰切的位置,那么,这个“表达”的过程,必然会有许多与生命个体、观念等相适宜的手法与技艺。不错,这个过程,我们说的是由语言发起的创作。
个人理解,韩东选择了去除语言的文化修辞,弱化甚至拒斥那种夸张的、表层的戏剧性,他让事物之间的关系,如其所是,也“在”那儿;他的语言,对准“当代生活”,朴素,精确,充满耐心,一点点抵达他所认为的那个核心,那个“真”。
韩东的《五万言》,充满洞见;这些诗学方面的思考,与其作品的高度契合,也同样在表明,韩东心中对自己的“作品质量”有明确的要求和衡量“标准”。有时候,从朋友圈看到,他在一首首修改诗作,用“及格”等来表明他的满意度,这不仅是习惯,更是一种态度,并同样包含写作精神的不懈实践。从“空处来”,甚至有时候写“空”,写虚无,但从不落于“空洞的空”“空泛的空”。他的写作很“具体”,依靠的是生命感(生命力)浸润、融入的细节。这样的细节,在他的作品中比比皆是。
“骑车带着小女孩——”,读到这儿时,我停顿了一阵,想到接下来的“情景”,应该在一首诗中出现过。果然,“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眸仍然那么清亮”,“已经是春天了”。这是我最近刚读到的《兔死狐悲》中的细节。
而翻开《路遇》一诗:“她们还要活下去,并且/这就开始活下去。/她一溜烟地骑过去了/一溜烟……”
一样,又不太一样。就像,虚无中的真实,真实中的虚无,而“爱真实就像爱虚无”。
他大量写母亲等亲人的诗,写皮蛋等动物的诗,写生命中出现过的那些人与事的诗,还有那些小说,一笔笔、一字字,都十分细腻、细致,情感上不离寻常而又直指存在和生命深处,客观,但让人潸然泪下。他没有煽情,而是如细雨般,一点点渗透进心的泥土。
换句话说,读韩东的作品,不要观念先入;作为一个读者,若真有所得,“这都是由于用心倾听/不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五
最早读到韩东,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了,但那时仅限于《有关大雁塔》,觉得其背后立意,还是在为了反对什么,比如,对文化的过度想象;在韩东这儿,诗就是最真实地切近日常生活与内心感受。是对北岛“做一个人”的“英雄观”的进一步后撤:在诗歌中做一个日常的人(这依然是另一种“英雄”)。而对“诗到语言为止”,觉得诗就是语言表面上的那点意思,无须过度阐释与解读。
及至再次断续读到,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了。印象最深的就是《甲乙》这样的经典,虽然读到的时候,不由得想起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空心人》等作品,想起法国自然主义的一些小说,甚至想起“下半身”写作,但无论是语言控制力、硬度和力量,都绝对一流,令人惊叹。《这些年》这样的作品,似乎多了一些岁月和经历带来的温情,可语言上依旧冷静,“不动声色”,十分克制;《格里高里单旋律圣歌》与早期的《我听见杯子》一样透明纯粹,但分明,语言与生命的契合度更为精准,有了新的方向和“语气”。而《长东西》,可以看出韩东在语言面前的“小心翼翼”,对语言的尊重和对“物”的切近在同时进行,他如同那个扛长东西的人,在不断地转换角度、调整方向,旁观者不知道怎么完成的,但“汗水擦亮的长东西”,“逐渐从深渊中升起”,这几乎接近寓言和元诗了。
他真的达到了写诗如说话。他在用说话的语气叙述一件具体的事,细微的生命感觉、情绪等。
读不到韩东的那些年,我以为他的写作中断了,而正是这“与世隔绝”的“幻觉”与事实,让人误以为韩东的写作是近乎天才般的写作。当然不是这样。从韩东的随笔集中,甚至他的小说中,韩东作为一个作家,常年在不停地写。那写让他对语言有了新的认识,对“物”,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对生命和艺术有了新的理解。写作没有让他对语言“疲劳”,而是始终保持对语言的信任。他的写作,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作品”。
他的作品“就在这里”。
合上他的诗集和小说,合上他的诗学随笔和散文,如同曾经有过的那样,我可能会长久离开,尤其作为一个写作者,害怕过深的沉迷会打乱自有生命节奏下的我的笨拙的脚步。但我知道,我合不上我的心。我的心会时不时穿行于他的文字中,会在读西蒙娜·薇依时,在读到真切的生命和匠心时,忍不住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他的一本书,再读一遍,或一篇,一首,一行,慢慢体味、品咂。
韩东的真,与爱,与手艺,与生命的会心会意,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