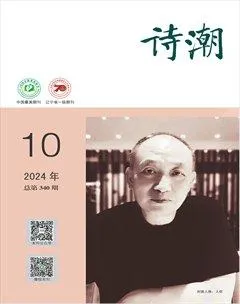诗之思[2024·第二辑]
89
政治与经济之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们从来都是一个时代那最鲜活的现场——那些最初的诗。
90
你必须去成为那唯一的自己,你必须试着去理解每一个人,每一粒草,每一朵花,每一颗露珠在孕育中那全部的艰难,你必须去理解人世从来,并一直作为一种如此珍贵的谬误。
91
我惊讶于我已活到了古人眼里的高龄,惊讶于我已年长于许多曾比我年长得多的亲友与故人。
92
真实是让人畏惧的,就像黑洞中那令人窒息的高贵与不自由。
93
江南不仅仅是盛产靡靡之音而醉生梦死的奢靡之乡,它更是那孜孜于日常生活中的神性的温柔敦厚之地。
94
江南之所以成为江南,是因王羲之、谢灵运,是因白居易、苏东坡,是因黄公望、倪云林,是因董其昌,因四王、四僧,因黄宾虹,因朱熹与王阳明,因你的毅然决然,以及那孤绝中的一往情深。
95
如果没有对这块土地的感同身受,那么,这一路的奔袭就是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劳役。
而你如此疲倦,又如此欢喜着。
96
当我看见塞尚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地坐在圣维克多山下的土路旁的照片时,我的眼泪滚落了下来。这何曾不是我所希望的,千年之后的读者从我的诗行间辨认出的形象。这何曾不是我试图用尽一生的徒劳,以获得的一张繁华落尽的脸庞。
97
汉语的未来恰恰在我们对我们之所知的,那世世代代的辨认中。
98
寂静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种极度的专注,是凝神于一,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绝。
99
游手好闲与一个静穆者是一段拙劣的分行文字与一首伟大的诗之间,那似曾相识的天壤之别。
100
不是我更为谦卑,而是我比他们多一份向那幽深处独自跋涉的坚毅与孤绝。
101
快乐是摩罗的诱惑,也是佛陀的教诲,在这无处不是欢腾,无处不盛放着忧惧的尘世。
102
我经常会想起,孔夫子在删定诗三百首的过程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时辰,那些在苦思与斟酌间敞开的无数匿名者,同样是这人世的命运。
103
所有伟大的书写都是我们在与曾经的知音不断地告别,而终于得以与最初的自己重逢的道阻且长。
104
隐地并不高贵于俗世,而我们是否依然配得上一颗心的圆融与自由?
105
在东方的智慧中,宇宙同样无垠,但又从来不会外在于那颗永不可名状的心。
106
知识是重要的,但读经能帮助我们获得那化繁为简的力。
107
你要祛除这人世重重叠叠的枷锁,你要祛除你之所以成为你的,那全部的虚妄与杂芜。
108
中庸是一次对人世绝对平衡点如此艰难地探求,以及大地之心,露珠般缓缓浮出草尖的一瞬。
109
不要用几天来审视得失,甚至不要用几年、一辈子,直到你终于获得了孔夫子在颠沛与造次间念兹在兹的千岁忧。
110
或许,是太正了,仿佛这人世一种如此坚固的偏执。
111
真正的澄澈与通透不是我们头顶的蔚蓝,而是此刻正从我们心中,从大地深处,从粗粝的岩层中缓缓浮出的幽暗与寂静。
112
道不远人,就像义理从来,或永远作为事功那最丰沛的源头。
113
我们的无辜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依然不能看见,我们的无辜是因为我们的耳朵依然不能听到,我们的无辜是因为我们的心依然配不上千古,配不上这宇宙,或是人世的全部。
114
传统不是我们想象中一个消失已久的帝国,而是那从我们心底,从大地之至深处汩汩而出的悲伤与欢愉。
115
传统是史,更是经。或者说,经是史之更深处,这人世从来的微茫。
116
所有的经文之所以成为经文,恰恰在于它向我们,向这人世敞开的,一种源源不绝的启示。
117
这世界的广阔与丰盈是通过自我——这个最坚固而细微的支点,最终得以与空无形成的一种奇异而玄妙的对称。
118
现代性或者说现代性的困境是建立在绝对个体的乌托邦之上的。
但事实上,绝对的个体并不存在,如果它不是作为道与空无的别称,就像地球,就像我们头顶的太阳与月亮,它们都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处于更多的星团,以及比星团尺度大得多的存在的相互作用与关联之中,而现代性的困境恰恰在于对这样一种关联的有意无意的忽视与遮蔽,终于赠予我们的,一个宇宙孤儿的绝望与荒芜。
119
才华对应于一种奇崛,而你愿意用这人世全部的奇崛,去换得一颗圆融的心。
120
我不能通过手中的笔记录下天空中这弯明月,是因为我的心依然配不上它此刻的皎洁。
121
当柳宗元写下“独钓寒江雪”时,他已然知悉千古不会长过一场大雪,或是一个独钓者的午后。
122
无可而无不可,你才配得上这人世之自由。
123
节哀顺变,最初是妈妈送我的一个崭新的词,直到我理解了它同样是生命在每一个瞬间,那源源不绝的赠予。
124
知音是千山之外,或是千年之后的那个不断醒来的自己。
125
年过四十,我才获得一种孤绝的自由。
126
那个用青山洗心的人,那个用绿水洗心的人,那个用白云洗心的人,终于获得大地至深处的澄澈、蔚蓝与深情。
127
与亲人的分离是人生中最艰难,而又必须独自去完成的一课,其深处依然是人世的局限与荒凉。母亲的离去,让我确信即使是死,以及构成一次具体死亡事件的无数细节依然源自生者与死者的意念,源自那不会因死亡而改变或消散的关联,以及人世至深处千古不易的绝望与深情。
128
节哀顺变,同样是一种悟道求真的力,以及因追随自然而终于重获的绵延不绝的人世。
129
圆满的是一个你不去强求,而又已不再被辜负的人世。
130
所有的“成”都是缓慢而艰难的,就像那一瞬中的永无止境。
131
天越来越寒凉后,西湖越来越完整。
而你越来越接近一个本来的人世。
132
只有终于理解了曾经以为永远无法理解的事,只有终于原谅了曾经以为永远不可原谅的人,只有终于释然于曾经以为永远无法释怀的一切,你才能说出一个饱满而丰盈的人世。
133
师山水与古人都是为了师法经由山水与古人得以显现的,那颗万物的太朴之心。
134
万物同源而又如此不同,人世才如此绝望而深情。
135
在一颗圆融的心中,任何际遇都在通向那最新的成全。
136
或许,荷马痴迷的是历史的波澜壮阔。
而一个东方诗人立志于从一颗露珠中淬炼出永恒。
137
感受力是帮助我们与人世发生联系而生发出的无数触角。
而洞察伴随于一铲铲的泥浆与碎石被抛出时,我们向永恒处一次次如此艰难地开掘与前行。
138
不是他向卖艺老人身前的碗钵中添加的几个硬币,而是他在屈身时为硬币赢得的与碗钵相触一瞬中的无声让你如此感动,并确信这人世依然拥有那从来的完整。
139
我希望能获得一种最单纯的人际关系,并因此重获一颗寂寞而饱满的心。
140
只要心正,一切就都是恰到好处的,就像你此刻眺望中所见的孤山与云亭。
141
我出生在千岛湖畔那个贫穷、闭塞,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我最初的知识来自村庄中一对亦农亦师的夫妇。直到二十四岁,我才真正开始接触西方的哲学与诗歌。又过了将近十年,我因一个契机系统地学习艺术,并帮助我不断地恢复一种最初的感受力。
年过四十,我就自身的传统进行补课,从四书五经到朱子、王阳明,并越来越深切地感动于一个曾经如此逼仄的村庄的最初赠予——善良、纯朴,而使得一个残缺的人世依然来得及修补。
142
没有什么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获允,并知悉那幽暗中的无穷。
143
万事万物都是在缓慢地积聚后而得以显现的这人世之奇崛。
144
当孩子们已然年长于我们相遇与告别的年龄,我们始得从这重逢中理解人世那从来的悲欣交集。
145
人世从来寂寞如漫漫长夜,而你一往情深似一粒皎洁而微茫的星辰。
146
我是突然间意识到并惊诧于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处于一种极度焦虑中,在一种时代的症候广为人知之前。是诗歌,还是经文终于带给我拯救?而我甚至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获得了一种淡淡的欢喜——那“无色声香味触法”处的微甜。
147
不是挥霍,而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成就了,江山处处之胜迹。
148
不是贫与富,所谓的贵贱是你在白发苍苍时能否依然拥有,一张如是清癯的面容?
149
越来越OM3YiseciOFbsrS6W7rhiQnH2+9ZkwPrfnyofh7NVKE=多的人辨认并指出,那不断从你脸上浮现的,恰是汉语的温润。
150
文学说到底是为那些公开或隐秘的知音存在的,并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残缺的人世赋形。
151
是对那些细微,甚至是不可见之物的感受,决定了一首诗的有与无。
152
这个世界会好吗?而你不断追问的,是你能否终于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153
这注定是一个悲欣交集的人世。
当你知悉——无数的星辰在一个瞬间诞生,而无数的星辰又在同一个瞬间悄然消失。
154
诗是我们在凝神或忘怀中所获得的那些最初的悲与喜……
155
诗人必须成为一个宇宙信息与密码的接收及转译器,他必须凝神屏息,以不错失那来自时间与空间双重深处的召唤——那汩汩而出的悲与喜。
156
不要与周围,甚至是同时代人去比较。
而你又因孤往,因终其一生的徒劳,而终于说出一个圆满人世。
157
夜幕即将垂落,恰是这人世最苍茫时。
158
如果不是诗,又会是什么让你走出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并终于得以与这片冬日的枯荷相遇。
159
一颗慈悲而智慧的心一定会发现与见证,一个艰难而圆满的人世。
160
你必须在死亡中理解生,就像你必须从一片枯叶中萃取永恒。
161
所有的割裂与隔绝都源于我们的执着。
162
一种深深的敌意,源于一股如此倔强的清流在这浊世的突兀,而为更多人捎去的不适与惊扰。
163
爱自己,爱——神那从这无穷无尽的幻象中得以显现的通衢。
164
多少“兼济”成为一种伪装后的私欲。或者说,相对于兼济天下,你更愿意成为那个独善其身者,并立志于以这最微小的善熔炼出女娲手中的彩石。
165
一个对瓷器无感的人,他很难真正理解你,以及东方的文学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