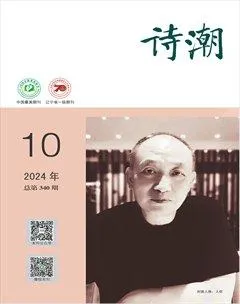生命缝隙中之小插曲

1
若干年前,某一仲夏正午。那时我们还是泱泱“自行车大国”呢。我让街角垂柳下一位连鬓胡子修车匠换条新自行车里带,后轮的,我回家扒拉几口饭菜,不久返回。
活儿已近尾声,正在安装车轮子。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像是有什么技术上的麻烦,必须重新卸下车轮,放气儿,把外带再扒开。
修车匠的红脸膛更红了,他背着我匆匆换好的里带是条补丁累累的旧带!和我淘汰的那条一样疮痍满目。我应当狠狠奚落他一番对吧,但上帝已帮我惩治了他。瞧着这个油渍麻花、满脸汗水、整天忙于养家糊口的修车汉,我把就要吐出的难听话又咽了回去。
他手忙脚乱地拿来一条新里带,重新为我安装,慌乱中手还剐破了,鲜血淋漓。
老话果然不是白老的,“人在做,天在看”。我可是不敢不信这个,谁若还有胆不信,那就继续你行你素,看看能否侥幸逃过天之巨眼?
2
21世纪20年代初某个冬日,我刚排长队扎完一款疫苗,在附近报刊亭买了一本《收获》,之后和老妪约定,再有新刊,电话通知。
我说了手机号,老妪输完后说:“我有你的电话呀,你在我这儿买过《当代》吧?”
我问她在她的通信录上我叫什么名字。她给我看手机,我叫“当代男”。
老妪又在手机上为我重新命名,现在我又成了“收获当代男”。
3
距此段文字公之于世已有二十余载,一个深秋之夜,我陪舅哥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打点滴,他得了急性肠炎。
环形急诊大厅里灯火通明,有好多张病床和好多急诊病人及亲属。有一张病床前围拢着十几号人,男女老少都有,患者是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平素一定快人快语。她大概刚从一道鬼门关闯过来,兴奋地戏谑道:“今儿死可好,人儿全,连干儿子都来啦。”
午夜将至,大厅静了会儿,很快又有新的戏剧上演:一个吞了大量安眠药昏迷的失恋女孩儿被推了进来,一个遭遇车祸的中年男人被抬了进来,一个浑身血迹、酒气和刀伤的斗殴小伙儿被背了进来。
隔会儿,又有一对肤色都较黑也较敦实的中年夫妇匆匆走来,男的状态很差,女的边搀扶他边向值班大夫介绍病情。男的只补充说喝完酒即开始胸闷,但情形显见着越来越糟,刚刚他还在走,这会儿已瘫软在地。
他吵着要大便,女的小跑着取来医用便盆,他又说要吐。他真吐起来,便盆派上了用场。
他的床位离我们很近,因此我是有证实资格的目击者。
很快地,在护士的来回小跑中,男人身上已插上好多管线,闪闪烁烁嘀嘀嗒嗒的监测仪也架上了,鼻腔还塞进了氧气管。他再也无力吵闹了,一肚子对人生的感慨我猜都堵在了嗓子眼儿。
后半夜了,他的心脏状态已貌似平稳,梳短发、穿紫色暗花毛衣的妻子伏在他身上啜泣着。
我竖起耳朵偷听到她哭腔说出的一句话:“等你好了,咱啥也不干了,要那些钱有啥用啊?”
4
我父我母私下里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那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来自民间,更不来自政治话语。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流落乡间数年后的某个夏日晌午,园子里三分之一人高的玉米刚被他们锄过草,主食为玉米面的午餐也已被他们吃过。我父半卧在秫秸炕席上眼皮开始发黏,我母却为什么事情大笑起来。笑声击碎了我父的小憩,他从茅屋里间走出,睡眼惺忪地对我母说:“一只小虫子睡觉,也应当受到尊重。”
我母笑声继续爽朗,随口接道:“老虫子,把里屋的针线笸箩递我!”
5
清晨的回笼觉里,又做了个梦,梦见与林雪、李犁两位诗人老友共商即将到来的文学人春晚事宜。我提议我们仨来一个男女声三重唱,还很少有俩男一女的三重唱呢吧?诗人林雪的唱功一点问题没有,她曾唱过难度很大的《孤独的牧羊人》,每个层层推进的段落都不含糊,最后一句大起大落又快得很的收尾“雷依奥多雷依奥多雷”,她的音准像坐过科的。诗人李犁的唱功有没有问题呢?多年前酒局欢悦时,我们只听他不时唱出两个字:“生活!”却不起立不捏金话筒不多唱一个字。那是某部电视剧主题歌头一句的头俩字,我们对他的音乐记忆也仅限这俩字了:“生活!”(但在梦里我认定李犁也是位有广泛适应性的歌者。)那么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李大诗神须抓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仨攒成一首歌词,我再谱成三个声部的曲子。然后……然后……我还没听到文学人春晚的开场锣鼓,就醒了。七点一刻,窗外已大亮。
6
午时读着卡夫卡,不觉间打了个盹儿,居然也像老卡一样梦幻起来,却见影视大咖张译正要用我的紫竹京胡为我拉弦。我对他说太高的也唱不上去,就唱段“在粥棚(正与磨刀师傅接关系)”吧。张译先拉了几下里外空弦,听上去还挺刚劲,是位腕力不错的硬派小生,就看他的左手指法了。可忽然,他停下来,提拉起我那把宝贝京胡,瞅啊瞅地鼓捣起来。我问他咋了他也不回答,只管使劲拧啊,拧啊。我说你可轻着点儿,别拧坏了,好几百块呢……话音未落遽然醒来,却是南柯一梦。
7
午后的小憩不会超过二十分钟,却常做些有悖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怪梦。方才的梦里浮现出多年前的一幅旧景:在京城胡同清晨排长队等候入厕。这正应了一则经典谜语:上厕所站排——轮蹲(伦敦)。而在梦里,男男女女鬼也没使神也没差地排成了一队。好不容易排到公厕门口时,我却转身高喊:“我愿意把机会让给我心仪的女神!”
8
偶见某网站有一奇文,本人恰在其中。那是关于我的长篇小说《把我的世界给你》的介绍,但又古又怪的文字已不像是写给此一时空的人了,譬如将我简介中的“乡村教师”写成“农村西席”,这还真有典可查,“西席”即早年私塾的代称,主人宴请私塾先生时坐东席,塾师坐西席;再如生僻得几近死亡的“■”(读交革)——“情绪■”(情感纠葛);“毕业”则写成“卒业”,简直就是民国范儿了。
还有更奇葩的呢,文中将我敬重的文学批评家孟繁华写成“文学指斥家孟富贵”,将“长篇小说”写成“长篇幼说”,将“发表小说处女作”写成“宣告幼说童贞作”,将“考场”写成“科场”,将《把我的世界给你》写成《把我的宇宙给你》,等等。
我很想知道这是何方神人意欲改写给何方俗人读的,但是无解。
9
20世纪90年代初,新型室内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开播,荧屏前的青年观众笑声不断,有的甚至从沙发笑翻到地板上,中老年观众则对该剧的“不严肃”“有什么教育意义”动了肝火,不仅拒绝“投入地笑一次”(主题歌首句),对不拒绝者也怒目而视。
“我只看了一点儿就看不下去了,所幸没受到更大毒害!”“我一听说糟得很,就一点儿都不想看了!”
冬装已显稍热的时候,某天午后,沈阳电视台搞了一场对该剧的观众大讨论,我受《鸭绿江》文学月刊主编老迟委派,前去参加活动。
女主持人先让大家发言预热,几十名文化界为主的观众中,青年与中老年的比例大约1:2,我属于少数派的青年阵列。试讲时,仅看了很少很少的中老年观众对该剧的“社会危害性”“文艺向何处去”却阐发出很多很多。只有我和几名(总共不会超过5位)青年观众明确表示了对《编》剧的赞赏。
该动真格了,女主持人宣布,对《编辑部的故事》持肯定态度的请坐到我和另几位青年观众一侧,一会儿正式录节目时先讲。
这时,好玩的事情发生了,一批中老年观众纷纷涌到我们阵列,灯光亮起时态度180度大转弯,表情和说法都翻了个个儿。而即使没入我们伙儿者,仍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也一个不剩了。
10
养生专家们常在报上疾呼:“不要养成药物依赖!”我们这些暗存长寿野心的凡夫俗子,随即从“药物依赖”走向“专家依赖”。
众专家的建议都是有教科书依据的,他们肯定是为我们好才不停地给我们支着儿的。增寿之路如马拉松赛跑,不管每个运动员能跑多远,专家们都在一旁击鼓不止,为我们“加油”。我们得领情,不能忘恩负义地说,因为场外叫喊得太厉害我们才跌跟头的。
但若一招一式全向“健康指南”看齐,一举一动全像电脑软件一样提前设计好,离快乐怕是会越来越远,特别是不期然的快乐。
一部分专家说不要发怒,因为“怒伤肝”;另一部分专家则说该怒不怒,就要抑郁成疾,因为“忧伤肺”。这让我们进退维谷。一部分专家说人应当高兴,那会使身体分泌一种良性激素;另一部分专家则说不要太高兴,否则血压和心脏受不了。这又让我们左右为难。
某一年,不避人接吻遭致万炮齐轰,专家们说即使不考虑中国国情,接吻至少不卫生,部分艾滋病菌即是通过口腔传播的。但没几年,养生报刊上又说,若将接吻爱好持之以恒,可获如下诸般益处:其一,比拒斥接吻者多活三到五年;其二,坚守工作岗位较少请假;其三,交通肇事率低;还有其四(这条最令吾神往),收入比不接吻者高百分之三十(另一说为高百分之二十)。
如此双向训导更让人心猿意马,我一直定不下来到底要不要做个接吻发烧友。
古时有一花发长者,一天到晚背着手在闹市上溜达,东张西望。后来我们得知他就是当年的健康问题专家。一日逢十,又是个热闹集市,绵延数里尽是卖吃喝及买吃喝的人丛。有一乌发呆汉远路而来,口燥得冒烟,连价都不砍,买下一堆梨并一堆枣,撩起长衫,急火火兜到参天古树下,席地而坐,大嚼开来。旧俗有新婚伉俪不食枣梨之说,因为枣梨会令其“早离”。
该呆汉要么尚未婚配,要么拿家庭不当回事儿,但他偏又是个珍爱生命者,事事信守养生原则。若将今日小报通过“时间隧道”遥寄给他,料他最先读的准是“健康指南”。
花发长者背着手溜达过来,见到眼前这一幕,捋着美髯开始履行养生专家天职。他蹙眉告诫呆汉,食梨益齿而不利脾,食枣益脾而不利齿。呆汉火速从之,将梨一只只嚼碎后吐了满地,将枣一只只囫囵吞下。
这个典故已讲述了上千年,后人的关注重心则只向一方倾斜。
古今健康专家给出的指令大概都是对的,但他们似乎不喜欢揭示生命运行的多种可能性。有的专家说,运动必须在傍晚,晨练和午练都不好。有的专家说,午睡易诱发中风。有的专家说,饭后一小时才适于饮不浓不淡不冷不热不多不少的茶。有的专家说,即使稀如啤水的低度啤酒,每周也只宜饮545.5或550至645.5或650毫升,并且务必要使他们指定厂家生产的专用刻度杯。所有说法的商量余地都很小。
由此,我酷爱上了多年前一个电视专题片:央视记者到南国某大山深处探访一位长寿阿婆,那一年她已一百有四,若用北美早期印第安人的计岁方式,老阿婆已活了一百零四次栀子花开。她向记者介绍自己的若干“长寿经验”,却少有能中专家之标者,其中一条是经常骂骂从她门前来来往往的后生。他们都不和这老小孩儿一般见识,连别人骂不得的村乡干部也一样,大家都笑笑一走了之,这让老阿婆爽呆了,骂尽兴了便吧嗒吧嗒抽上一袋旱烟。面对惊叹不已的京城人的话筒和摄像镜头,老阿婆的成就感更强了,露着豁牙子呵呵笑称,她一抽烟就不咳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