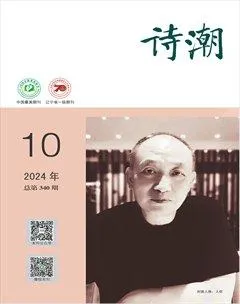小自然 [组诗]
杂 诗
书页被淋湿,印刷体们开始泛绿。
为一个梦开花,他继续在春夜无眠,
薄薄的雨水潇潇,卧室是旷野的大床。
枝叶仿佛都有了,一首诗,沙粒中的
小宇宙,一万年的修辞之光终归徒劳。
只有他一一数过的种子才被生平召唤。
田野调查
鞋带系住了新池塘,出来走几步透气。
水里多云,月亮浸泡白内障的眼球盯着看。
一首古体诗也看不到,乐府的鸟也没有,
楼堂馆所平仄一声,阴性草木等待着商业繁荣。
隔山隔天眼,公路出鞘了,大巴日行千里。
戴墨镜,听蓝牙,刺客信条没有骑驴的慢时光。
桃源捉迷藏,躲不过猫,百度摆渡里像条船。
来了就长一岁,一分钟春潮带雨已不是六十秒。
寒食节
晨练时枯叶从雪被的捂盖下释放出来。
风颠簸这些昨年的小心脏,耳朵听见了跳动。
视力顺着风筝的努力也提高了湿润的四月天。
慢慢恢复着肺,呼吸腐烂的和新鲜的气息,
你感到了解放。如此泥泞,冗冬怎能不软弱?
虽然寒凉,冻土带还是站在必然转折点这一边。
橙色园艺工们在小公园的树木下走动。
他们用铁耙刮厚厚的死树叶,堆起小坟冢。
审美的洁癖,仅为一公顷能见度的草坪。
七点钟,枯叶被装进编织袋倒进红色垃圾箱。
不能彼此回去,景观,以及不自然的小自然。
黑树干仍然是一炷烟,从泥土里升起却又经久不散。
赵 佶
跟着他,带着笔墨纸砚。
一群宫女和侍臣,迤逦在白茫茫雪原,
灰色的苍穹下,像纸上的淡墨点儿。
他们一直向北。停下来时,
他流着鼻涕,单薄的绸缎瑟瑟发抖。
用舌头舔着冻笔墨,
在一方锦缎上,他画一路风雪。
我说,你知道吗?你被流放到北方了。
他的嘴唇有一层黑墨,胡须里牙齿很白。
他说:谁敢流放我?这断无道理可言!
你看这千里江山,都是我画出来的,
我要画出完整的王土。他指点即将完成的画,
白色苍山若隐若现,风雪中全是行走的
小小瘦背影。我用手机给他们拍照,
想发抖音,但什么影像都没有。
风雪漫卷的北国原野,只有他画铺成的
下陷的地窨子,无边刺眼的白色锦绣和寒冷。
自闭症
夜里的城池不明来由的孩子游荡着,
心事重重的成人成为他们体内的孩子。
客栈,寄存了一些南来北往的灵魂。
房间铜钥匙孤单悬挂着,开锁的肉身,
带来一场骤雨。没有谁愿意写忏悔书,
光脚的小街,路灯下穿水靴的都是帝王蟹。
读《海奥华预言》
实际上地球与月球,
像一对核桃包了浆,
彼此缠绕的文争和武斗,
像宇宙里体面的夫妻。
谁是运行联姻的黑手党,
看燃烧的太阳就知道了!
跨出银河系比骆驼
穿过针眼儿还难,
再向外移动是超光年的。
星球各自的错位中,
一粒尘土生一粒尘土落,
多大的体积算细菌?
多小的细菌算体积?
坐地日行久了,
又被深井所困,
如蟾蜍日攀三尺掉四尺,
肉身的重力跳不出肉身?
海奥华不是想象的,
黄昏金星疏远地球,
距离的立场是小看了对方。
相对论果然有真相,
灵体永远都不会消亡。
高贵的辉光和灵性知识
主持着无微不至的浩瀚。
海奥华,这个九级星球,
肯定是宇宙里的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