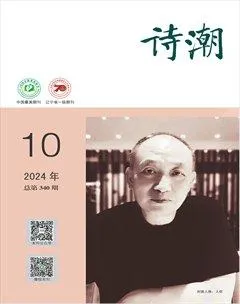诗六首
无目的的歌
三月肤浅的样子。从消融的白雪下
从合欢树枯萎而颤抖的枝柯间
从一只鸟脱离了群居的整体,又回到
孤独的状态,从小镇越来越窄的街道
那上面,拥挤的人们催促着焦急。
我关上窗户,在没有阳光的日子
似乎做什么都不合适,唯有书本让人安静。
三月进入春天的心脏,但仍然充满未知。
升温的道路,重型车出现,并碾过
对抗的热情,这时候,残存的冰雪也丧失了
污浊的身份。
这是似曾相识的三月,但显然不是去年
也不是前年的三月,它回来,在我的记忆中
寻找一个词语,或者歌声。
但仍然充满未知。因此
任何一个三月,对我而言,都是新的
是新的一个词语,或者是一首,新的歌。
地 址
我忘记了昨天去过的地方,但我仍然
会深深记得,某个陈旧的地址。
当年寄往的一封信,至今没有回音,像是
一枚落叶,随着流水不知漂向了何方。
而我,从奔马墩出发,经历了白莲寺、螺蛳壳等
标志着我成长的地名,我的见识在风中摇摆难
以定型。
我经历了少年和青年,初识了农业的启蒙课,
以及
沉默和清朗的感情生活,拓展了我的本土版
图。
我的中年和老年,并没有超越飞机的轰鸣音,
所有的
城市都在我的梦中遗失,无法具名。
无数的地址潮起潮落。此后,更多的地址
被圈养在我循环的血液中,不断重复着回忆的
命题。
而且,几个模糊的地址逐渐变得明晰。
另有一些新的地址,我确信它们正在赶来
其中一个,带着黑色告别的语言在迎接我的路
上。
夜 宴
并不是每个夜晚都让人舒适,让人高兴
一个人穿上休闲服,在厨房煎鱼
时针走向二十点,无声漫步在它自己的规则里。
那青鱼是腌制过的,被剁成小块块
用淘米水浸泡三小时可去掉少许咸味儿
用文火慢慢煎,华丽金黄,小心地翻身。
妻子久不在身边,但日子仍然在婚姻的状态中
爱情变得模糊,或者蹉跎成消逝的电波。
灯光明亮,客厅里的电视放着,声音调小了
一个人举杯,没有对饮的人,三月站在窗外
春风的长笛从窗前吹过这夜的安谧。
音乐响起
音乐响起,但并不令人快乐。
这取决于心绪的波动?
我在早晨
打开手机音乐,有时是晚上,比较而言
早晨的旋律略显明快。
某个时刻,并没有实体的乐器,也没有
任何发声的音响,音乐响起
只是在我的脑海中。
比如昨夜
我躺在床上迷糊,有一首歌
突然来到副歌的复调,循环在我脑际,将
一个人的房间,掀起浪潮。
忍耐以一种惯性贯穿了我们的生活
桉树林分开一条路,从中穿过,我牵着老黄牛
去溪边饮水。黄昏降临
炊烟飘荡在村庄上空,缠绕着归巢的燕子。
这是三十多年前,在将
那头老黄牛卖给屠宰场的头天,我最后一次
牵着它去饮水时的情景。
日子的脚步不紧不慢,一头牛的情绪总归是
平和的,就算它老到不能下地劳作,也保持着
惯常的沉默。
我死于1984年的父亲也是一头老牛,风箱般咳喘
证明着他肺部的病变,除了咳嗽和劳动的响动
他几乎不发声,同样保持着惯常的沉默。
忍耐以一种惯性贯穿了我们的生活。
我也遗传了这种特质。也是一个能将激情的沸水用沉默寡言来调适成冷水的人。
如今,某个恰当的日子会启动我记忆检索的开关:
有一头老牛,仿佛一直陪伴在我身边,黄昏时
我和它一起去溪边饮水。抬起头时
我们双目对视,我们的眼眶里蓄养着
同样晶莹的泪水。
尽管甘蔗长着锋利的叶片
有时候甘蔗林无风自动,叶片互相摩挲
发出细小声响。守夜人警惕地
从值守棚走出来,打开手电筒扫描一番。
夜色黑黢黢总让人怀疑
是有人进了甘蔗林。田鼠们也喜欢在夜晚行动
茂密的蔗林是它们的乐园。
甘蔗长满锋利的叶片,内行的人应该长袖善舞
甘蔗以锋利的叶片来保护自己的甜
人用全身包裹的布料来遮蔽自己的身体
月光下的甘蔗林充满神秘的气息
一些轻微的响动都会被放大。
守夜人并不能确保甘蔗不会损失,但他们知道
吃的东西总归是要进入嘴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