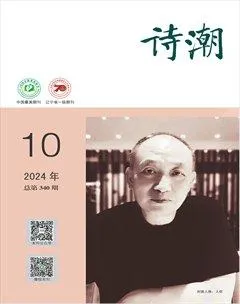寒冬记 [组诗]
又下雪了
又下雪了,但
下雪并不代表冷
雪更在乎慢
和干净
并不在乎你的体感
在零下三十度的某刻
结冰或直线滑行
它带来一个诗人死去的消息
但忽略眼泪和悲伤
它加速一个作家的心跳
或癌细胞
却从不悲悯
它只用慢
和一种更干净的白
代替亡灵哭泣
和遗忘
冬至以后
冬至以后,嗓子更疼了
头晕日益加重
润喉片里的冰片
强压着舌苔下的焦虑
脉若游丝,却仍然
如鲠在喉。只有药片
可以作为虚拟的抗体
聊以自慰
他们说应该庆幸放弃从医
但我懊悔,二十年前为何改行
作为一名医生,至少现在
我就可以给众人聒噪的咽部
安装一个隐形的消音器
寄往北京的包裹
寄往北京的包裹里
应该有一封信
但那本旧书里的标记
仅用于遗忘
问题是上海也冷
车里结冰的矿泉水说明
你好久没有写诗
一个词体内的温度
仅限于活命
大寒之日
我抱着一本《甘州府志》
却无法给大汉的饥民
送去一颗粮食
又下雪了
我只能告诉你
河西走廊的冬天一直就这么冷
但有史以来从没有在史书里
冻死过一匹马
他乡下的母亲
他乡下的母亲半夜出门小解
在院子里摔了一跤
一根股骨和八根肋骨全部摔断
一场雪本不该这么绝情
一场事故也不该这么轻描淡写
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雪还在下
天空也需要表达绝望
给久病不起者一个清清白白的葬礼
光照进来
光照进来
忽然想起那年
一次漫长的旅行
躺在绿皮火车的下铺
读一本诗集。仿佛词语深处
旅程永无尽头
阳光透过车窗
刀片一样飞进来
切割着书页上的诗句
我就那样静静躺着。多年以后
直到火车的轰鸣完全静止,才感到
莫名的疼痛从胸口缓缓蔓延出来
一些人死去的消息
一些人死去的消息
之后是一些人病危的消息
仿佛总有陌生人
每天都在忍受着煎熬
这于我是宽恕。因为陌生
我有理由忍住眼眶里的泪水
假装死亡和怜悯与己无关
像天空下着雪,倾泻,然后归于平静
我只是个深夜写诗的人,偷偷
为这个世界和自己寻找些许光亮
哪怕一小块黑暗都让我觉得
无能为力也是一种难以宽恕的罪
去乡间买鱼
去乡间买鱼
突然惊起荒草中的
两只白鹳
它们匆忙飞起
两根细长的黑腿
像是在天空画了个等号
几秒钟,太短暂了
天空还是那么空
旷野仍然一片肃杀
仿佛它们只是种幻觉
一闪而过
仿佛只有等号
是真实的。只有你和我
在无边的旷野里
飞——
是真实的
根本不存在
对虚无的陶醉①
注:①引自波德里亚《冷记忆》。
铲雪的声音
铲雪的声音早上响过一阵
下午又响起。铁器刮擦着路面
同时也尖锐地刮擦着我的耳膜
一天两次,我的耳朵感受着人们
重新走上街头的兴奋,也感受着
自由赋予噪声的更多意义
对声音的敏感来自寂静
居家半个月后我不这么想了。有时候
雪顽固不化是另一种慈悲
冬天的湖
冬天的湖应该是这样的
青黛色,掩藏着更深的绝望
虹鳟鱼在水底,像水
自己的阴影,随光浮动
有时,黑色的身躯
突然跃出水面
仿佛隐匿已久的自由
终于找到了出口
但金鳟无畏
修长的身子,逆流而上
像一道道闪电
竭力想要表达什么
养鱼人说这种鱼
非干净的冷流水不能存活
养在鱼缸里不如
当场杀死
池边的荒草上雪还没有化
绕池三圈,我始终踌躇不定
捉哪一条鱼回去下酒
都觉得是一种罪恶
以果树为例
以果树为例,十一月和十月
真的没有可比性
枝头上的落寞和内心的丰腴
恰好成直角。凋落是宿命
没有什么值得惋惜。中年以后
坦露是一种美德。冬季呈现的萧瑟
更像是富足后的减法。山楂血红
冻果中饱含着浆汁
没有跌落的果子
抬着干瘪的头颅
环顾四野。任何角度
都一览无余。父亲在果园里
被落日拉长的背影就像上帝
在祝福那些被岁月遗弃的果实
据 说……
据说金丝雀时常被带到矿井
北美金柏对寒冷具有依赖性
温暖对北极熊的伤害大于猎枪
一个人死于短篇小说
比死于肺炎更无辜
有一次在梦中,一把斧头
突然砍进她的脑袋,她清晰地
感觉到自己已经死亡
却并没有感觉到恐惧
中年以后,她对死于安逸的设想
并不满意,时常在梦中
借助亡者之口
修改自己的墓志铭
“每个人都是神为了感知世界而设计的一个器
官”①
她觉得至少应该像一只鸟
或一棵树那样
作为一个肺细胞去感知恐惧
死亡才是有意义的
注:①语出博尔赫斯小说《神学家》。
可鄙的
总提到绝望但一辈子不为一个真正绝望的人写
一首诗是可鄙的
总在庙里上香却对庙门口躺着的流浪汉熟视无
睹是可鄙的
对一个躺在街头裸露下体对着一个年轻女人的
照片放大提琴曲的人指指点点是可鄙的
训斥一个疯子就像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是可鄙的
总感觉自己无能为力只有眼泪也是可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