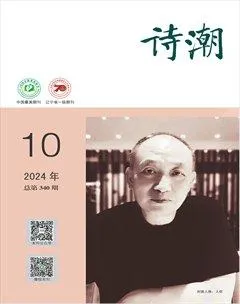明月之心 [组诗]

明月之心
我居住的地方更加遥远、寒冷了。黑色的麦子
等着收割。
女人们偏爱红色的鞋子和
灰色的房子。她们终日搬运夜色,用它喂养自己的马匹
距离语言最近的地方,潮湿,像一片沼泽,充满
泥炭和死亡的味道
只有那枚皎洁的月亮用它酿酒
琥珀色的酒液在空中流淌。有时,它从一侧
倾倒进人间
把人间当成它的酒器
书 架
奈良的小鹿躲在第三层左侧第六本书里。
伊豆舞女的一泓泉水
属于旁边的另一本。我喜欢的蝴蝶藏在第四层,它制造的
效应一直波及第二层,并且在《海底三万里》
伪造了
一艘潜艇。与那只蝴蝶相比,年轻的父亲夹在
《叶之震颤》与《刀锋》之间
那年他27岁,有帅气的外表和无量的前途。第
四层
属于1982到2024年
跨越四十年的集邮册以及影集和书信。几年
前,那里
被杂物占据:纪念币,相框,针线盒以及
哑了嗓子的唱片和磁带
虽然只有四层,却占据了卧室的四分之一,
那些
书籍和杂物每天晚上看着我
与我一起睡觉,做梦,变老
雨 水
带着某种幸运
它们落着
落在叶片松针以及一个孩子的眼镜片上。落下
的时候
十分轻微,就像某位画家的笔尖:
在烟雨朦胧的湖中出现了一座岛,一间房子,
一个女人
女人的发簪是带刺的红玫瑰。然后水珠从
画面上滚落
滴落在一双皮鞋上
或许整个六月都要将此度过
把潮湿的记忆留存下来
寂静的部分
清晨,寂静属于一只麻雀,它安静地
站在窗台
看着不远处的香樟树。房间里熟睡的人因昨夜
的一场酒
而牺牲掉整整一天。此刻,寂静属于一场
小雨。它安静地
落着,没有任何声音,静悄悄地浇湿土地。
走在上面的人
也是静悄悄的
从南到北或者从东到西。他们选择
悄无声息
用脚步丈量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喑哑的东西
紧紧收住带光的部分,生怕被谁发现
直到午后
它们才会破土而出,接受阳光的恩赐
美丽的事
曾经我们因不期而遇伤感。十八岁的周末和
一枚
荷尔蒙的指南针构成了一艘船
曾经,八百磅的力量施加在一个人身上:
他有八百亩玉米地
还有八百亩国土
始终与家人一起——
他的思想也有八百亩,但容纳不了自己的妻子。
他,
选择消失更多为了坚持尽管人类活在数的世界
那些终极的话题一直等着解答,包括
那些难以证明的
谎言和真实。黄昏将至,踢球的孩子被母亲喊
着回家
他们的书包藏着的内心秘密大于母子亲情里的
一切
谷 雨
缝合天空的人正在经历变声期
他不得不为自己
准备了一副新嗓子
为了阻止雨季的到来,他加紧工作,用更多的
针线
将飘浮在天空中的白云固定
只有黑夜来临时,
他才会忙碌自己的桑葚园。黑色的桑葚是他的
眼睛
现在它们已经
变红。当天空被缝合,他就来收获甜蜜的果实
铁 轨
废弃的铁轨安静躺着,它并不期盼
火车的到来
反而与野草为伍
三十年前,它位于阜新与葫芦岛之间,每天接受
九列火车的碾轧。黑色的煤炭撒落在它的身旁,
等着孩子们捡拾——
后来它来到山东
距离火电厂外三百米的地方慢慢生锈,像
一截死人的断肢
没有小偷觊觎它:实在太重了,哪怕切割机和
角磨机也把它
当成了敌人。岁月的肆无忌惮没有让它服软,
让它
更加坚挺。一条
骨裂的痕迹出现在它的腰腹部,多像那些
桐油干枯后的枕木
灰 尘
灰尘是我也可能我是灰尘,当我喝到第四瓶
啤酒
没有一个人与我说话
我更像一只怪兽。疏离,覆灭,时代的鸿沟,
把一罐啤酒
变成雕塑。想起我们在春天的湖边散步
抛弃各自的烦恼只为这一瞬。我们彼此
没有一张合适的照片,却有
病假和
一身伤病。朋友们唱着的
生日快乐歌更像在伤口里
开了一座超市
热闹却空虚
斑马线上
黄昏,斑马来到一条公路,只为驮着一个盲人
穿过
他收回探路杆
摘下墨镜,像一位诗人。整座城市被
黄昏染成浅红色
仿佛
塞伦盖蒂的傍晚
有时,生命更像是一道加减乘除:仿佛只有做
对的人
才会拥有
整整一天。那些等着铃声的人
也会等着属于自己的斑马,镶嵌在城市的
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