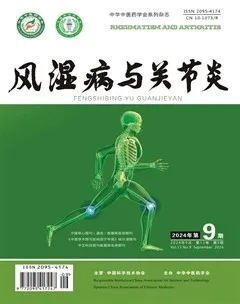加味除湿定痛方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病因病机证治规律初探
【摘 要】 中医学中痛风与当今之痛风性关节炎的疾病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但两者在病因病机及证治规律方面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中医典籍中所载之经典方剂或可成为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有益补充。《丹溪心法》中专设一方用于治疗酒湿痰痛风,该方被后世沿用,并更名为除湿定痛散,可湿热清利、经通络活、气血周流,达祛风除湿、消肿止痛之效。以除湿定痛散为基础进行加减化裁,用于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痛风性关节炎;加味除湿定痛方;酒湿痰痛风方;除湿定痛散
“痛风”首见于《名医别录》,曰:“独活味甘,微温,无毒。主治诸贼风,百节痛风无久新者。”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所谓之痛风与当今所论之痛风性关节炎(gouty arthritis,GA)、类风湿关节炎等风湿病的病证特点有较多相似之处[1-2],并在其医学著作中对痛风病因病机和证治规律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朱丹溪所述病因涵盖了先天禀赋、外邪侵袭、内伤杂病、饮食偏嗜等,涉及风、寒、湿、热、气、痰、瘀、虚、酒毒等多种病理因素;并针对各病理因素常兼夹致病的特点,提出了以祛风散寒、利湿清热、行气化痰、活血补虚为主的通治大法,以及通治痛风的“大法之方”(由苍术、川芎、白芷、天南星、当归、酒黄芩组成),并在此基础之上创制一系列方剂[3],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4-5]。
值得注意的是,《丹溪心法》和《丹溪治法心要》中将“酒”列为重要病因之一,并专设一方用于治疗酒湿痰痛风。而饮酒作为目前已知诱发GA最常见的因素之一,酒湿痰痛风方可契合GA病机发挥治疗作用。本文从除湿定痛散治疗痛风的因机证治,及加味除湿定痛方治疗GA的证治规律和临床应用经验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GA防治及传统经典方剂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GA的临床特征及与“酒湿痰”的关系
1.1 GA的临床特征分析 清代医家张璐言:“按痛风一证,《灵枢》谓之贼风,《素问》谓之痹,《金匮》名曰历节,后世更名白虎历节,多由风寒湿气,乘虚袭于经络,气血凝滞所致。”该论述将痛风病机归结为机体正气不足,复感外邪,以致气血凝滞所致。虽古今痛风概念不完全等同,但在病因病机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目前认为,GA病机总属本虚标实,本虚责之于“肝脾肾亏虚”,邪实则常见“痰浊”“瘀血”和“湿热”之邪内盛[6],且标本之间常可相互转化,互为因果。“痰浊”“瘀血”是GA发病过程中的重要病理因素,两者均为阴邪,其性重浊黏滞,常互为因果,易相互胶结,形成痰瘀互结的病理状态,难以泄化,日久而成“浊瘀”之邪;若流注于筋骨关节,可见关节结节畸形,甚则溃破,渗溢脂[7]。“浊瘀”之邪内伏,若因饮食不慎,或遭外感外伤,则可引动伏邪,诱发GA,如《灵枢》所言:“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8]
GA急性发作时,患处常呈一派火热之象,如关节肿胀,皮肤焮红灼热,伴有酸痛或剧痛难忍等。但就整体而言,部分GA患者的证候特征复杂,湿热与寒湿常难以界定。治疗时,若一味强调湿热之证机而过用清热燥湿药,则急症虽除,却有败胃伤正之嫌,或病势虽缓,但日久难愈,甚至变生他证,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辛散温通之法治疗GA常可获效[9],乌头汤、防己汤、附子理中丸等散寒除湿的方剂也常用于治疗历节病[10]。治疗过程中,患者在急性发作期患处常见肿痛,说明此期确有湿热证机,但整体与局部之湿热仍需明审细辨。若患者整体湿热证机较显,过用辛温或可加重病情。因此,遣方用药当兼顾虚实寒热。
1.2 “酒湿痰”在GA发病中的作用 “酒湿痰”旨在强调GA之病因病机。《伤寒论》中论述桂枝汤的服用禁忌时指出:“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陆渊雷云:“酒客,谓素常嗜饮之人。”《格致余论》曰:“醇酒之性,大热大毒。”古人饮酒又多为温饮,易化热酿湿,并可损伤脾胃,导致津液输布失常,最终酿生湿热[11]。正如刘完素在《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论述湿邪的产生机制时指出:“湿病本不自生,因于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行,即停滞而生水湿也。凡病湿者多自热生,而热气尚多,以为兼证,当云湿热……。”亦有学者从现实角度进行解析,认为古今饮食习惯差异较大,当前人们多喜冷饮,长此以往,可损脾肾阳气,因此当前酒客者多寒湿[12]。此两种观点相左,却有相通之处,即长期嗜酒可损伤脾胃,致痰湿之邪内生。痰湿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伏不去,使气血凝结发为痹证,并在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诱发疾病。诚如《灵枢》所载:“贼风邪气之伤人也……尝有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通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
2 加味除湿定痛方的来源及组方分析
加味除湿定痛方是结合GA的临床特点,在除湿定痛散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的经验方,经临床检验疗效显著。
2.1 除湿定痛散方药解析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痛风篇》中专列治疗酒湿痰痛风之方,载曰:“又方治酒湿痰痛风。”后接药物组成和服法,“酒炒黄柏、威灵仙酒炒各五钱,苍术、羌活、甘草各三钱,陈皮、芍药各一钱,上为末。每服一钱或二钱,沸汤入姜汁调下。”但并无方名。《丹溪治法心要》中言:“饮酒湿疼痛风。”后接药物组成和服法,且与《丹溪心法》中所述一致,但亦无方名。至明代,医家李梴于《医学入门》中记载痛风的辨治方法时沿用了朱丹溪酒湿痰痛风方的药物组成,但对各药物的剂量及服法进行了调整;明代另一医家芮经亦在其著作《杏苑生春》中收录了朱丹溪所创之酒湿痰痛风方,且沿用了原方的组成、剂量和服用方法,并将其更名为除湿定痛散,仍用于酒湿痰痛风的治疗。此后,明代医家杜大章在《医学钩玄》中则将除湿定痛散描述为用于因饮酒过多所致之“肢节中风作痛”的方剂。
除湿定痛散中威灵仙味辛、咸,性温,可导可宣,长于祛风湿、通经络,止痛作用较强,并能消积湿停痰,《本草纲目》谓其治“风湿痰饮之病”有捷效。《本草正义》谓其:“以走窜消克为能事,积湿停痰,血凝气滞,诸实宜之。”《药品化义》谓其:“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中,致成痛风走注,骨节疼痛,或肿,或麻木。”黄柏味苦性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之力强,此一味药物亦称潜行散,可用于治疗湿热注痛,与威灵仙相伍,借其辛散走窜之性,可搜剔筋骨脉络中已聚之湿热,故两者共为君药。苍术味辛、苦,性温,可祛风散寒、燥湿健脾,使中聚之湿不致注于肢节为患,与黄柏同用,即为名方二妙散之配制,尤能清热燥湿,为治湿热下注筋骨、关节红肿疼痛之常用组合;羌活味辛、苦,性温,可祛风胜湿、散寒止痛,除风寒湿痹以通利关节,此二药共为臣药。又以陈皮和生姜理气消痰,燥湿和中,以助苍术除中焦之湿,杜其生痰之源;芍药和甘草相伍,《症因脉治》谓之戊己汤,功能调肝脾和气血,并可缓急止痛,制辛散药物之燥烈,以防伤正;此四药共为佐药。生姜榨汁兑服,可借其辛温发散之性助药力达于病所,以驱邪外出,故为使药。诸药合用,可使湿热清利,经通络活,气血周流,以达祛风除湿、消肿止痛之效。故本方所治之痛风,以风湿痰热留滞经络、关节,气血不得宣通者为宜。
2.2 加味除湿定痛方组方分析 GA患者的火热之象主要由“浊瘀”之邪郁久而化,并复感外邪外伤,或因饮食不慎,加重体内湿热,致使湿热之邪壅滞,阻滞气血运行,故引发疼痛,即所谓“不通则痛”。故治疗时,重心当在“通”。所谓“通”,即针对“痰浊”“瘀血”“湿热”等GA的病理要素进行治疗,旨在恢复经络气血的正常运行,从而缓解病情,即所谓“通则不痛”之治。然而,除湿定痛散并非专为治疗GA而设,其化瘀通络止痛的功效稍弱,不能完全契合GA病机特点。但朱丹溪“祛风散寒、利湿清热、行气化痰、活血补虚”之通治大法对GA辨治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加味除湿定痛方是在除湿定痛散的基础上加减化裁而来,该方由滇紫参30 g、威灵仙15 g、黄柏15 g、制天南星9 g、羌活9 g、白芷9 g、白芍6 g、甘草6 g组成。方中滇紫参又名小红参、小活血等,是云南茜草的根,《滇南本草》谓其味苦、甘、平,性微温,可“通行十二经”,《云南中草药》和《红河中草药》等地方本草则记载了其调养气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等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其具有活血通经、祛风除湿、镇静止痛、调养气血的功效[13]。威灵仙辛散宣导,走而不守,可宣通十二经,是国医大师朱良春治疗GA的常用主药之一[14],与滇紫参相伍可增强通行搜剔之效。黄柏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并能疗郁热所致之痹痛,如《兰室秘藏·腰痛门》言其功用时所述:“初得之时,寒也,久不愈,寒化为热,除湿止痛。”且借滇紫参和威灵仙通行走窜之性,可搜剔和宣散局部壅滞之湿热;三药相合,可促“浊瘀”之邪消散。制天南星味苦、辛,性温,具有燥湿化痰、散结消肿等功效,朱良春谓其长于搜剔深入经髓骨骱之痰瘀,是治疗骨痛的常用主药[14];羌活和白芷均可祛风除湿、散寒止痛,并兼具辛散发表之性,二药相合,可增强除湿止痛之效;白芍与甘草相合,可缓急止痛,并能制约诸药辛散走窜之性,以防太过伤正。诸药合用,可使痰瘀得消,湿热得化,气血条达,经络通畅,以收除湿消肿、通络止痛之效。
3 加味除湿定痛方临床应用经验
《至真要大论》云:“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张景岳将这一治则解析为:“湿为土气,燥能除之,故治以苦热,酸从木化,制土者也,故佐以酸淡,以苦燥之者,苦从灭化也,以淡泄之者,淡能利窍也。”《藏气法时论》曰:“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即此之谓。”国医大师路志正则认为这一治则即为“开鬼门,洁净府”的具体体现,并将其概括为苦温燥湿、淡渗利湿、疏风胜湿、清热祛湿等具体治法[15]。加味除湿定痛方参照以上观点,并结合朱丹溪“祛风散寒、利湿清热、行气化痰、活血补虚”的通治大法,全方以味苦、辛,性温之威灵仙、制天南星、羌活、白芷等祛风散寒药物为主体,取“以风胜湿”之意。在大队苦温药中配以苦寒之黄柏,以清怫郁之火而除湿热。脾喜燥而恶湿,湿去则脾运自健,此为“寓补于攻”之治,故方中未再专列淡渗健脾之药。白芍味酸,可从木化以制土(湿),并制全方之燥,以防太过伤正。此外,针对“活血补虚”之治,重用可补血、活血、通经的滇紫参,以代替朱丹溪治疗痛风的大法之方中当归、川芎。全方以苦燥温通、祛风止痛为主,兼以养血、清热。寒热平调,虚实兼顾,常用于GA急性发作期和类风湿关节炎活动期的治疗,尤其在患者整体辨证结果是以湿为主,但寒热难辨时疗效尤显。
临证加减:关节肿痛较甚者,加川芎15 g、透骨草15 g;湿热较重者,加虎杖15 g、苍术15 g、石膏30 g;寒湿较重者,加附子6~30 g、干姜15 g、桂枝10 g;关节活动不利者,加山慈菇10 g、土茯苓30 g;津伤口渴明显者,加南沙参30 g、淡竹叶10 g。
4 小 结
GA诊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已有多项指南和共识相继推出,但仍缺乏统一规范的治疗策略[16]。中医药治疗GA急性期以缓解关节症状为目标,目前认为,该期的核心证候为湿热蕴结证,但具体治则治法并无定见[6]。临证时部分GA患者急性发作时痛势不剧,以酸痛为主,疼痛绵绵不绝,并伴患处肿胀,且仅凭舌脉难以辨明寒热。推测可能与人们生活和饮食习惯的(下转第54页)
(上接第49页)改变有关;经常熬夜、嗜食生冷等起居和饮食习惯常可导致患者脾肾阳虚,内生寒湿,虽日久可郁而化热,但其病机根本仍为寒湿。故治疗时以苦燥温通、祛风止痛为主,兼以养血、清热。方药以加味除湿定痛方为主加减化裁,取得较好疗效。但该方的实际疗效和作用机制,以及发挥作用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仍有待进一步探明。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通过临床观察对其疗效进行验证,并以基础实验对其治疗GA的作用机制和发挥疗效所依赖的物质基础进行探讨,以期为该方的进一步开发和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方勇飞.痛风病名考据[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1,10(11):53-55.
[2] 秦涛,孟庆良.痛风中医病名考辨[J].中医研究,2021,34(6):49-53.
[3] 肖战说,殷海波.朱丹溪痛风通治思想探赜[J].江苏中医药,2021,53(6):12-14.
[4] 朴勇洙,张京,任慧,等.国医大师卢芳运用丹溪痛风方治疗痛风经验[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4(8):715-718.
[5] 肖战说,罗成贵,殷海波.朱丹溪上中下通用痛风方的研究进展[J].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24(2):126-129.
[6] 姜泉,韩曼,唐晓颇,等.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病证结合诊疗指南[J].中医杂志,2021,62(14):1276-1288.
[7] 朱婉华,顾冬梅,蒋恬.浊瘀痹-痛风中医病名探讨[J].中医杂志,2011,52(17):1521-1522.
[8] 冯博懿,韩亚光,龙文.运用伏邪理论探讨痛风性关节炎[J].中医学报,2020,35(9):1878-1881.
[9] 谢庆,韩智云,冮顺奎.经方辨治痛风研究进展[J].风湿病与关节炎,2018,7(8):77-80.
[10] 张璐.张氏医通[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474.
[11] 蔡嘉缘,阮善明.酒客病辨析[J].浙江中医杂志,2018,53(1):32.
[12] 唐可,黄兰莹,周杨帆,等.《伤寒论》酒客病辨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9,25(10):1346-1347,1376.
[13] 崔大鹏,张国伟,瑞欣.小红参的药理活性和作用[J].河南中医,2011,31(4):408-409.
[14] 朱步先,何绍奇,朱胜华,等.朱良春用药经验集[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0.
[15] 吴朦,杨燕,郑昭瀛.国医大师路志正湿病证治思想探析[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22,17(11):2170-2174.
[16] 张学武.痛风关节炎治疗中几个备受关注的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53(6):1017-1019.
收稿日期:2024-03-05;修回日期:2024-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