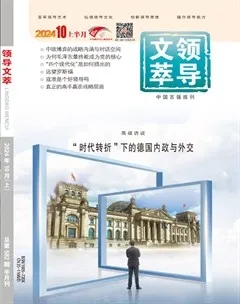一个被传统困住的改革派

1868年是日本启动明治维新的年份。明治天皇颁布诏书说,日本决定走“万机决于公论”之路,要打开国门“广求知识于世界”。
对清朝而言,1868年同样也是一个“广求知识于世界”的大好机会。在美国人蒲安臣的推动和率领下,清朝组建了第一支正规的外交使团,启程前往欧美。
志刚是总理衙门里的中级官员(总办章京),随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时已经50岁了。
出访期间,志刚遍览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德国、俄国的风土人情,见识到工业革命后喷薄而出的种种近代文明。这些见闻被他写入日记,后来整理出版为《初使泰西记》一书。
与之前随赫德前往欧洲的斌椿、张德彝等人不同,志刚在总理衙门任职,是一位典型的洋务派官员,所以他有一种自觉的使命感,知道自己的欧美之行不是为了走马观花,也不是为了域外述奇,而须着眼于寻找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东西,将它们的存在与运作模式记录下来,以便回国后让清朝效仿。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若使人能者而我亦能之,何忧乎不富,何虑乎不强?”——如果人家有的好东西,我们也能够有,何愁国家不富有,何愁国家不强大?
基于这种心态,出洋之前,志刚已阅读过一些西学书籍,对欧美政教与近代科技都有一些浅显的认知。这些认知赢得了恭亲王的好感,评价他是一个“结实可靠、文理优长,并能洞悉大局”之人。也是基于这种心态,志刚的《初使泰西记》里很少记录饮宴游玩,也很少记录奇观异景,他将主要笔力留给了那些他认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物。
这些事物当中,又以近代科技为最多。比如,他记载了美国轮船“China”号的结构与动力系统;详细记载了旧金山的造船厂、铸币厂、炼汞厂如何运作;记载了巴黎的煤气灯、比利时的“藕心”大炮、伦敦的泰晤士河隧道、美国造“司班司尔”步枪、德国的甜菜制糖工艺、俄国的橡胶工厂;还记载了显微镜、印刷机、农业机械、自来水管道、吊车、钢材轧制、织布机、空中索道……这些记载的详细程度,已经到了将整个铸币流程自铁砂入槽到钱币出炉,一步步全写下来的地步。
可以说,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朝内部,志刚是一位难得的有见识、有理想、愿意做事的中级官员。他试图通过自己的日记,将那些他认为好的、对大清有帮助的近代技术文明,统统搬进来。
但也不是没有遗憾。一个人能否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既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获取充分的信息,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初使泰西记》这本日记,让我们见到一个努力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如何孜孜以求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因未能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在面对新事物时的“独立思考”是如何苍白无力。
这种苍白无力见于他在伦敦参观“万兽园”时所发出的感慨。“万兽园”即著名的伦敦动物园,始建于19世纪20年代,1847年之后对公众开放,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的动物园,用志刚的话说,是“珍禽奇兽不可胜计”。他用了好几页纸来记录自己的所见,结论却是:万兽园里的动物种类确实是多,但其中没有“四灵”里的麒麟、凤凰、神龟和真龙。那麒麟与凤凰,得有圣人才会出现。这里没圣人,所以找遍所有鸟兽也不会得到麒麟与凤凰。乌龟倒是或大或小有不少,龙不能豢养,他们肯定也是没有的,总之,这万兽园里养的仍全是些凡物。
志刚承认万兽园的宏大,对里面不可胜数的珍禽异兽也很感兴趣(否则便不至于用好几页日记来记录所见),偏偏又要在日记的末尾发这样一段议论,说什么“伦敦动物园再好,毕竟也没找到中国四灵传说里的麒麟、凤凰和龙”,实在是一种极值得深思的文化心态。当这种文化心态与陈旧的传统思维方式结合到一起,又不免生出一些匪夷所思的“独立思考”。比如他在去美国的轮船上,对蒸汽机作了一番仔细观察,然后利用自己的传统知识结构,就蒸汽机的运作原理写下了这样一段神奇论述:
如人之生也,心火降,肾水升,则水含火性,热则气机动而生气,气生则后升前降,循环任督,以布于四肢百骸,苟有阻滞违逆为病,至于闭塞则死,此天地生人之大机关也。识者体之,其用不穷。此机事之所祖也。
将蒸汽机与中国传统医学里的“心火、肾水、任督二脉”捆绑在一起,然后得出一种共通于天、地、人的原始规律(大机关)。这种思维方式,是后世武侠小说里主角顿悟神功时常用到的桥段,竟也见于务实的洋务官员志刚的日记之中。
在波士顿,志刚参观了一家纺织工厂。该厂有2000多名工人,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印染机器。志刚详细记录了这些机器的具体结构、如何运转、人力多少、产量几何。他完全不排斥将这些机器引入中国,且在日记里说,洋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跑来大清要求通商,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了这些先进的机器,所以货物一天比一天多,必须去寻找销路。“若使西法通行于中国,则西人困矣”——如果我大清也引进这些机器,那这些洋人就没钱可赚了。可是,表达完欣赏之情,志刚那纠结的文化心态又浮了出来:“是由利心而生机心,由机心而作机器,由机器而作奇技淫巧之货,以炫好奇志淫之人。”——这些机器好是好,也应该引进到大清。但终究是出于牟利之心(利心),才会想着要发明这样的机器(机心),再用这些机器来制造出许许多多充满“奇技淫巧”的货物,来引诱那些有“好奇志淫”贪欲的人。
通观整本《初使泰西记》,可以发现志刚的认知始终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出洋给了他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但陈旧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结构,又让他无法处理这些新获取的信息,无法对这些信息做出正确的解读。
如此剖析,并不是要苛责志刚。事实上,这位50岁的洋务官员对待近代文明的心态,已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的同时代人。他不但不排斥近代文明,还努力试图用自己有限的知识结构,对近代文明做祛魅化的处理。“照相机”这个在今天的中文世界被广泛使用的词语,就来自他的发明。在他之前,中国人对照相机的称呼是“神镜”,对其工作原理的描述是“炼药能借日光以照花鸟人物”。志刚摒弃了“神镜”这个玄幻的名称,代之以朴实的“照相机”三字;也摒弃了“炼药能借日光”这种修仙式的解释,代之以一种颇为准确的描述:“照相之法,乃以化学之药为体,光学之法为用。”就“开眼看世界”一事而言,在1868年的欧美之行中,志刚用自己的日记,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全部。
他留下的遗憾,也就是日记中那些纠结的“独立思考”,只是他陈旧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造成的必然结果。爱因斯坦在1953年给友人的书信中,总结过现代科学诞生的两大要件: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这两个要件,志刚不了解也不具备。他被困在了“天人合一”“义利之辩”之类缺乏逻辑的传统知识框架之中。他得到了充分获取信息的机会,却没有掌握处理这些信息的正确思维工具,于是,他的种种独立思考,虽始于赞赏,终不免归于荒诞,蒲安臣努力塑造出来的那个开明中国,当然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摘自《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