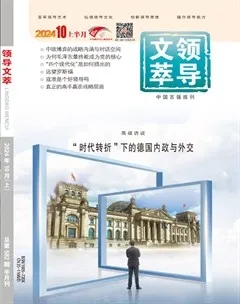司马光:在智者和“迂夫”之间

司马光,一个临危不乱、勇于砸缸的追风少年,这是许多人孩提时代的记忆。在那篇《司马光砸缸》的小学课文里,小小年纪的司马光,给人的印象除了勇毅,还有那个年龄段一般人所不及的智慧。有趣的是,少年时代的司马光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天赋异禀,反倒背记都比别人慢。好在这种慢并没有成为阻碍司马光学习的拦路虎,而是倒逼他倍加勤奋,愈加努力。
写司马光,至少有三件事不可回避。首先当然是前面提到的砸缸传奇。然后是历经十五年沉寂后,捧出的震惊世人的巨著《资治通鉴》。毫无疑问,这套跨越1362年历史、294卷约300万字的编年体通史是司马光人生的高光时刻。再说他的仕途经历,尤其是他和王安石因为改革而互生龃龉。他在生命最后登上相位,其执政举止多为人诟病。
司马光生命中跨越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五个朝代。北宋群星闪耀,在司马光四十八年的仕途生涯中,他与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名人有过交集。从司马光个人仕途纵深看,这也是他深耕基层和边关,饱经官场历练,政治见解逐渐趋向成熟的过程。
在司马光的仕途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分别是他的父亲司马池,以及父亲挚友也是他恩师的庞籍。父亲是他步入仕途的导师,恩师庞籍则会指点迷津,关键时刻还为他挺身而出,将他视如己出。庞籍对司马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盖过了他的父亲司马池。庞籍是一个勇敢正直、坚持原则的人,就连皇太后的懿旨他都敢抗命,司马光的执拗也少不了受他的影响。
司马光的执拗还表现在“谏院五载”。在宋代,能够被皇帝钦点为谏官是一种荣幸。欧阳修说:“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司马光则坚信“致诚则正”“蹈正则勇”。当上谏官后的司马光就像一道光,射向了那个迷茫的变革时代。黑暗因此而照亮,光彩因此更加耀眼。
嘉祐六年(1061)七月二十一日 ,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一口气呈上三篇札子。第一札《陈三德》,被宋仁宗留中;第二札《言御臣》,被宋仁宗转发中书,供宰相们学习;第三札《言拣兵》,宋仁宗转至枢密院,给军政管理者参考。三篇札子言之有物,说明司马光有备而来,并非博取眼球。
谏官五载期间,“司马光一共上了一百七十多道谏书,平均每个月三到四道”。被他批评过的人,上至皇帝宋仁宗,及“各位宰相大臣,韩琦、欧阳修都被司马光批评过”;“往下是皇帝身边的那一群受宠的嫔妃、骄傲的公主、弄权的宦官、膨胀的外戚;再往下才是犯了错误的其他官员”。司马光火力十足,但绝不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尊重原则,持论公允,理性而温和”。
一件小事足证司马光对谏官身份的重视与爱惜。北宋时期的谏官是有严格的职业操守,比如“谒禁”规定。所谓“谒禁”就是不能有私人聚会,这意味着,即便是有如义父的恩师庞籍,他也应有所回避。当恩师庞籍好不容易来到都城开封,“两人近在咫尺,一生情同父子,此刻却不能相见,只得书信频繁。命运如戏,司马光辞去谏官等待新任命书之时,恩师庞籍辞世,十九年师生之情,同城同地,最终未见到最后一面”。
司马光的政见极具远见,他的思考常常独到抢眼。在《贾生论》一文里,他明确直言反对贾谊观点。“文帝的时候,汉朝对匈奴,就像宋朝对契丹一样,是要每年奉上‘金絮采缯’来赎买和平的。这一点让贾谊感到屈辱。司马光却说:‘贾谊念念不忘那一点点的金絮,却忘了如果打仗要花多少钱,贾谊对匈奴与汉之间的礼节感到愤然不平,却忽视了如果打仗会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危害。所以,凭什么说贾谊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呢?’司马光认为,像贾谊这样,抛开国家真正的大政,只关注削藩和匈奴,是本末倒置、缓急失序、不明大体的。”当然,司马光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当王安石力推对有自首情节的杀人凶犯从轻量刑时,司马光却坚持认为“罪不可赦”。
司马光当时之所以会去潜心编纂《资治通鉴》,主因是熙宁三年(1070)反对王安石变法,他坚决辞去枢密副使的任命。在司马光眼里,《资治通鉴》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史书,更像是他呕心沥血搜集史料,精心给宋朝编纂的一本历史发展规律的参考书。
回到变法问题上,司马光认为“本朝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他想要的是,“改变王安石排斥异己的政治作风,取消王安石这些以搜刮老百姓为目的的新政,回到庆历,进行官僚体制的内部改革,节约国家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从这一层面看,司马光对民生的关注甚于王安石对“国库”空虚的焦虑,司马光赞成对社会影响更小的渐进式改革,这样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自然更小。在这方面,司马光不乏知音,比如苏轼。元丰八年(1085),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但生命并没有给他太多机会,当然他的那些举措也没能得到士大夫们的广泛支持。
坐上相位后的司马光,最终还是“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也许是司马光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急于在有限的生命里干出一番“惊天伟业”!然而,他致力推动排除异己的那些方式,恰恰是当年他坚决反对王安石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年多的为相经历,也让他原本光彩照人的仕途生涯,平添了些许灰暗的色调。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