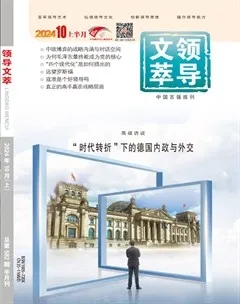史沫特莱眼中的朱德

我最初打算写朱德,是1937年1月刚到中国西北古城延安的时候。那时,百炼成钢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支配这支军队命运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刚刚以延安为根据地。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朱将军,国内和国外的外文报纸也吠影吠声。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打算说明,为什么有几百万、几千万正直而勤劳的农民和工人,以及满怀理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乐于为他所推行的事业而斗争或牺牲。
围绕着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抱着这种好奇心,我和两位朋友在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前往他的司令部,踏进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身穿蓝灰色棉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
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51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了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人们早就对我说过,他是一位单纯、亲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丝毫没有使自己成为个人英雄的兴趣。这些人的介绍都是正确的,不过,“单纯”这字眼需要稍加保留才显得真实。他那双打量我的眸子,注意力非常之深,很富观察力。中国人的眼睛大都是黑色,他的眼睛却很深,而且是淡褐色,大大的一对,闪烁着智慧和判断力。我想,像这样一位有着多年苦痛的经历的革命指导者,既然能够生存下来,就不可能非常单纯。
我在这一瞬间,有了这样一种感觉:不论以他的哪一部分来看——从声音,动作,以至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充满了大丈夫气魄。我对屋里的阴暗光线稍能适应后,发现他的制服因为常年穿着,洗得已经破旧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脸并非没有表情,而是蕴藏在心头的感情强烈地在脸上显现出来。
我在这时候想起了关于他的各种传说,便笑着向他提起关于称他为“土匪”的说法,以为他会像我一样,一笑置之。然而,他不但没有笑,反而突然默默垂下了头,眼睛直视地面。但是,转眼他扬起头来,直视着我说:“土匪问题是个阶级问题。”我立刻把话题转到他的一生,提出了许多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个问题,他作了订正:他的出身并不是富有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户贫农家庭。后来我才知道,很少人或者根本没有人了解他的一生,更没有人有时间坐下来把他或其他人的生平写成书籍。
就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打定了写一本他的传记的主意,因此,当他问我愿意在延安做些什么事时,我回答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为什么呢?”他惊讶地问道。
我回答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我的生平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小部分,”他说,“等一等,你各处走走,和别人见见面,再做决定吧!”
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果然遇到了许多比朱将军还有戏剧性的人物。但是,中国的农民并不是戏剧性的,我还是坚持原方案,1937年3月,我们开始了工作。
我们这份有关他的生平的记录正写到一半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他动身到前线去。我因此将这份材料放到一边,不久也上了前线,这不只是为了另写一本书,也是要尽可能在行动中对他进行观察。因此,我得以在工作中,在球场上,以及在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对他观察了一年之久。
我们且不说他所负担的各种各样军事的、政治的工作,单是像他那样执着于生活,而又有民主作风的人,我过去就从未见到过。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似乎没有哪一方面是他不愿探索和了解的。在延安的时候,他除了在一定的工作时间里同我在一起之外,有时,我和其他的朋友们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他也经常出现,一起吃花生、讲故事、唱歌,以及说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吹一吹。”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虽然很喜欢跳,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像他的下属贺龙将军那样,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跳舞家的才华。
为了不放过从各方面认识朱将军,我有时发现他到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即抗日军政大学)——去讲演,有时在那所大学看到他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后来在前线,我也经常坐在白线外边,好像体育评论员一样,看他和参谋人员组成一队,与司令部的卫兵们赛球。朱将军还时常感叹似地摇摇头,说年轻的士兵们嫌他球技差,不愿他参加他们那一边。
他既喜欢戏剧,又喜欢唱歌,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前线,只有必要的工作才能迫使他放弃欣赏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曾公开放映电影,他几乎每场都到,不时为阿波德和考斯提洛的表演纵声大笑,据说,他们两个的表演很像中国传统的相声和滑稽戏。
第一天他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我们一边等人,一边俯瞰着眼前山谷中的小城延安,延水在古老的城墙那边缓缓流过,对岸,在黄土的断崖上,耸立着一座高塔,再望过去就是一片平川坝子,延水经此东流,注入号称为“中国的忧患”的黄河。
朱将军是个绝对守时的人,到了约定时间,就看到他从下面山谷的小城中走来。在他质朴身影的后面,有卫兵随行,他不时回过头去,大概是在讲话。他的腰板稍稍前倾,脚步像打气筒一样向前移动,他就是用这样的步伐踏破了中国几千几万英里的大道和小路。
(摘自《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