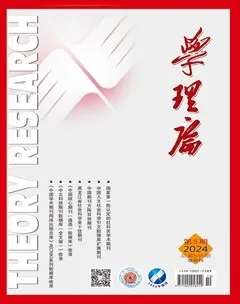大国博弈:二战时期美国调查审判生物战的历史启示
摘 要:二战结束初期,以美苏中为代表的反法西斯力量,与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集团,围绕生物战犯的调查与审判,争夺重建世界秩序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在调查进程中尽展大国之间的博弈,美国政府在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的生物战调查过程中,虽然都发现反人类、非人道的人体实验证据,甚至是战争暴行,然而,两个战败国家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对德日两国的调查与审判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德国纳粹医生,宣传其恶劣行径的调查审判;二是隐瞒有关日本生物战人体实验的信息,让日本战犯免于起诉。二战前后美国参与调查审判德日两国生物战犯,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对战后国家政府间关系产生影响。
关键词:七三一部队;德国;日本;美国;调查审判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4)05-0084-05
收稿日期:2024-05-22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美国调查日本生物战史料整理与研究”(22SSE4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汝佳,副研究员,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平学、战争经济史、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环顾世界历史长河,学界关于美国参与调查德国与日本生物战犯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仍有拓展的空间。其一,从研究内容上讲,既有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对日本生物战调查、美苏交涉等,涉及一些战后生物战调查研究。但是,尚未有对德国和日本调查的对比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结合国内外军事法庭对德日战犯,特别是生物战犯的调查审理经过。其二,从档案文献材料上讲,既往的相关研究较多依靠英文、日文、中文档案,资料基础比较扎实,但是相关文献材料所涉及德文生物战的信息并不是特别丰富,还有进一步拓展材料的空间。其三,从研究方法上讲,既往研究多从冷战对抗的角度解读美国对日本生物战调查问题,本文就战后美国对德日赔偿政策影响进行比较,旨在谴责德国和日本战犯暴行,以及美国掩盖真相的“事后共谋”行径,同时寻求战时医学暴行的本质,深入剖析重要事件的历史原因和伦理原因[1]。以期对未来世界和平发展探索历史借鉴。
一、二战前后美国对德日人体实验及生物战调查
据德文资料记载,二战期间德国反人类、非人道、违反医学伦理的人体实验值得深入挖掘与思考。“在德国,只有斯塔拉格·卢肯瓦尔德战俘营有500个黑人可供热带医学实验研究。在元首的命令下,大部分非洲囚犯(8万人)都被驱逐到法国南部(波尔多),黑人不允许生活在德国的领土上,只有少数黑人留在德国被用于某些特殊肤色人种实验,并且这部分实验用的黑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与平民共同生活,无论是吃住还是在研究所参与实验。总指挥部表示,只要研究人员提交用于实验的战俘人数申请,并确定实验是在卢肯瓦尔德或波尔多进行,非洲战俘就会被顺利提供给他们”[2]257。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教授、医学史学家保罗·朱利安·温德林在本校创建的数据库已经确定了大约2.5万名二战期间德国人体实验受试者,确认约一万份文件。面对德国人体实验,德国纳粹以种族主义信仰、优生学以及战时国家利益等三个理由为其人体实验辩护。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战败。至此,日本法西斯已濒临灭亡,但仍妄图谋划一场最大规模的生物战,来挽回其败局。据现有史料不完全统计,日军生物战部队为研究和生产大量生物武器,在多地开展生物实验。1936年天皇敕令建立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位于伪满洲哈尔滨平房地区,首任部队长是石井四郎。川岛清在苏联伯力法庭上供述梗概内容是,1940年至1945年间,七三一部队每年消耗受试者至少600人,总计五年消耗受试者至少3 000人。美国著名研究日本生物战史的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1994年出版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一书中,认为1932年至1945年期间至少有受试者4 000—5 000人在七三一部队及其各支队中遇害[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分别成立了两个审判法西斯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追究侵略战争罪犯的战争责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开庭,第二年10月1日,对德意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审判,判决甲级战犯12人绞刑。在战后美国调查德国过程中,军医约翰·韦斯特·汤普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945年5月,军医汤普森抵达德国后,初次经历照顾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很快发现,这项研究的很多实验都是以非人道的方式进行的,并通过对德国科学家和幸存受试者的访谈证实了这一点。汤普森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个人接触和外交手段这两种方式。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医学史研究教授、医学史学家保罗·朱利安·温德林表示,加拿大军医约翰·韦斯特·汤普森幕后角色的重要程度,足以获得“纽伦堡法典和知情同意的教父”的称号[4]。
二战结束初期,在美国的庇护下,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及其上级、下级等生化战罪犯3 000余人,始终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其战争罪责的追究,而且此后长久以来这种反人类的战争罪责一直被深深地隐瞒起来。究其原因是相较于德国,日本“科学家”们更精于预先谋划,并联手应对美国的调查,在意识到美国对其医学资料感兴趣后,将此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美国共分四批派出调查官,第一位前往日本的美国调查官——微生物学家莫瑞·桑德斯中校服役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战部队。第二位美国调查官是阿尔沃·T.汤普森中校[5]。第三位美国调查官诺伯特·H.费尔博士是德特里克堡的文职雇员,于1947年抵达日本[6]。第四批美国调查人员是来自基础科学部的技术主任埃德温·希尔博士和工作人员病理学家约瑟夫·维克多博士,并于1947年12月,提交了最终报告,即希尔报告[7]。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人这个群体,只要进行强制教育,施加威胁,无论斯大林教也好,天皇教也好,或者其他一切宗教也好,任何思想他们都会相信——而且已经相信了。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民族。德国兵即便当了俘虏也是很有骨气的,对此美军感到十分棘手。可许多日本兵一旦被俘,就变得很顺从,积极地迎合、协助美军。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8]。
二、二战后对德日生物战犯的审判
(一)德国生物战犯与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后续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对战犯最著名的军事审判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9]。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要针对日本主要战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德国战犯,对战后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1943年以来,一个代号为“避雷针”的生物战工作组一直在活动,该工作组将病原体和植物害虫用作战争武器。工作人员主要是陆军卫生检查组、陆军兽医检查组、国防军高级司令部军事科学部门以及陆军兵器部门的成员。据有关德文资料记载,希特勒反对生物战。然而,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科特·布洛姆(Kurt Blome)教授却在资助德国生物战研究基金会。为了掩盖生物研究的真相,他让这个秘密项目以“癌症研究”的名义进行[2]87。
1945年8月8日,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4个国家牵头,在伦敦直接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这两份文件,签订文件之后,并依据于此迅速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苏联希望在世界焦点的审判会上证明纳粹的邪恶与苏军胜利的不易,而美国不想向世界展示德国(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在不通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剥夺别人的生命。
纽伦堡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审判之一是医生审判,该审判于1946年12月9日开始。由美国领导的军事法庭审判了23名被指控犯有各种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德国医生。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医生在未经“不值得拥有生命”的人(包括残疾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人体实验。纽伦堡的主要战犯审判结束后,被称为纽伦堡的后续审判开始了。这些审判是在美国军事法庭进行的,因为紧张局势加剧、与苏联关系越来越差,这使得在其余的审判中合作变得不可能。
1947年1月15日上午9时,在东京的原陆军省大楼里盟总召集的会议上,苏联上校斯米尔诺夫(Leon N. Smirnov)表示:“在纽伦堡审判中,一名德国专家证人称,以跳蚤传播斑疹伤寒是公认的生物战最佳战法。日本人似乎也掌握了这种技术,而得到这个情报对美国和苏联来说都是有价值的。”[10]二战德国战败之后,大量科学技术流入美国,大量的装备和设备流入苏联,大量的科学家、科技图纸以及大量可观的发明和一些武器装备重工厂等,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和苏联,对美苏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助力作用,为之后美苏两极争霸埋下了伏笔。
(二)日本生物战犯与东京审判
1945年8月14日晚,杜鲁门总统在国家电台广播中宣布日本天皇已经接受《波茨坦公告》中要求的“无条件投降”。8月6日广岛和8月9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使杜鲁门有底气作为世界仅有的核大国发声。杜鲁门提醒道,正式的抗日战争胜利日不得不等到投降文件正式签署后才能确定。杜鲁门指定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负责这一事件,并任命他为盟军最高司令。这一决定是事先与英国、中国和苏联共同商议后决定的。9月12日,麦克阿瑟再次向陆军和海军军官以及来自华盛顿战争罪行办公室的一个小组阐述他设想在大型法庭和小型审判中都起诉日本战犯:“审判必须是公开透明的;必须是公正的,不夹杂报复或政治色彩;必须成为法律和正义世界的典范。我们可以被批评,但我们将争取做到历史性的裁决。”[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京审判(即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依据是一系列与现代战争和暴行有关的国际法、条约、协议和保障,如《波茨坦公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审判语言为英语,被告语言为日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包括英文和日文两种文字的记录,即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审判记录。在东京审判期间,中国代表履行了他们的使命,在法庭记录中留下了他们的正义话语。庭审结束后,中国代表带回了两箱文件,包括48 000多页的庭审记录和20 000多页的证据。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这些档案已经流失,给研究东京审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12]。
二战后,与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相比,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惩罚过于有限。苏联甚至将两名曾参与生物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押送至东京作证,并以生物战罪对日本提起诉讼。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前生物战元凶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笠原辛雄和裕仁天皇均免予起诉,逃脱了司法制裁。尽管昭和天皇的确负有战争责任,国际社会要求审判天皇的呼声也很强烈,但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为了利用天皇完成对日占领,以及将获取宝贵生物战和人体实验资料作为交换筹码,东京审判的最高机构远东委员会在东京审判开庭前夕的1946年4月3日决定不起诉审判天皇,这个最大的战争罪犯逃过一劫[13]。这一结果对各国生物战(包括相关实验)的受害者,尤其是对绝大多数伤亡的中国同胞来说,显然既不公平也非正义。最终,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历时两年有余,竟未能将日本生物战犯送上国际法庭,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14]。
(三)日本生物战犯与伯力审判
基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抗,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日本侵华时期研制、使用生物武器的12名日本生物战战犯,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接受伯力审判,其中包括山田乙三(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隆二(原日本关东军医务部部长、军医中将)、高桥隆笃(原关东军兽医部部长、兽医中将)、川岛清(原七三一部队总务部部长、军医少将)、柄泽十三夫(原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等,他们犯下了“准备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战争罪。在日本侵华期间,它开发和使用生物武器对包括一些苏联、蒙古和朝鲜人在内的大量中国士兵和平民进行不人道的人体实验和屠杀,违反了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
自1931年至1945年,日军对中国20个省区发动了多达36场大规模生物战。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六四三支队(又称海林支队)队长尾上正男供认,其在任职期间,仅在第六四三支队内就训练培养了生物实验工作人员共计160人。尾上正男供述,该支队供给部部长神尾少尉兼任过老鼠捕获队队长职务,同时进行过繁殖老鼠的工作。该支队起初是由10人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到各个部队及居民区捕获老鼠,将其送到支队来,然后再由支队送至七三一部队的库房去。此外,由神尾少尉带领的支队还在牡丹江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捕捉老鼠行动。侵华日军第六四三支队最初有10至15人,但到1945年已增至30人。当时,大规模捕捉老鼠的行动已经列入日程[15]。1939年至1944年在七三一部队任职细菌生产班班长期间,柄泽十三夫“积极研究生产大量细菌生物,并将其用作生物战剂的最可行方法。”[15]他承认,“我是一名生物外科医生,所以我知道大量生产这些细菌生物是用来消灭人类生命的。”柄泽十三夫也对石井四郎所在的部队使用细菌的行径供认不讳,据柄泽十三夫供述:1940年下半年,其带领支队成员培养了70公斤伤寒细菌和50公斤霍乱细菌。这些细菌被供应给一支前往中国中部地区的特别细菌远征队,该远征队由七三一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亲率。
经过这次审判,苏联向世界宣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准备并使用生物武器”的犯罪事实,成为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的强大“外交武器”。尽管如此,由于伯力审判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为的曲解和隐瞒,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日本生物战争罪行的披露和取证,以及对生物战争罪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均未完待续。
(四)日本生物战犯与民国政府审判、新中国特别军事审判
民国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十个军事法庭,分别指南京审判、北平审判、济南审判、武汉审判、广州审判、徐州审判、沈阳审判、太原审判、台北审判、上海审判。受东北政治局势的影响,沈阳军事法庭是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十个军事法庭中最后一个开始工作的。
根据1947年南京国防部统计的《日本战犯名册》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保存的《中国战犯裁判结果表》,可以看到逮捕拘留的人数和审判人数的对比,从审判人数中又可以看到实际判刑人数和无罪不起诉人数的对比。其中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受审判人数只占被拘留逮捕人数的38%。三分之二的被拘留者没有受到审判。审判中无罪和不起诉的人数又占到受审人数的41%,可见,大多数战犯嫌疑人都逃过了审判。这种局面究其原因,最主要是证据不足,或者无法取得符合审判要求的证据。由于证据不足,无法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深入审判,这贯穿了国民政府的整个审判过程。由于主要依靠公众举报和收集证据,证据大多集中在指控日本宪兵和驻扎在城市的间谍等低级战犯上。然而,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起诉大量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日本高级指挥官。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在国军受降和接管之前,日军各级军政机关都将战争档案予以销毁,这就毁灭了日军最大数量的罪证[16]。
1942年,联合国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于同年1月伦敦九国会议决定开始调查德日法西斯战争罪行后,中国国民政府也开始了对日军侵华罪行的调查工作。经历东京审判和国民政府审判后,1956年6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即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生物战战犯■原秀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57年得到中国政府特赦[17]。
■原秀夫出生于1908年1月9日,籍贯是冈山县冈山市山崎町五十号,别名是■原英男,家庭成员有妻子■原房子,长子■原宽树,长女■原松子,次女■原贵子。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原秀夫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林口支部长,在第七三一部队长指挥之下,除承担细菌战的实施及准备任务之外,还承担第五军管区内一般部队的防疫及给水任务[18]。其供述内容如下。
一九四三年七月,根据关东军的命令,我去第七三一部队参加对师团防疫给水部长进行的“特殊防疫教育”三天。
这个特殊防疫教育是关于为细菌战的教育。其内容是:第一天上午由第七三一部队长北野军医少将报告有关教育的指示:下午由总务部长太田大佐以“细菌战的概念”为题,报告有关能使用于细菌战的病菌,即解释鼠疫菌、炭疽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破伤风、狂犬病、霍乱菌、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斑疹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疟疾等病菌,还报告了攻击方法是用炮弹、飞机等撒布,攻击目标为敌人的重工业地带、兵站基地、飞机场、敌军高级司令部所在地、交通要塞、粮库、军港、水源、部队密集地方等。
第二天上午,由教育部AyEkBxyHeDtVVd9eihh0JA==长圆田中佐以“中日战争中阴谋破坏的事例以及其教训”为题进行了造谣欺骗的报告,下午,由第四部草味药剂少佐以“毒物中毒”为题报告了关于青酸、砒霜、磷、硝酸奎宁(毒药:Strychnine)、升汞等中毒问题。第三天上午,由第四部河岛药剂中佐来关于对“简易毒物检测知法”做了报告,并参观了消毒车的实际演习操作后训练结束。当这个训练结束后,我不顾人道上、国际公法上禁止的关于细菌战问题,向部下军官进行了上述内容的宣传教育。……
同时,石井指出当捕鼠时特别要注意防谍并指示了要欺骗群众说捕鼠的目的是除掉“鼠害”和解释了由第七三一部队编印之关于“鼠害”的小册子[18]。
三、二战后美国对德日赔偿政策的影响
从国际宏观战略考虑,由于美国在二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至于美国以支配者的身份参与战后欧洲政局,并对德国的未来命运掌握着决定性话语权。战争赔偿是战后德国诸多问题中的关键,不仅关系到重建战后国际格局的稳定、恢复战后经济秩序、引导德国重新融入战后国际体系,还关系到美国战后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证等一系列问题。美国吸取一战后对德国赔偿政策失误的惨痛教训,对二战后德国赔偿政策遵循服从于全球冷战战略原则。二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亦经历两个不同阶段,随着远东政策战略目标的转变、中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从打压日本政策到利用日本政策,致使赔偿性质和赔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变,严重损害了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利益。
二战后德国和日本政府对受害国的赔偿政策,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德日两国战后的不同态度。中日双方就战争经济赔偿问题经历了从放弃战争赔偿到获得日本经济援助的发展过程。中国放弃对日本索要战争赔偿的缘由有数个,其中很重要的是道义论。二战后,日本对中国战争赔偿问题是较为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对中日、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四、余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结成了军事联盟,在战争期间犯下了无数罪行。美国在整个美苏冷战时代,始终以遏制观念为主要国家大战略基础,以包含种种具体历史形态的遏制战略为其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内涵。这种对历史的真诚反思和面向未来的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推动了民族和解进程,使德国成为国际社会的早期成员。然而,在东京审判中受审的日本情况却大不相同。日本政府在人类实验性生物战中犯下的医疗暴行令人发指,不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还要对国际社会履行义务。
美国以国家安全等理由不仅粉饰更掩盖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所犯的战争暴行,充分体现了美国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的实用主义国际关系理念。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体现出的重要军事价值,促成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和提高。中国参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四强”之说随之出现。签署《莫斯科宣言》,则标志着四强地位得以确认。开罗会议上,中国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就。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政府形象,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终确立了政治大国的地位[19]。建立共同历史认知,致力未来世界和平发展,仍需坚持不懈地努力。
参考文献:
[1]周丽艳.“Q”报告与侵华日军细菌战[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9(4):69-79.
[2]Ernst Klee. Auschwitz,die NS-Medizin und ihre Opfer [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2001.
[3]Sheldon H. Harris.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79.
[4]Weindling PJ. John W. Thompson: Psychiatrist in the Shadow of the Holocaust [M].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0: 148.
[5]刘汝佳.关于《汤普森报告书》的初步解读——基于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的调查[J].北方文物,2012(4):98-105.
[6]杨彦君.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报告再解析——以美国馆藏史料为中心[J].抗日战争研究,2022(3):81-90.
[7]鲁丹,赵倩.从《希尔报告》看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基于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的调查[J].黑龙江档案,2021(2):213-217.
[8][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4-85.
[9]王孝华.七三一部队溃逃之际屠杀活体实验者问题再探究——以中日两国见证人的口述史料为中心[J].北方文物,2022(5):111.
[10]Doc Title: Bacteriological Warfare Experiments by Japanese,summarizes meeting with Russians over their requests to interrogate ISHII &OTA; Location: 290 /24 /02 /03,RG#331,Entry#1901,Box1,National ArchivesⅡ of USA,Maryland.
[11]Jeanne Guillemin. Hidden Atrocities: Japanese Germ Warfare and America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t the Tokyo Trial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27-32.
[12]东京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5-7.
[13]宋志勇,周志国.战后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
[14]人类首次对细菌战罪行的审判[EB/OL].(2016-05-02)[2022-07-23].抗日战争纪念网,https://www.krzzjn.com/show-548-29955.html.
[15]伯力审判中的十二名日本细菌战犯[EB/OL].[2022-07-23].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官网,http://www.731mu-seum.org.cn/system/201507/117458.html.
[16]刘统.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875-876.
[17]杨彦君.《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复七名簿》释读[J].武陵学刊,2021(6):127-132.
[18]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贰)[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309.
[19]王建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五卷:战时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13.
(责任编辑:田 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