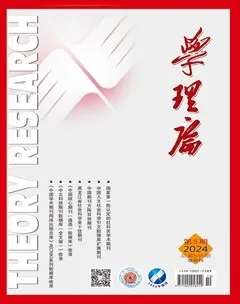中期维特根斯坦论“Satz”
摘 要:“Satz”一直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中心概念。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命题”(Satz)的基本功能就是对世界中的事态做出可真可假的论断。中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命题一般形式”,“可真可假”的命题不过是“Satz”的一个部分,他还质疑了前期所说的那种“图像与命题的对应”,初步提出了“意义即使用”理论。本文将基于《大打字稿:TS213》文本,阐述中期维特根斯坦关于“Satz”的观点,分析其中对前期理论的批判,并说明后期观点在中期文本中的奠基。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Satz;命题;《大打字稿》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4)05-0041-04
①在涉及“Satz”及其翻译时,本文采取以下策略:如果只是一般意义上谈对“Satz”的理解,那么本文保留这个德文词不翻译;如果涉及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哲学时,本文将“Satz”翻译为“命题”;如果涉及中期维特根斯坦或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这个词的使用时,本文将“Satz”翻译为“句子”。
收稿日期:2023-12-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现象学语言’到日常语言:维特根斯坦《大打字稿》研究”(23FZXB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家荣,讲师,博士,从事维特根斯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自1929年返回剑桥之后,维特根斯坦开始对以《逻辑哲学论》(以下简称TLP)为代表的前期哲学展开全面反思,这种从“逻辑语言”向“日常语言”的转变在1929—1935年的中期文献中就已出现,从维特根斯坦这个时期关于“Satz”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这一点。
德语的“Satz”可以翻译为“命题”,也可以翻译成“句子”。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有意义表达式称为“句子”,但并非所有句子都可以称作“命题”,“命题”是以主谓形式对世界进行陈述或描述的句子。对于以TLP为代表的前期维特根斯坦来说,把“Satz”理解成“命题”较为合适,根据TLP中的哲学,“Satz”的根本特性是对事实的刻画,因而基于与事实的一致或不一致而有真有假。自从维特根斯坦于1929年开始关注日常语言后,他对“Satz”的界定和使用就越发宽泛,可真可假的“命题”不过是“Satz”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比重较小的一部分,“Satz”包括了日常语言中的所有句子。①
对于任何研究中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学者来说,《大打字稿:TS213》(The Big Typescript:TS213)都是一份无法绕开的文本,从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维特根斯坦对前期哲学关键议题和概念的批判以及向后期哲学问题和观点过渡的征兆。按照相关主题,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Satz”的驱魅和语言整体;2)句子没有“本质”;3)句子和图像的“一致”;4)句子的意义。
一、“Satz”的驱魅和语言整体
在TLP中,“命题”(Satz)与所描绘的事态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对应,这种对应“不可言说”因而是神秘的,“命题”这个概念似乎超然于所有概念之上,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征。在转向日常语言之后,维特根斯坦对“Satz”的看法开始改变。维特根斯坦认为,“Satz”这个概念“只有在一个有限制的范围内被允许使用,在这个范围内,它们的使用是自然的。如果这个领域被扩大了,这个概念就成了哲学概念,那么这些语词的意义就蒸发了(verflüchtigt),它们成了空洞的影子。我们必须放弃它们并且将它们拉回到界限之内使用”[1]50。这里的“有限制的范围”是指日常语言,换句话说,维特根斯坦认为只有在日常语言之中谈论“句子”及其使用才有意义,而前期那种将“Satz”概念理想化进而等同于“命题”的观点就超出了“Satz”的合理使用范围,进而将其弄成了“哲学概念”。
在中期维特根斯坦看来,“Satz”概念并不比语言中的其他概念更为重要和神秘。句子某种意义上就是使用符号,维特根斯坦说,“人们将使用符号(Zeichengeben)与其他行为活动区别开来。一个人睡觉、吃饭、喝东西、使用符号(使用一种语言)”[1]51,人是符号的动物,使用、说出、理解符号并根据符号而行动,这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征。虽然使用符号与其他行为有别,但从后半句话来看,维特根斯坦仍然将使用符号与人类的其他自然活动并列而言,“说出一个句子”与“吃下一顿饭”“睡一个好觉”等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行动,在概念层面上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造成这种区分的原因是,人们以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使用符号这种活动,并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解释。由此,维特根斯坦某种意义上去除了围绕着“Satz”的神秘光环,将“句子”以及与之有关的活动拉回到了日常层面。
中期维特根斯坦更强调“句子”(Satz)所构成的整体,“一个东西只有在语言之中才算作一个句子”[1]52,换句话说,只有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经由逻辑关系相互勾连而形成的语言整体之中,我们才能说句子是句子,句子的意义位于语言整体之中,理解一个句子就是理解一种语言。既然是从语法和整体的角度才能规定何为句子,那“感觉”或“经验”就不能界定“句子”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在文本中反对了这种“经验主义”视角。他认为,如果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我们可能会认为句子有一种听起来像是句子的感觉,我们读句子的时候似乎是有独特节奏的,维特根斯坦用了两个词来表达,其一是“Satzklang”,勉强可译为“句子声响”;其二是“Satzrhythmus”,勉强可译为“句子节奏”。但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声响或节奏并不是句子的本质成分,他在文本里没有具体说明他所谓的这种节奏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是一个句子的感觉”,例如一个大略知道汉语声调但对汉语似懂非懂的外国人听到一句汉语时候的感觉。“抹香鲸的尸体落在海床上”是一个汉语句子,但类似构造或具有相似节奏的另一个句子“红色的素数落在海床上”就不是一个句子,一个不懂汉语的人可能会误认为后者也是一个“句子”,仅仅是因为听上去像一个句子。所以,维特根斯坦说这种节奏对于理解句子来说并不是本质性的东西。
与“Satzrhythmus”(句子节奏)相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以节奏而论,那么单个的语词不会是一个句子,因其毫无节奏。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直接喊出一个词“糖”来替代“把糖拿给我”这个句子。为了说明“句子”不一定需要所谓的节奏或构造,维特根斯坦设想了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在一个房间里,我打开控制灯光的开关,这时灯亮了,我对小孩子说“光”(Licht);我关掉开关,灯灭了,房间也随之暗了下来,我对小孩子说“暗”(Finster),如此反复几次后,我到隔壁房间去控制先前房间的开关,让小孩子根据情况告诉我“光”还是“暗”,维特根斯坦问道,“我应该把‘光’‘暗’称为‘句子’吗?可以,只要我喜欢”[1]156。
因此,“一个表达式是不是句子”这一点,不是基于表达式的外形去界定,而是根据表达式在具体情境或具体语言游戏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说“光”“暗”不是在单词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作用和句子相似,在这里的使用方式不同于它们出现在“那里有一束光”“现在天暗了下来”等句子之中时。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说出一个词“光”或“暗”,别人可以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一个句子!”在这种情况下,说出“光”或“暗”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游戏。换言之,我们唯有通过情境或者语境去判断一个表达式到底是算作语词还是句子。
二、句子没有“本质”
无论是中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似乎没有对什么是句子做出过清晰界定,当然,下定义并非他的风格。维特根斯坦说句子就是所有那种我用来有所意谓的东西,或者说句子就是那些我们通过其而有所意谓的符号。我们可以问:我们意谓什么?我们何时在意谓?如上所述,句子之所以有意义、能意谓,根本原因是其从属于语言整体之中。我们意谓什么?这是由句子所在的语言整体规定的。我们何时在意谓?当我们使用语言整体之中的句子时。
在TLP中谈到命题本质的时候,“真值函项”(Wahrheitsfunktionen)是一个重要概念。在TLP之中,维特根斯坦曾给“命题”(Satz)下过一个定义,“一般的命题形式就是命题的本质”[2]5.471,而命题的一般形式是“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换言之,命题的根本功能就是对世界中的事态做出可真可假的论断,命题表现基本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如果一个基本命题是真的,则(它所描述的)基本事态存在;如果一个基本命题是假的,则(它所描述的)基本事态不存在”[2]4.25。即是说,对于TLP来说,命题是那种可真可假的东西,“真假”属于命题本质性的构成部分。
从中期维特根斯坦文本中看,他认为“真假”没那么重要,甚至认为“真的”(wahr)这个词可以直接从语言中取消,当我们说“他说的是真的”时,这句话说的其实就是“他说p,并且p是事实”。维特根斯坦进而认为,“真的”“假的”不过是适用于真值函项的特殊概念系统中的两个词,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适用于语言中的所有句子,毕竟语言中的很多句子难以用“真假”来描述,“‘事情是如此这般的’仅仅是一种真值函项符号系统中的一个表达式”[1]92。这句话表明,语言中的“句子”是多样的。
既然“句子”是多样的,那么先前那种完全从“命题”出发去理解语言功能的观念就错得离谱,维特根斯坦列举了当时剑桥哲学家布罗德(Charlie Dunbar Broad)的观点,后者说“某事会发生”(etwas werde eintreffen)不是一个“命题”(Satz)。维特根斯坦没有解释布罗德的意思,布罗德这个断言可能意思是:因为所描述的事态还没有发生,所以具有将来时态的命题不能为真也不能为假,而既然可真可假是命题的本质特征,因此它们就不是命题。如果要这么推论,那么语言中的大部分“Satz”都被剥夺了功能。维特根斯坦认为,布罗德的想法就像是用语词实施的魔法(Die Magie mit W■rtern),“试图用魔法去影响一种化学变化,通过让诸实体领会它们应该做的是什么”[1]62,物质实体的化学反应自有其自身规律,不会跟随着人们对它们的“指示”而反应,维特根斯坦这个比喻意在说明:布罗德企图用自己构建的关于命题的观念去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表面上看,维特根斯坦是在批驳布罗德,但在布罗德的背后,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幽灵在闪烁。
哲学家试图追问本质,TLP中的维特根斯坦也曾如此。在中期,维特根斯坦以反问“搪塞”了对命题本质或“命题的一般形式”的追问,“当我问:‘命题的一般形式(allgemeine Form des Satzes)是什么’,那么与之相反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拥有我们想要准确地把握的关于命题的一般概念吗?’——就像:我们拥有关于现实的一般概念吗?”[1]50。概念总是与概念相对,我们如若“拥有关于现实的一般概念”,那它是与什么相对待?你可以说是“非现实”,但既然是“非现实”,我们又如何拥有关于它的一般概念?
三、句子和图像的“一致”
中期维特根斯坦对TLP中语言图像论的反思与对句子多样性的强调有关。在TLP中,“命题”的概念与“图像”关联紧密,“命题是实际的图像。命题是我们所思维的实际的模型”[2]4.01,要言之,“Satz”(命题)就是描摹现实的一幅图像。
在中期,维特根斯坦开始反思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自问: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命题是一幅图像?每幅图像都是一个命题吗?把“写实画”看作一个命题,这也许不成问题,但是“抽象画”或者“风俗画”(Genrebild)呢?每个命题都是一幅图像吗?物理学命题“F=ma”所对应的是何种图像?关于万有引力公式的图像与描摹苹果砸在牛顿头上的图像之间的关系为何?维特根斯坦说,“认为一个命题是一幅图像,这不过是强调了‘命题’这个词语法上的某些特征(gewisse Züge)”[1]67。“某些特征”指的是“Satz”中的某一类具有描述现实的特征,但这只是“Satz”中的一个类别而已,根本不能概括所有的“Satz”,“命题”不能代表所有“句子”。在TLP中,维特根斯坦说“它(一幅图像)像一把尺子一样被置于实际之上”[2]2.1512,换句话说,他把命题比作一把尺子。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中期维特根斯坦所写的下面这段话,“测量尺——正如所有关于句子的比喻一样——只是句子的一个特殊案例(besonderer Fall)”[1]70,在这里,维特根斯坦说把“Satz”比作图像,这“只是句子的一个特殊案例”,如果以特殊案例来理解所有的句子,那是以偏概全。讨论句子与图像的关系时,维特根斯坦还讨论了“与现实一致”这个概念,“与现实一致”意味着作为图像的命题描摹的是现实,但是句子的功用是多样的,当一个人掉到水里,他大喊“救命”,这时他是陈述他需要帮助这个事实吗?显然不是:落水者的呼救不是在描摹事实,而是引发关注并获得救援。
如果像TLP那样把“Satz”根本地看作是描摹现实的图像,那么“Satz”都是可以证实或证伪,“Satz”的意义与可证实性紧密关联。而维特根斯坦现在问道,“Satz”都是能证实的吗?文学作品里的句子能被证实吗?“它们与能够证实的句子之间的关系就像风俗画(Genrebild)与肖像画之间的关系”[1]69,肖像画某种意义上是描摹实际的人,因而可以证实,但是风俗画则很难说“证实”,然而我们不会因此就说风俗画不算画,因为风俗画的意图并非严格地描摹现实。同理,不能因为某个“Satz”不能证实或证伪就认为它不是“Satz”,换言之,“句子”的范围远大于“命题”。
如果把命题看作是关于现实的图像,就意味着“命题P断言这个特定事实发生了”。但是,这个“特定事实”如何寻找?换言之,如何寻找那个对应于某个命题的具体图像?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是通过其他命题,那么我们什么也没解决;如果是通过其他现实(Realit■t),那么后者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掌握。这意味着:你不可能指着一个命题和一个现实并说:‘这个对应着那个’。相反,只有已经被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才能与一个命题相一致。也就是说,不存在关于命题的实指解释”[1]142。维特根斯坦的意思很明白:你不可能一边单独拎出一个命题,另一边指出一幅现实的图像,然后说两者相互对应。无言的图像,只有被转化为另一个命题才能与命题相互对应,但转化为命题的图像与图像本身的关系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似乎只能不断地通过其他命题来嫁接,而不断地嫁接意味着永远无法嫁接。
说“命题与图像对应”,这意味着它们两者某种意义上“一致”。命题是思想的表达,维特根斯坦问道,“什么促使我们认为在思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一致性?——我们这里可以放心地用‘描绘性’(Bildhaftigkeit)代替一致性。但是描绘性是一种一致性吗?在TLP中,我说过类似的话:描绘性是一种形式上的一致性(eine ■bereinstimmung der Form)。但这是一种误导(Irreführung)。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任何其他东西的一幅图画:只要我们把图画概念延伸得够广”[1]141,“相似性”或“一致性”不足以构成命题与图像之间的“一致”,只要不断地转换观看方式,或者不断地创造“误解”,任何图像都可以是任何其他东西的图像,真正的“一致”是在语法中获得规定的。
IMMtJCnH7saXlPranZPrEA==“相一致”这个词本身就是多义的。“两个钟表相一致”,这是两个表都指向同样的时间;“两个标尺相一致”,那是它们的刻度长短是一样的,“相一致”也不必须就是数量长短的相同,也可以是比例的一致,每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在“相一致”这个词名下我们所理解的是什么。换言之,没有什么本质意义上的普遍的“相一致”,“相一致”在不同语境之中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具体的语境,而非抓破脑袋地去思考“相一致”的本质。
四、句子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总是从一种语言整体或语法的角度谈论意义,句子的意义也不外乎此,“我们可以说:只有在解释一个语法系统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谈论句子”[1]50。维特根斯坦说,“‘句子’一词以及‘经验’一词已经具备了一种特殊语法。它们的语法必须事先就已经确立。它并不取决于未来的事件。这也表明了‘意义的实验理论’(experimentellen Theorie der Bedeutung)的无意义。因为意义是在语法中被确定的”[1]51。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的实验理论”是不成立的,但他没有具体界定这种理论的内涵,“意义的实验理论”的基本主张可以大致理解为“句子的意义是通过实验操作或经验行动而被确定的”,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反对这种理论,是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意义就是通过经验被确定的,这种将意义与经验相勾连的观念与维特根斯坦这个时期从语法角度规定意义的基本思路大相径庭,如果语法不首先确定一个句子的意义,我们就无法在经验中展开这个句子,如果关于测量的程序或方法不首先被确定下来,我们就无法在实际中进行测量。
按照一般的理解,句子的表达式是有形的,但句子的意义是无形的,意义不同于意义的表达,意义存在于人的心灵对它的把握之中。既然关涉心灵,那就很容易设想意义如无形的气体一般,维特根斯坦说,“句子或者其意义(Sinn)不是像某种具有生气的本质(pneumatische Wesen),仿佛它具有自己的生命”[1]210,关于意义的解释经由语言之中其他表达式而来,那么句子的意义是在语言整体中确定的。而用来解释意义的其他表达式是可见的,因而句子的意义并不是无形的。
句子和句子经由各种逻辑关系而组成整体,句子的意义不是通过心理之物而规定的,它是在“作为算式的语言”之整体中获得规定。顺便一提,能否根据句子去进行有意义的想象,这往往被当作判定句子有没有意义的一个标准,我们能想象“抹香鲸的尸体落在海床上”的场景,但是想象不出“红色的素数落在海床上”的情形。维特根斯坦曾经谈论过这个标准,他大部分时候认为这个标准没问题,但我们可以问:如果以这种“想象”而论,那么句子的意义不就是可以通过“画面”等经验性内容来规定了吗?这不是和维特根斯坦的整体思路相背离了吗?维特根斯坦在提出这个标准之后,旋即话锋一转,说“如果我能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些词,那么它们就具有意义。或者实际上:如果我用它们去计算(Kalkulieren),那么它们就有意义”[1]65,即使想象能成为一个标准,但维特根斯坦要强调的重心还是“使用句子”“用它们去计算”等从整体角度出发的标准。在后面,维特根斯坦甚至说了一句位于后期哲学之中心的话,“句子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1]80,这里的“使用”勾连着由语言游戏构成的语言整体,也提示后期哲学中的核心论点,即“意义即使用”。
根据上面基于《大打字稿:TS213》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语义之基本单位的“Satz”的思考,中期维特根斯坦不同于前期那种从逻辑视角出发的观点,而是在日常语言实际使用之中去审视其意义和使用,对前期哲学中被冠以特殊性的“命题”(Satz)进行驱魅。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Satz”,某种意义上是想暗示前期哲学对“Satz”的偏见,即:如果只从描摹事实的角度去理解“Satz”之功能的话,那就是对语言之多样性全貌的闭目塞听,以致出现以偏概全的错误,或用后期的比喻说即是“吃偏食”。中期维特根斯坦认为,“Satz”的意义并非来自与所描绘事实的相对应,而是由“语言整体”所决定的。顺便一提,这个“语言整体”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超越于经验层面的“语法整体”;其二是根植于人类实践的“社会实践整体”。从上所引“句子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中期维特根斯坦开始明显地倾向于后一种解释。由此,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种子,在中期就已撒下。
参考文献:
[1]Ludwig Wittgenstein.The Big Typescript:TS213[M].ed.&trans.C.Grant Luckhardt and Maximilian A.E.Aue,Blackwell Publishing,2013.
[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