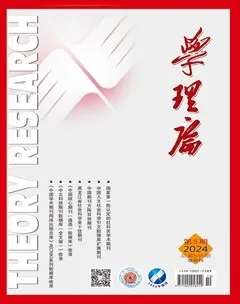可能世界、现实世界与元宇宙
摘 要:在逻辑学上,可能世界一般有两种界定:其一,认为逻辑上一致或无矛盾的世界;其二,认为我们能想象的任何一个世界都是可能世界。解决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在于我们给予可能世界何种本体论的认定或承诺。元宇宙是人类基于一定科学技术的聚合,采用数字化呈现的方式,从而构建出的现实世界的可能状况或状态。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可能世界的构想和创造,最多是现实世界的“副本”。根据元宇宙的设计原理,它在未来有可能“侵犯”现实世界,这种侵犯主要体现在它的“繁荣”有可能会造成现实世界的“贫困化”。
关键词:可能世界;现实世界;元宇宙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4)05-0037-04
收稿日期:2023-10-12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研究”(20BKS006)
作者简介:葛宇宁,副教授,博士,从事哲学与时代发展研究;郜甜甜,助教,硕士,从事德性伦理学研究。
人作为万物之灵,其中一个宝贵之处,就在于人有联想力和想象力。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沉重的肉身,人总是过着一种局限性的生活,无法超越自然法则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限制,但是这不耽误人类放飞心灵,去想象或者建构一个可能世界来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在当下,元宇宙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的话题、一种积极的创造,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会全方面影响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因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哲学视角厘清元宇宙与可能世界、现实世界的关系,对于推进元宇宙的健康有序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也对我们避免陷入一些资本构造的“美丽陷阱”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一、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
可能世界真正成为思想论证或者学术研究的对象是从近代逻辑学开始的,可能世界理论是逻辑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逻辑思想史上,一般认为莱布尼茨最早开启了对可能世界的学术探讨。他认为:“世界是可能的事物组合,现实世界就是由所有存在的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可能事物有不同的组合,有的组合比别的组合更加完美。因此,有许多的可能世界,每一由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就是一个可能世界。”[1]也即,在莱布尼茨看来,每一可能事物或者每一簇可能事物就构成一个可能世界,存在着多个不同的可能世界,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且是最丰富、最好的那个可能世界。
是可能事物构成了可能世界,而可能事物,就是逻辑上不矛盾的事物,也即只要在逻辑上不存在矛盾性的事物,就是可能存在的事物7nlx4b3MA/lthKN7DBsErr4xyMlfnjZnsP2h6FDDbEg=,具有存在的可能性。从哲学意义上来讲,可能性的最极端形式,也即现实性极度匮乏的可能性,就是抽象的可能性,就是逻辑上的可能性。如认为太阳在未来可能会每天从西方升起,虽然这一可能性命题缺乏现实经验的支撑,但是它却不违反矛盾律。由此莱布尼茨对可能世界的定义就可以简化为逻辑上一致或无矛盾的世界[2]129-130。
对可能世界还有一种定义,这种定义在逻辑上不那么严格,或者不那么具有“逻辑性”,但依然对我们思考可能世界具有一定的价值,那就是认为“可能世界包括我们能想象的任何世界,也就是我们能想象的任何一个世界都是可能世界。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中的一个”[3]。这里的界定主要借助了“想象”这一概念,而想象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从弗雷格和罗素开始,现代逻辑学就特别注意避免和心理学发生纠缠,认为心理学的引入会败坏逻辑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可能事物、可能世界,都得借助一定的想象才能呈现出来,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可能世界。正是人类不断想象超越现实世界的美好图像,可能世界才会不断被设定或“创造”出来,元宇宙最初也是人类想象的产物。
由此可见,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复杂的关系,有的认为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的一种,而且是最好的一种,有的认为可能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解决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在于我们给予可能世界何种本体论的认定或承诺。目前,从逻辑哲学上说,关于可能世界的本体论主要存在三种学说:激进实在论、温和实在论、非实在论[2]133-134。在激进实在论看来,“可能世界是某种现实的、独立于我们的语言和思想而存在的实体,它和我们目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完全一样真实地存在着”[4]331。这种观点认为,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一样真实,它要么是一种遥远的真实国度,要么就是现实世界的平行世界。在温和实在论看来,“真实存在的世界只有一个,这就是现实世界,可能世界只是现实世界及其各种可能状况”[4]332。也即在这种观点看来,可能世界不是遥远的国度,也不是平行的世界,只是对现实世界各种可能状态的设想集合。而在非实在论看来,可能世界只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不具有本体论的地位,我们谈论可能世界,并不意味着要给予其本体论的承诺,从本质讲,可能世界就是“言说事物或事态的一种方式”[2]134。
如果我们设定了可能世界的本体论地位,在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关系中,还需要解决一个跨界识别问题,也即要识别出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一主体问题。虽然一些学者认为跨界识别是一个伪问题,尤其是持非实在论的学者多持有这种主张。但是,元宇宙的出现从实践上提出了这种必要,我们需要认定元宇宙的某一主体与现实世界中的某一主体是否具有同一性,因为这涉及现实的伦理责任和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即使抛开元宇宙来说,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这一问题就已经十分突出,尤其在预防和惩治网络违法犯罪问题(如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等)时,如何把网络中的“匿名者”“虚拟人”和现实世界的某个主体对应,以使现实世界的某个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十分必要和急迫的。
从理论讲,设定可能世界,就已经从逻辑上提出了跨界识别的必要性,因为可能世界的提出就是为了实现主体的跨界梦想,尤其是元宇宙的提出更是如此,既然主体是准备跨界的或者说是可跨界的,就存在着主体的跨界识别问题。因此,这是“可能世界理论家们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4]339。目前学术界在跨界主体识别上主要的学说是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也即从本质标准上去判断不同世界的主体是否具有同一性。
二、作为可能世界的元宇宙
“元宇宙”(Metaverse)这一概念是由“元”(Meta)和“宇宙”(verse)组成的,人们普遍认为其重点在于“宇宙”,但是我们认为其重点在于“元”,只有理解了“元”的含义,才能真正洞悉元宇宙的本质,包括其本体论或者存在论问题。
“元”(Meta)虽然有多种含义,但其最根本、最原始的含义是本原的、在什么之后的、在什么之外的。其实,这些含义从哲学视角来看,又是密不可分的。从本原的意义层面来讲,元宇宙要指称的是本原的宇宙,是最充实的宇宙,我们现实世界只是其派生的。从什么之外的意义来讲,它是要指称元宇宙是处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世界,是一种超世界。在什么之后的含义,则是要赋予元宇宙形而上的意味,认为元宇宙是现实世界背后的根据和支撑。
当初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把其研究各种具体事物之外的论述编辑整理成册,命名为“Metaphysics”,直接意思就是“物理学之后”,也即所有具体事物共同的本质与特点,这些内容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可感性,是一种超越性(超物质、超感觉)的存在。中文直接译为“形而上学”。其中,上述“Meta”的三重含义基本都是蕴含的。
较早关注元宇宙问题的学者韩民青就曾把元宇宙界定为:“比我们的本宇宙层次更原始的背景宇宙层次,它具有与本宇宙不同的性质,属于另类宇宙;我们的本宇宙生长在元宇宙的基础上,本宇宙是由元宇宙演化生成的更高一级的宇宙。”[5]学者王寅也通过梳理国内学者对元宇宙的理解和界定,指认元宇宙“在国内语境中指涉具有根本性的、第一的、占据首位的超级性大时空集合”[6]。这里的“根本性的、第一的、占据首位的”也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基本上涵盖了上述关于“元”的三重含义。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把这种可能世界的构想命名为“元宇宙”,多半是出于商业宣传的噱头,它永远不可能达到其宣传的“疗效”。也即元宇宙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可能世界的构想和创造,它最多是现实世界的“副本”,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世界的背后支撑以及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层次的世界、本原的世界。甚至,我们都不能在激进实在论上理解元宇宙,最好采取温和实在论的立场,把元宇宙理解为人类基于一定科学技术的集合,采用数字化呈现的方式,从而构建出的现实世界的可能状况或状态。尤其是以虚拟的方式,把现实世界基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水平未充分展现的状态在元宇宙中尽量充分展开,把尚未出现的存在状态借助元宇宙给虚拟出来,让未来提前“到来”。
有学者批判性地指出,“采用元宇宙这个晦涩难懂的概念,相比于可以顾名思义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代表了一种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趋势,很可能提示了概念的采用者或许并不希望一般大众真正理解这一概念,事实上颇具干扰性披露意味”[7]。这种见解是比较中肯的。基于目前人类的认知水平和元宇宙的设计原理,如果给予元宇宙过高的评价和期望,也许我们收获的将是失望。
元宇宙在本质上就是现实世界的虚拟化,是一种虚拟世界。只是借助各种现代技术集合,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区块链等,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化。不过由于其体验感过于逼真,给人的感觉带来一种现实性的冲击和震撼,且由于其功能超越了单纯的游戏娱乐,造就了更多的社会交际平台和空间,所以有较大的商业开发空间。
元宇宙也需要遵循可能世界的基本法则,即无矛盾性,人的意识再具有创造性,也不可能创造出圆的方、尖的平、白的黑等存在物。元宇宙之所以除了商业功能之外,还能吸引那么多人的向往,就在于在这个可能世界中,逻辑上可以把现实世界的存在物推向极端状态,更好地满足人的欲望。如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很多环境优美的岛屿,除了少数极端富有和拥有极大权势的人可以占有一个或多个岛屿外,大多数人也只有想象一下的“权利”,甚至在现实世界中,一些人毫无立锥之地,更不用说拥有一座岛屿。而在元宇宙里,如果人们放弃了资本的增殖法则,实现人人都拥有一座岛屿的梦想便有可能成为现实,毕竟在元宇宙中造mPX1+bGlg3m4SDlfZqID0w==出一座岛屿,成本十分低廉,甚至可以无限“复制”出来。
此外,元宇宙还被设计出一项新的功能,那就是“创造”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在元宇宙中,人处于相当于神的创造者位置而可以创造任何数字化的虚拟存在”[8]。比如许多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消失的动物,完全可以在元宇宙中“复活”,同时许多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如《山海经》中的奇珍异兽,也可以被人“创造”出来和“虚拟人”“做伴”。
从这个意义上讲,元宇宙作为一种可能世界,是人借助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它和神话世界、文学虚构世界等一样,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性,满足人超越现实世界的渴望。同时,它和以往的可能世界也有所不同,作为一种虚拟世界,却给人一种现实性的体验和感觉,不是仅仅停留在思维、语言上,而是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体验上的虚实融生[6]。也即在元宇宙的理想状态下,人们在其中可以得到一种过去在现实世界中才有的体验,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获得比现实世界更具“现实感”的体验。
不过,对于人在元宇宙的创造状态和能力,也不能过于夸张,把人赋予上帝的地位,或者认为在元宇宙中是思维决定存在,思维有什么,元宇宙就可以创造出什么。须知元宇宙和现实世界一样,都是人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也创造出了许多原本没有的东西,如飞机、火车、宇宙飞船等,甚至现代世界上大部分的存在物,都源于人类的伟大创造,不是世界直接提供给我们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上帝”,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可以“无中生有”。既然如此,在元宇宙中也会是如此,唯物主义原理在元宇宙中也应该可以适用。
三、元宇宙对现实世界的可能“侵犯”
根据元宇宙的设想,大多数学者还是对元宇宙充满担忧的,这就是它未来有可能“侵犯”现实世界,这种侵犯主要体现在它的“繁荣”有可能会造成现实世界的“贫困化”。大致说来,元宇宙未来主要有可能会在以下五个方面造成现实世界的“贫困化”。
其一,人们过去沉迷于元宇宙的生存方式,从而造成现实世界中的主体性贫困。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可能世界,从逻辑上可以推导出,元宇宙可以突破现实世界的某些限制,把现实世界的存在物推向极端状态,乃至“创造”出现实中没有的对象,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某些欲望难以实现的问题,由此一些人会迷恋于元宇宙的生活方式,过度消耗自身的时间和精力,造成在现实世界中生存能力乃至主体能力的弱化。
其二,作为上述问题的极端形式,会出现“意识在元宇宙里获得好过身体经验的任意经验而荒废了身体”,从而“真实世界基本上只剩下生存价值,身体只剩下维持生命的功能,一切存在的意义、价值和精神都归于元宇宙”[8]。很显然的是,能够进入元宇宙的是人的意识,身体必须被留在现实世界,如果意识沉迷于元宇宙,不再回归现实世界,人在现实世界中就只剩下皮囊或变成行尸走肉,现实世界将会因意识的“出走”,出现“荒漠化”。
其三,元宇宙与现实世界共有一个“存在”,元宇宙中的“人”占用的是现实世界的时间。作为一种虚拟世界,其主体绝不能像一些学者所设想的是虚拟原生的产物,也即在元宇宙中,人类有望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主体的“再造”,从而呈现“虚我”与“实我”的分离,乃至对话,这样一来,元宇宙的“居民”就可以摆脱对现实世界居民身份的依赖。从逻辑上讲,元宇宙的主体只能是现实世界主体的“进入”,如前所述,正因为如此,才存在跨界识别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元宇宙的“居民”甚至都不能是我的“分身”,只能是虚拟的“我”,与“真我”同在。假如元宇宙的“我”是虚拟原生的或者是我的“分身”,两者便可以不具有同在性,立马就会产生伦理法律困境,一个人在不同的世界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乃至多件事,哪件事可以归责于“实我”?也即,元宇宙无法摆脱时间的局限性,如果“我”长时间在元宇宙中忙于“创造”,那我为现实世界能够创造的时间就会减少。不管“我”具有多少重身份,“我”只有一个,即使可以实现跨界,我在同一时间内也只能做一件事。
其四,元宇宙会弱化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9]。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实世界作为人的世界,其主要材料构成形式之一就是社会关系。人在社会关系中诉求信任和自由,而这两者都可能因为元宇宙而弱化乃至消失。元宇宙本是人为了摆脱现实世界的一些束缚所构想的可能世界,但是元宇宙能否给人们带来自由却是一个未知数。现代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弱化自由确保安全,各种监控设施的完善和大数据的发达,使得人的隐私无处可躲,私密空间极度萎缩。事物存在的数据化和海量数据的存在是元宇宙的“物理基础”,大数据的运用,尤其在管理和预测上的应用和滥用,会压缩我们自由选择的能力和空间,也使行为责任自负的伦理信条失效[10]。在今天的网络时代,悖论已经出现,本该重视的隐私保护,却成为人们“自愿”的“奉献”,对各种隐私的放弃恰恰是“自由”的结果:人们在各种网络平台上频频曝光自己,以求得更多关注。这种趋势也应该会递归到元宇宙中。此外,元宇宙作为依赖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存在形式,其行动法则是5d3cb2a822d16e780c402afce483b3e6算法而不是直觉信任,当算法为王时,人们既有的信任感就缺少了存在的必要。
其五,沉迷于元宇宙的生活状态,把元宇宙视为真实的世界和存在,造成“虚我”和“实我”不分,当人的欲望在元宇宙中得到极大满足时,就可能对现实世界产生不满,把现实世界的局限和弊端放大化,从而反抗乃至破坏现实世界。究其本原,元宇宙的存在动机和基础是欲望的更好满足,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基于现实世界物质资源、自然法则、伦理道德、法律制度等的限制,人的许多欲望都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元宇宙的设计者就以更好的体验、更丰富的生活形式作为噱头和卖点。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元宇宙在未来的推进有可能会造成现实世界的“贫困化”。但是元宇宙无法杀死现实世界,它对现实世界的“谋杀”一定会失败。没有现实世界,元宇宙就无法存在,人可以在元宇宙中任意地遨游,但必须在现实世界中吃喝和繁育后代,离开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元宇宙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它无法自存。元宇宙虽然可以突破现实世界的一些限制,在逻辑上把现实世界的存在物推向极致。但元宇宙的创造一定来自现实世界,这种创造能力只能扎根于现实世界之中。机器可以学习,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可以超过人类,如下棋等,但是它们的基础是人类智能,人类没有的东西,它们也不会有,人类拥有的某些东西,它们也可能无法拥有,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类生活在社会状态下,在社会交往中建立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机器越“高级”、越智能,就越无法组成社会,因为它们过于“理性”和“算计”,社会状态没有存在的空间。而人除了理性,还有情感、温情、意志、信仰等,既能够算计,也能够“装糊涂”,其实“糊涂”对社会的持存是十分重要的。以人们繁育后代为例,如果人们精于算计,时刻核算生养孩子的成本与收益,很多人很可能会选择不生育,乃至不结婚。久而久之,可能会因为人口的锐减,社会难以存在。
四、结语
行文至此,一个可能出现的疑问就是,我们是否应该承认元宇宙的存在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只是在元宇宙问题上做了一些可能具有批判性的思考,从而有可能使人们不至于对元宇宙抱有过多的期望,乃至厌弃现实世界,成为“流浪者”,空等元宇宙的“救赎”,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元宇宙的价值。元宇宙作为各种最新技术的聚合,在某种意义上会实现技术上的突破和变革,从而反作用于社会,元宇宙的推进会在某些方面造福人类社会,在教育、医疗、抢险救灾、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1]。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元宇宙目前的推动主要还是基于资本增殖的需要[7]。如果不对资本增殖逻辑进行一定的限制,资本就会“绑架”元宇宙,穷人甚至可能无法获得进入元宇宙的“通行证”,因为穷人不具有消费能力,无法进入资本的“法眼”。此外,我们也不要对元宇宙抱有太大希望,人类真正应该致力的方向是携手改善现实世界的治理,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关系,美好生活只能在现实世界中来实现,“天国”只有植根于“尘世”,才会有进入的“天梯”。
参考文献:
[1]张家龙.可能世界是什么?[J].哲学动态,2002(8):12-17.
[2]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逻辑哲学专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王雨田.现代逻辑科学导引: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525.
[4]陈波.逻辑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韩民青.宇宙的层次与元宇宙[J].哲学研究,2002(2):28-34.
[6]王寅.“元宇宙”之技术构镜、叙事症候及哲学反思[J].甘肃社会科学,2023(4):36-45.
[7]邱遥堃.走出虚拟世界:元宇宙热的批判性解释[J].中外法学,2023(4):1080-1099.
[8]赵汀阳.假如元宇宙成为一个存在论事件[J].江海学刊,2022(1):27-37.
[9]沈鑫.元宇宙时代人的“新异化”与破解[J].保山学院学报,2023(4):1-8.
[10][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07.
[11]王龙意,高娣.元宇宙概念下智慧城市的构建与发展研究[J].未来与发展,2022(12):14-19.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