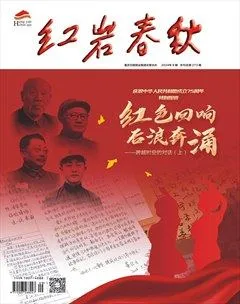乡场上的饭店
很多年前,家乡场上有且仅有一家饭店,饭店的名字就叫饭店。饭店是栋一楼一底的木板房,很有些年岁了,老黑破旧,歪歪斜斜。楼下是店堂兼饭堂,楼上是客房。
由于几乎没有旅客入住,客房就作了店员的宿舍。沿着咯吱作响的木楼梯上去,是五六个小房间,房间很矮,站在地板上,一伸手就能摸到屋瓦。店员在房间里起居作息,有时候动静大点,震得木楼板咯吱作响,楼板缝隙里的灰尘就扑簌簌落到楼下的饭堂里。
饭堂很宽,门口有一座很大的老虎灶,屋里有一个石板大水缸、一个旧的木柜台、几张同样旧的大八仙桌,张张桌子都隙牙漏缝。水缸旁边是一扇木门,拔出门闩,吱呀一声推开,可见屋后一片青青的玉米林。
饭店卖大米苞面两糙饭,有时候也卖净大米饭,卖得更多的是面条、烙饼。顾客走进店堂,把钱递给柜台后面低头打毛线的姑娘,报出吃食品种,姑娘就从抽屉里摸出牌子“啪”地一声按在柜台上。牌子由竹片削成,上面用毛笔分别写着“面”“饼”“饭”的黑字,顾客拿着牌子交给老虎灶前系着围裙的胖女人,就坐在八仙桌旁等。
平日里,饭店一天也没几个顾客,几个胖瘦不一的女人坐在门口打毛线、缝鞋垫、扯闲篇。只有到了赶场天,店里才会热闹起来。
赶场天,街道上的人摩肩接踵,许多人站在饭店前看胖女人捞面,像欣赏一场表演,多少有些眼巴巴的意思,却舍不得掏出角把钱来买一碗吃。这些人都住在离场镇不远的地方。而几十里外的浪水坝、大小泔溪、大河口、马家坝的人来赶场,半夜就得起身。他们爬了一面又一面坡,蹚过一条又一条河,到场上已是中午,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这些大都是男人,他们走进饭店,把钱交给柜台后面的姑娘,大声喊:“三碗面,一人一碗。”取得牌子后,转过身交给老虎灶边的女人,就大模大样地坐在八仙桌边,一边抽着毛草烟,一边等着享受美味。老虎灶边的胖女人朝滚水锅里丢下一把面条,用筷子搅两圈,就捞起来,盛进粗瓷青花大碗里。再从一口鼎罐里舀一瓢泛着油花的汤,淋在面上,朝八仙桌喊一声:“端面!”汉子们就争相跨到老虎灶前,端过面,放在桌上,又撩开衣服,解开腰上的塑胶袋,把老婆半夜起来装在袋里的饭倒进面碗,拿筷子搅匀,就呼呼吃起来。
赶场天,饭店会接待一拨又一拨这样的客人,直到最后一拨客人吃饱喝足,走出店堂,匆匆离去,场上的人也散尽了。天渐渐黑了,风从山上的树林里吹下来,在街上呼呼刮过,女人们打着寒噤关门打烊,场上复归寂静。
赶场天是方圆几十里的人的节日,也是饭店的节日。过了这一天,饭店的人早起背完水,又坐在店门口聊天、打毛线、缝鞋垫,将简单无痕的日子重复着过下去。
多年后我重回故乡,在一排贴着白色瓷砖的水泥洋房中间,看到了当年的饭店。几十年过去,饭店更黑了,也更老了,几乎是摇摇欲坠。店门口仍然是一座大的老虎灶,在灶前捞面的,还是当年那个胖胖的女人。她有些老了,也更胖了,但声音、仪态跟气质仍趋于温和沉静,让人不由相信,在她的身上,曾有怎样一段寂静清凉的时光流过。
编辑/娄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