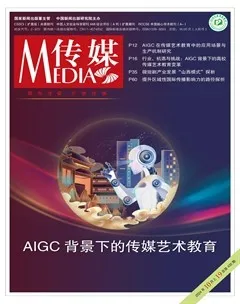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途径与内容
摘要:早期华夏文化通过贸易、战争、人口流动等多种途径被传播到东北亚地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重点梳理了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具体传播内容,包括货币、纸张、政治制度、文学等方面的传播。货币的传播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发展;纸张和印刷术的引入推动了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系的传播增强了政治治理的有效性;文学作品的传入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东北亚地区在吸收华夏文化精华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文化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早期华夏文化 东北亚地区 华夏传播 传播史
华夏文化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其丰富的观念、机制和技术对后代有着深远的意义。华夏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对周边族群多有辐射。自燕昭王起,燕国经略东胡、箕子朝鲜等东北地区族群,使得华夏文化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东北亚地区(包含今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笔者重点梳理了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途径及内容,认为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途径主要有贸易、战事、人口流动等,而传播内容具体为货币、纸张、政治体制和文学等。本研究尝试为早期华夏文化传播活动探索其传播学解读视角,揭示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
一、早期华夏文化及其传播学研究视角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经过不断的民族融合发展进程,内迁戎狄蛮夷逐渐融入华夏族,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华夏”一词发展成为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早期华夏文化具有强大辐射作用,为周边地区民族的开化和文明进步带去了新的曙光。
华夏文化是以古代中原地区为载体,包含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内容的综合性文化体系。其主体清晰、范围广博,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态、手工业、建筑艺术等物质文化,以及儒家理论、道家哲学、法律法规、文艺创作等非物质文化。华夏文化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和革故鼎新,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点和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华夏文化因其出色的科技而著称。“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华夏文化科技成果的杰出代表,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而且深刻影响了东北亚地区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华夏文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多有交叉。除考古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外,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开始关注华夏文化的传播史。如学者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中国文化中的传播》一文中,围绕古代文化与传播的关系阐述了华夏文化,对华夏文化传播的概念、特征和内容进行了探讨;学者谢清果在《华夏文明研究的传播学视角》一文中,从传播学的视角解读中国古代文明,把传播研究拓展到了文明的范畴,考察早期华夏文化的特征;学者潘祥辉在《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一文中,将中国古代传播的媒介进行了考察,对华夏本土传播学的议题和思想进行了探讨。综上,笔者通过对华夏文化及其传播学研究视角的梳理,确立了本研究的传播史学面向,并据此梳理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途径与内容。
二、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途径
早期华夏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主要通过贸易、人口流动、战争等途径逐渐传入东北亚地区,并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基于陆海“丝绸之路”的贸易传播途径。“丝绸之路作为一条交通路线,其意义不在于交通路线本身,而在于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各个国家、民族通过这条路线所进行的互通、互动。”这条贸易通道,把货币、纸张、丝绸、瓷器等早期华夏文化中的诸多元素传播至东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不仅是经贸往来的过程,也是文化沟通与文明交融的过程。早期华夏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向东北亚地区传播的金属货币影响了当地产业布局,节约了贸易和经贸活动的时间;造纸技术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为文献记录和知识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高效地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海上贸易是早期华夏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隋唐时期,早期华夏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地,广州、明州(今宁波)等海港成为海上贸易中心。中国的绸缎、陶器、茶叶等货品不断通过海港出口,同时也将早期华夏文化与科技成果传播出去。在日本,海上贸易不仅为其带去了大量的中国商品,同时也令日本接触并引入了儒家、佛教理论,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在朝鲜,海上贸易也为其带去了商业与文化的双重利好,推动朝鲜半岛的社会进步。
2.基于战事和外交活动的政治传播途径。燕秦汉时期,是早期华夏文化通过战事传播的重要阶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逐步将早期华夏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和东北地区。汉武帝通过数次对外战争,进一步将华夏文化输出至东北亚地区。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法规及农业生态逐渐被东北亚地区族群借鉴与学习,如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官僚制度对朝鲜半岛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及至唐朝,华夏文化借由对外战争和外交手段,进一步在东北亚地区广泛传播。唐太宗和唐高宗通过多次对外战争,建立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手段,唐代中国与日本、朝鲜等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文化联络。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学、法律、礼仪、音乐等被传播到日本和朝鲜,影响了当地文化的样态与类型。
3.基于人口流动的人际与组织传播途径。学者和僧侣是华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唐宋时期,大量来华学习的日韩学者、僧侣、使团、官员,将华夏文化带回本国,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文化发展。在日本奈良时代,遣唐使不仅对中国的政制、法度有所研究,而且将大量的佛经与典籍带回日本,这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宗教、思想与文化。同样,在朝鲜,文士和僧众的交流也为朝鲜半岛文化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佛学和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在日本平安京(今京都),也有许多中国僧人、学者立身处世,成为早期华夏文化对外传播事业中的中流砥柱。
中原人口迁徙为东北亚地区带来了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人情。因战事、政治或经济原因,一些中原人迁居东北亚地区,逐渐成为当地居民和商人,不仅把古中国的商品和技术输出至移入国,还传播了中国的生活习俗、宗教文化和社会意识,推动了文化交流与文明融合。例如,在汉朝时,一些中原移民定居朝鲜半岛的乐浪郡,改良了当地的农业生态、手工业和商业模式,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内容
早在燕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就开始经营东北地区,设郡置县发展经济,传播汉字文化教化民众,使得华夏文化进一步向东传播。目前的考古材料表明,燕秦汉时期东北亚地区就出现了具有华夏文化特色的器物,如铜币、铁制农具、长城等。至隋唐时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进程达到了一个高峰,东北亚诸多民族政权由学习华夏器物的初始阶段逐步过渡到学习华夏制度、文学、艺术的高级阶段。早期华夏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传播内容主要包括货币、纸张、政治制度和文学典籍。
1.金属与纸质货币的使用。中国的金属货币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交易工具和方式。金属货币的出现和普及,使商品交换不再拘泥于传统的物物交换形式,交易便捷性和交易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中国古代铜钱形制多样、制作精良,经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流入东北亚地区。这些铜钱在朝鲜和日本不仅扮演了货币的角色,还影响了当地制造和流通货币的方式。如日本仿照唐钱,于奈良年间自铸铜钱,也是日本国历史上第一种官币,名为“和铜开金”,该命名直接体现了中国铜币对日本货币体系的影响。同样,朝鲜半岛国家新罗也在中国货币体系的影响下发展了本国的货币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其国际经济往来与地区商业繁荣。
作为早期华夏文化的一项重要发明,纸币助力了商业贸易活动向东北亚地区的传播。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宋代的“交子”就是一种轻巧易携带的货币。元朝更广泛地使用纸币,蒙古帝国的疆域扩展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也扩大了使用纸币的范围,元朝的纸钞制度逐渐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的货币体系。尤其是朝鲜高丽、李朝时期,更是大量使用纸币。纸钞的流通在方便商业活动的同时,也促进了财政制度的变革,提升了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
2.印刷术与造纸术的大规模推广。纸张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向东北亚地区传播,对当地文化教育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一种轻巧耐用、易于制作的书写材料,纸张取代了粗重的竹简和昂贵的绢帛,使记录和传播文献更加方便。在日本,造纸术的传入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与文化的发展。日本在奈良、平安时期,开始大规模生产和使用纸张,用于书写经书、佛经、官方文书等。纸张的使用使知识更易于积累、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同样,造纸术的传播也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文学创作和宗教思想。尤其是朝鲜王朝时期,纸张被用于印刷佛经和儒经,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和儒家思想的普及。
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北亚地区传播的中国古代雕刻印刷和活字印刷技术,已成为促进当地文化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如在日本奈良时期,日本从唐朝引入雕版印刷技术,印制了《百万塔陀罗尼经》等大量佛书。同时,日本进一步发展印刷工艺,逐步印刷《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本国的文学著作和历史典籍。
3.中央集权制度与官僚体系的借鉴。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效率提升,被东北亚地区国家借鉴和学习。以君主为最高权力中枢的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为保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建立了严密的官僚制度和法律体系。日本受唐朝影响,在奈良和平安时期开始仿效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奈良时期,日本借鉴唐王朝的政治体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和律令制,实行“大化改新”改革,强化了天皇的权威,巩固了国家的执政能力;平安时期,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官僚体系完备,行政效率提高。同样,在朝鲜半岛,高丽王朝和李朝都借鉴了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官僚体系和法律制度;尤其在李朝时期,朝鲜的中央集权制度同儒家思想结合紧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政治体制,在促进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科举制度不仅为古代中国提供了选官用人的机制,也推动了官僚体系的形成,这亦对东北亚地区的选任制度和官僚体系产生了影响。例如,日本借鉴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在奈良和平安时期建立了自己的施政体系。日本在奈良时期推行律令制,确立中央和地方行政架构,对选任官员进行规范;在平安时期,官僚制度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制稳定,治国理政能力得到提升。官僚制度在朝鲜半岛的应用和发展也十分广泛,高丽王朝和李朝时期,朝鲜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任用了一大批有才能的人,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官僚制度;特别是李氏朝鲜时期,其形成了独特的儒学官僚体系,有效提升了行政效率、推动了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
4.文学典籍的译介。《论语》《道德经》等中国经典文献在东北亚地区广为流传,对当地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经典文献既记录中国的文化精髓,又是传播思想的重要载体。在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大量中国经典文献被引进和翻译。奈良时期,日本从唐朝引进了《论语》《孟子》等一大批儒学经典,并将其发展为日本教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安时期,日本进一步吸收了对其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具有意义重大的《道德经》《庄子》等中国道家经典。同样,中国经典文献在朝鲜半岛亦广泛传播。高丽王朝和李氏朝鲜时期,朝鲜大量引进了中国原创的儒家典籍和译介的佛学经典,尤其在李氏朝鲜时期,经学成为其国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文化繁荣和思想发展的儒家学者。
四、结语
早期华夏文化对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来说,其以贸易、战事、人口流动等为传播途径,以货币、纸张、政治体制、文学等为传播内容,不仅促进了东北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推动了文化的沟通与文明的融合,提升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治理的高效性。上述具备华夏特色的文化符号在东北亚地区生根发芽,逐渐融入并影响东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样态。
(作者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7BKG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吴东权.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M].台北:中视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2]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J].考古学报,1997(03).
[3]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中国文化中的传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潘祥辉.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5]傅朗云.东北亚丝绸之路历史纲要[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6]白云翔.公元前一千纪后半中韩交流的考古学探究[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04).
[7]谢清果,等.华夏文明研究的传播学视角[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9.
[8]董莉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济南:山东大学,2021.
[9]赵振成.从考古发现看燕国开拓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4-26.
[10]陆晓光.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索[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11][日]樋口隆康,蔡凤书.弥生时代青铜器的源流[J].辽海文物学刊,1995(02).
【编辑:曲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