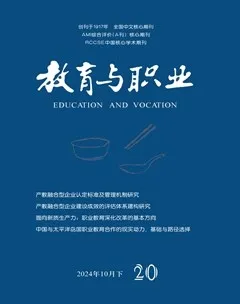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动力、基础与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催生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职业教育合作的新机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的职教合作擘画了蓝图,深层次教育合作基础为双方的职教合作搭筑了基石,中资企业“出海”为双方职教国际性产教融合赋能,“职教出海”经验助力双方的职教合作行稳致远。深化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不仅是南太平洋地区大国博弈的政治诉求,更是推动岛国产业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于提升岛民就业率、减少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职业教育合作可以尝试以下路径:以政策机制为关键点,引导共创;以示范项目为着力点,激发动能;以政侨企校为突破点,凝心聚力。
[关键词]职教出海;太平洋岛国;职教合作
[作者简介]刘建峰(1981- ),男,山东济南人,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刘雨晨(2000- ),女,山东潍坊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在读硕士。(山东" 聊城" 252000)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20-0031-08
“职教出海”是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主题,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重要支撑。太平洋岛国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扼守亚洲与南北美洲的海上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当前大国博弈的主要战场[1][2][3]。随着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推进,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4]。太平洋岛国主要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汤加、萨摩亚、库克群岛、帕劳、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图瓦卢、瑙鲁、纽埃等14个独立主权国家,陆地总面积仅为55万平方千米,但拥有2800万平方千米的海洋专属经济区[5],属于典型的“陆地小国、海洋大国”。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太平洋岛国在全球市场上仍以资源输出为主,基础产业发展能力有限,这导致海外移民人口快速增长,人才流失问题突出[6],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太平洋岛国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迫切需要同中国加强合作,以提升人才储备和产业发展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太平洋岛国实施国际教育援助,从早期提供来华奖学金名额到设立孔子学院,再到直接向岛国本土派遣教育援助教师,国际教育援助的方式不断更新[7],职业教育援助越来越受到太平洋岛国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简称中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可以为太平洋岛国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太平洋岛国经济社会的内生发展动力,同时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
中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应立足太平洋岛国的国情,有针对性地输出中国方案,推动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基于此,笔者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汤加、萨摩亚等六个太平洋岛国开展实地调研,通过跨国多点民族志、叙事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专注收集四类不同分析层次的数据,即太平洋岛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政策、太平洋岛国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太平洋岛国本土企业的人才需求、中资企业的人才需求,最后通过两个以上来源交叉检测来验证数据的有效性。从现实动力和基础出发,探索中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有效路径,对于加强中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布局规划和精准实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太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动力
(一)政治动力:南太平洋地区大国博弈的政治诉求
随着全球治理时代的发展,南太平洋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大国博弈再次加剧[8]。中国需要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国际合作,深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共享发展经验,推进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树立大国形象的正向认同。太平洋岛国希望获得中国的支持,提升国际地位和对南太平洋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也为太平洋岛国提升国际影响力、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新契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9],担负重要的使命[10]。斐济、巴新、萨摩亚、汤加、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基里巴斯等国已同中国签署了教育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18年,我国教育部与汤加教育部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汤加王国教育部关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支持建立聊城大学汤加学院,协助汤加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2022年5月,在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上,中方提出将全面落实2020年到2025年向太平洋岛国提供25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3000个研修研讨名额;中国“鲁班工坊”将向岛国提供首批20个职业技术教育留学生名额。中太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可以输出职业教育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有助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并具有共同发展意识的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有利于促进中太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
(二)经济动力:产业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南太平洋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稳步实施,职业教育合作将成为推动中太产业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太都需要大量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来推动项目投资建设。一方面,太平洋岛国多数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陆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且海外务工人员数量快速增长,面临高质量应用型技能人才缺乏的严峻挑战,产业发展能力受限,社会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严重不足。所罗门群岛国立大学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主任所罗门·皮塔(Solomon Pita)表示,“在所罗门群岛某些行业不得不招募海外人员建设国家,所罗门群岛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对国家建设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华商和中资企业赴太平洋岛国投资创业。据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经济商务处统计,2019年,华商企业在斐济注册投资项目共172个,占斐济吸引外国投资项目的46.7%,中国成为斐济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太平洋岛国华商和中资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劳动力资源短缺、技能水平低等人力资源供给问题。有华商表示:“太平洋岛国资源很好,也有很好的海外投资政策,但当地员工的专业技能很难满足企业需要。”也有华商表示:“我们需要既懂当地文化又懂技术的本土人才,他们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扎根,但很难找到。”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有利于促进职业院校尤其是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才走进太平洋岛国,也可以为太平洋岛国培养本土专业技术人才。于中国而言,可以有效刺激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于太平洋岛国而言,可以在不断吸引域外投资的同时积极转化海外技术溢出,实现产业转型和经济持续发展。
(三)社会动力:提升岛民就业率和减贫的迫切需求
太平洋岛国的主要产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旅游业,属于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内外部市场环境、自然灾害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11],自主发展能力严重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滞后[12]。多数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发展依赖海外侨民汇款和外国援助,其中10个太平洋岛国在世界援助依赖国排名中位列前20。2022年,太平洋岛国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净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普遍超过13%,其中图瓦卢最高,占比为79.9%。太平洋岛国亟须从传统农业经济向多元化、现代化的经济结构转变,提高居民就业率。斐济驻华商务参赞拉蒂什·辛格(Latish Singh)表示,“斐济也想拥抱数字化时代,发展数字化经济,将本国传统经济通过数字化逐步升级,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深与中国在多产业的经济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有华商表示,“巴新当地人技术水平很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社会治安很不理想”。瓦努阿图有华商表示,“瓦努阿图土著人要么种地、要么在酒店打工,还有一部分到新西兰果园里务工。但凡懂点技术,在岛国都能过得不错”。汤加前驻华大使、汤加—中国友协秘书长西亚梅利耶·拉图(Siamelie Latu)表示,“中国的诸多发展成就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力量……我们十分钦佩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期待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我国学者李兴洲认为,职业教育是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精准扶贫方式[13]。多年来,中国一直向太平洋岛国派遣技术专家,建设农业和渔业示范项目,培训技术人员,助力太平洋岛国减贫发展。
二、中太职业教育合作的现实基础
(一)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太职教合作擘画蓝图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斐济,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斐济,习近平主席还同8个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了首次集体会晤,共同决定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再次同建交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将双方关系上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太双方陆续建立了经贸联委会、农业部长会议、渔业合作发展论坛等双多边对话机制,以及应急物资储备库、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减贫与发展合作中心等一系列合作机制,与太平洋岛国合作机制初步形成。2021年,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渔业合作发展论坛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渔业合作发展论坛广州共识》,为中太渔业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2022年,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访问太平洋岛国期间宣布将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菌草技术示范中心。2023年,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中心、中国—太平洋岛国农业合作示范中心正式启用。政府之间的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和高级别对话机制为中太岛国职业教育合作擘画了蓝图。一方面,太平洋岛国地缘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多变,中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设是双方职业教育合作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6+1”合作平台建设精准定位太平洋岛国的主导产业和国计民生的核心问题,将成为中太职业教育合作重要的着力点和载体,可有效支撑相关专业合作的落地实施。
(二)深层次教育合作基础为中太职教合作筑基石
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太职业教育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首先,中太已建立良好的教育合作机制。中国向岛国提供政府奖学金,支持岛国学生来华留学,同时在巴新、萨摩亚、汤加等国援建了小学、中学、大学等一批学校项目。2015年开始,我国先后举办了太平洋岛国高级公务员培训班、太平洋岛国青年领袖研修班、“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太平洋岛国)等,培训了大批管理人才。2023年,首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教育部长会在巴黎举行,中国承诺与太平洋岛国携手,为各国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其次,中太已开始探索适合岛国发展的职业教育实践路径。2018年,聊城大学汤加学院成立。2022年,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南南合作线上培训班成功举办。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举办了中国—太平洋岛国渔业技术线上培训研讨班,目的在于加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创新渔业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促进海洋渔业产业和职业教育的合作。
(三)中资企业出海赋能中太职教国际性产教融合
协同中资企业走出去,为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是中国“职教出海”最鲜明的特征。中资企业和华商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发展迅速,已成为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12年,中冶集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投资的瑞木镍钴项目正式投产,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境外最大的镍钴矿投资项目;同年,烟建集团进入斐济,十余年来扎根斐济,承建了20多个大型基建项目,为当地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技术支持。此外,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所罗门群岛承建了2023年太平洋运动会体育场项目;中铁建设集团巴新公司承建了新爱尔兰省议会大厦;中国远洋渔业公司在太平洋岛国从事渔业捕捞和水产养殖,建造渔港和渔船维修设施,以支持当地渔业发展。有中资企业负责人认为,中资企业在太平洋岛国投资需要大量既懂中国技术标准又懂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当地员工。一方面,太平洋岛国对外资企业雇佣当地人比例有要求;另一方面,雇佣当地员工也能节约企业人力成本。有中资企业负责人认为,“太平洋岛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滞后,难以支撑中资企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而且当地员工与中国企业文化融合非常困难。为保障国际产能合作安全有效,实现当地员工的在地职业技能培养非常迫切”。因此,中资企业在太平洋岛国的在地化发展蕴藏了中国“职教出海”大有可为的发展空间。
(四)“职教出海”经验助力中太职教合作行稳致远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成效显著,可以为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提供借鉴经验。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非洲援建了苏丹恩图曼职业培训中心,是苏丹最重要的职业培训机构之一[14]。之后,中国陆续在非洲其他地区援助建立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如援坦桑尼亚心脏外科诊疗培训中心、援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援赤道几内亚职业技术学校、援纳米比亚青年培训中心、援乌干达工业技能培训与生产中心等。中国与东盟国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领域范围广泛,包括农林牧渔、电子信息、医药卫生、交通运输、旅游、财经商贸、装备制造、能源动力与材料等领域[15]。2023年,我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合作共建的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揭牌,这是中国职业教育领域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同年,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柳工机械印尼有限公司、雅加达国立理工学院三方合作共建中国—印度尼西亚智能运载装备现代工匠学院。从中国在泰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鲁班工坊”,到中亚首家“鲁班工坊”——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启运,截至2023年,中国已在海外25个国家建立了27个“鲁班工坊”,开启了中国职教品牌化、体系化服务国际社会的历程。2023年,山东省启动实施职业教育海外“班·墨学院”建设计划,推动职业教育“走出去”,面向中资企业海外本土员工、当地居民开展“中文+职业技能”培训。中国与非洲、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领域广阔且较为成熟,可以为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提供重要经验。
三、中太职业教育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以政策机制为关键点,引导共创
政策体系和相应的制度基础是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跨域治理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治理目标的实现[16]。在中太教育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中太职教合作政策机制建设尤为重要,对此,应以政策机制建设为关键点,通过优化发展政策、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健全工作机制以及完善沟通机制,形成制度化保障,优化中太职教合作发展环境,推进职教合作高质量发展。
第一,优化发展政策。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组织实施层面提出要强化政策扶持。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应积极出台支持新时代中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完善各地关于中太职教合作化的发展政策,将职业教育“走出去”作为中太教育合作的重点领域,并提供相应的政策、资金和资源支持。对参与“职教出海”的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给予支持,对成就突出的职业院校、企业、行业组织等给予奖励,鼓励多方主体参与中太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中太合作交流的纽带和桥梁。要做好相关政策文件的宣传和解读工作,确保政策能有效执行,提升社会各界对中太职教合作发展的认知和支持力度,为中太职教合作创设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二,共建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是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前置性工程[17]。推进中太职业教育合作,必须与太平洋岛国的各国架设互联互通的桥梁,建设区域性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打破不同教育形式之间的隔阂,实现学习成果的相互认可和多维转换。一方面,我国要立足国情,不断完善本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根据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实行的学制年限以及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合理划分框架级别,建设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资历转换机制。不断丰富分配规程、条件设置、学时要求、学分结构等方面的规定,确保资历框架科学翔实。同时,在完善本国资历框架时,也要吸取他国优秀教育经验,在与他国资历框架对接的过程中凸显本国特点。另一方面,明确中太合作区域内各国的资历互认标准。应根据区域内各国不同的职业教育资历框架,通过对话与协商,共同搭建不同国家资历等级互通和标准互认体系。基于此,区域内每个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资历可以通过这一体系实现职业教育国际资历互认。
第三,健全工作机制。健全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职业院校、海外企业工作机制,明确职责定位,强化协同合作。一是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开展职教合作的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设立中太职教合作专项基金支持重点合作项目,激发各方参与热情。二是搭建中太校际合作网络及行业组织协作平台,促进中太之间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与项目合作,拓宽国际合作渠道。同时,还要注重中太职教合作质量监控与评估,建立健全国际合作项目评估体系,确保合作成效与预期目标相符,及时调整优化合作策略。
第四,完善沟通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沟通机制,是深化职业教育领域国际合作、促进教育资源与经验共享的关键。首先,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在多方共同参与的职教合作项目中,明确各方职责,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尤为重要[18]。通过“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合作论坛建立中太职教合作沟通机制,定期召开中太国际职业教育论坛、研讨会、视频会议以及建立在线交流平台等,实现跨国界、跨时区的即时沟通,确保信息交流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其次,明确沟通内容与重点,围绕中太职业教育政策、课程标准、教学方法、师生交流、科研合作等核心议题,制订详细的沟通计划,确保每次沟通都能聚焦问题、达成共识。最后,也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借助其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搭建更广阔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中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沟通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二)以示范项目为着力点,激发动能
开展职业教育合作援助项目是拓展中国职教输出的新途径,也是探索中国与合作国家职教科研交流的新方式[19]。中太职教合作以建设示范项目为着力点,通过精准定位太平洋岛国发展需求、以“6+1”合作平台为支撑、探索中太“数字大学”建设以及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等,共同激发中太职教合作动能。
第一,精准定位太平洋岛国发展需求。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结构和速度,既受社会需求的激励和拉动,又受社会需求的约束[20]。因此,在探索中太职教合作新路径时,要精准定位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需求,与大使馆开展合作研究,深入调研各岛国的具体需求,确保合作内容贴近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有效提升岛国人民的就业竞争力与自主发展能力。同时,要组织专家团队对太平洋岛国的职业教育现状进行深入调研,了解其实际需求和发展瓶颈,为合作方案制订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可以通过派遣教师、提供教学资源、联合办学等方式,帮助太平洋岛国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符合当地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人才。
第二,以“6+1”合作平台为支撑,打造中太职业教育品牌项目。结合中太双方的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针对双方共同关注的行业或领域,设立专业化、定制化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以“6+1”合作平台领域为基础,开展职业教育课程互认、师资交流、实训基地共建、在线教育资源共享以及科研项目等深层次、多方面的合作项目,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逐步打造和推广中太职业教育品牌项目。
第三,探索中太“数字大学”建设。在职业教育领域,数字化赋能被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21]。中太“数字大学”建设是当前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探索,旨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育资源、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由于岛国网络基础设施滞后,一方面,我国要帮助太平洋岛国构建覆盖广泛、互联互通的网络体系,确保师生能够随时随地接入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在数字资源体系建设上,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丰富的在线课程库、学术资源库和虚拟实验室,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此外,也应逐渐完善中太资源共享机制,建设高性能的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平台,为教学、科研和管理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持。
第四,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一是为了提供政策咨询,旨在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二是生产学术知识,旨在探索和生产知识[22]。基于此,利用我国海外办学的经验,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各国在产业、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搭建起产业、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桥梁。一是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深入理解太平洋岛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及社会结构,发掘双方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互补优势,为中太职教合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更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宝贵的决策参考,助力构建更加紧密、高效的合作机制。二是围绕职业教育创新、产教融合、技能人才培养等热点议题,依托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举办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行业领袖等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三是国内专门研究太平洋岛国的组织和机构要及时关注国际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及时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为中太职教合作提供最新的研究动态。
(三)以政侨企校为突破点,凝心聚力
构建政府主导的职业教育三方联动合作机制,是推动区域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23]。由政府引领方向、华侨搭建桥梁、企业注入活力、学校贡献智力,四方携手,凝心聚力,共同促进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更好地发展。
第一,校企合作联合办校。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校企合作办校将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模式。我国要积极探索与太平洋岛国政府、企业以及学校的合作新模式,共同开展联合办学,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在校企合作办校的过程中,我国职业院校充分发挥其在教学管理、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与在太平洋岛国的中资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确保教育内容紧密贴合当地实际需求。同时,太平洋岛国的中资企业也应积极参与,提供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实践机会。此外,华侨在太平洋岛国拥有广泛的人脉和资源,可以为我国职业院校与当地中资企业、学校搭建沟通的桥梁,为职业院校学生搭建更多的实习实训平台。通过华侨的引荐和协调,促进各方了解和信任,为合作项目的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校企联合开发教学资源。通过深度融合中太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与企业的实践资源,共同设计、开发和实施一系列符合行业需求、贴近实际工作场景、精准对接中太岗位需求的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职业院校发挥其在教育教学理论、课程设计、教学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企业则以其丰富的行业经验、技术标准和实际工作案例为支撑,双方携手构建既具理论深度又具实践广度的职业教育体系。华侨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协助双方确定合作领域、制订合作计划并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实力和教学水平。
第三,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中太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的紧密合作,精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培养出一批具备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高素质人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首先,职业院校根据太平洋岛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求,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确保学生所学知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其次,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工学交替等教学模式,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技能、提升职业素养,从而在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岗位需求,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最后,华侨可以协助职业院校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海外人才,为地方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推动职业院校与中资企业联合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等,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地方产业升级和转型。
综上所述,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是促进双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太平洋岛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政治体制因素的影响,也有大国博弈、地缘环境以及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增加了中太职业教育合作的复杂性。总体而言,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机遇大于挑战。首先,中国同太平洋岛国交往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化,双边已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次,中国同太平洋岛国资源和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职业教育合作共赢的潜力巨大。最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为中太职业教育合作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中太职业教育合作对于中国来说,可以为在岛国的中资企业提供可用人才,开拓更宽领域的合作项目,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贸易机会和更广阔的市场;对于岛国而言,可以为岛国提供人才,激发岛国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岛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的发展。
此外,中太职业教育合作对于“职教出海”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在理论上,重点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拓展了“职教出海”理论研究的维度;在实践上,中太职教合作将在深化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为太平洋岛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切实援助,还能进一步激发资源和产业合作潜力,促进双方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汪诗明.区域与国别视阈下的大洋洲研究[J].俄罗斯研究,2022(2):40-61.
[2]陈晓晨.“人的安全”与地区主义:太平洋岛国地区安全研究[J].国际政治研究,2022,43(5):70-89+6.
[3]陈晓晨.多重内涵的“蓝色太平洋”——太平洋岛国对地缘政治新环境的应对[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5):149-158.
[4]吕桂霞.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及未来前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7):70-77.
[5][8]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196.
[6]倪鹏.太平洋岛国地区移民活动及治理问题析论——以气候移民为中心的考察[J].世界民族,2021(4):76-87.
[7]秦升.以发展援助为支点打造新时期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关系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9(5):16-19.
[9]熊建辉.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N].中国教育报,2016-08-25(3).
[10]黄尧,邓文勇,陈伟.“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动因与路径[J].教育科学,2020,36(4):83-89.
[11]Chloe K.H. Lau, et al.Chinese Venturers to Pacific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Travel and Lifesty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9(1):665.
[12]周余义,杨阳,胡振宇.2019年太平洋岛国经济形势[M]//陈德正,吕桂霞.太平洋岛国发展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5-46.
[13]王斯迪.职业教育助推减贫的实践案例与行动策略——“职业教育助推全球减贫进程论坛”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22,43(24):59-61.
[14]梁克东.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理念与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6):69-74.
[15]王忠昌,侯佳.中国—东盟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的现状、困境及路径——基于254个平台的分析[J].教育与职业,2023(4):44-51.
[16]张菊霞.“一带一路”背景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困境与路径——基于跨域治理的视角[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2):31-38.
[17]蔡晓棠,王玉苗.我国职业教育资历框架的价值意蕴、建设现状及路径探析[J].成人教育,2023,43(5):69-75.
[18]马雁,孔晶,李珊珊.中非职业教育合作模式研究——以潍坊职业学院为例[J].现代职业教育,2022(40):109-111.
[19]祝蕾,胡宇,张慧波.高职院校援外项目的现实困境和行动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6):11-15.
[20]朱新生.江苏省职业教育需求变化与政策调整[J].教育研究,2004(11):87-91.
[21]伍星,章谦.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的路径[J].继续教育研究,2024(9):88-93.
[22]谢韬.区域国别研究: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9(3):36-46+242.
[23]王丽雅,魏春梅.高职院校创新“政企校”联动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探索[J].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13(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