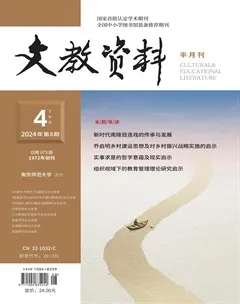在边界穿行:水仙花的跨国书写
摘 要:北美华裔文学之母水仙花的唐人街故事和华人书写已为读者所熟悉,但随着其生前发表在报刊上作品的不断再发现,水仙花的思想有待进一步认识。近年来,学界新发现了一些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牙买加金斯顿报纸上的报道、穿越美加边境的游记以及以加勒比海为背景的虚构故事。借助跨国主义视角分析以上各类新归文本可以看出:水仙花在写作中不仅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亚之间以及美洲国家之间的跨国实践,而且对异域进行了跨文化想象,表现出情感跨国主义的倾向,从而为构建人类情感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路径。
关键词:水仙花;边界;跨国主义;情感共同体
水仙花(1865—1914年),原名伊迪斯·莫德·伊顿(Edith Maude Eaton),是一位欧亚混血儿。她出生在一个跨国、跨种族结合的家庭,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两人在上海恋爱结婚,婚后返回英国;之后又从英国移民至美国,最后定居加拿大。水仙花从小就跟着父母往来于英、美、加之间,长大后为了谋生又经常穿越美加边境,辗转于美国东西部,并一度到加勒比海地区工作。除了散见于报刊的新闻报道和短篇故事,她生前仅正式出版了《春香夫人》这一部文学作品。尽管如此,水仙花在其去世70年后重新获得了关注,并因其在作品中描写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华人的生活而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先驱。[1]由于水仙花拥有一半中国血统,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正面的华人形象,因此她的作品,尤其是唐人街故事,在美国华裔文学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研究。其实水仙花的创作不局限于美国,还涉及中国、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她是一个不断穿越边界的作家。
本文在旧有唐人街故事的基础上,结合加拿大学者玛丽·查普曼(Mary Chapman)新发现和整理的文本,特别是水仙花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牙买加金斯顿报纸上的报道、穿越美加边境的游记以及以加勒比海为背景的虚构故事,从跨国主义视角来分析水仙花的作品。水仙花不仅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亚之间以及美洲国家之间的跨国联系和互动,而且展现了跨越文化的异域想象,在表现情感跨国主义之余,呼吁构建一个人类情感的共同体。
一、水仙花早期跨国实践的书写
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又称跨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理论思潮,主要研究以移民群体为主体的跨国、跨文化现象。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员、资本、信息、技术及思想等的跨国流动现象日益频繁,跨国主义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跨国主义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描述的是由跨国实践参与者建立起来的、超越民族国家及其边界控制的社会网络”[2]; 第二,它是关于这种社会现象的理念和立场,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强调跨国社会实践的全球视野。自1990年以来,跨国主义视角被引入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学。跨国主义的文学研究旨在“弃置文学史的民族主义叙事,把作家和作品置于跨国、跨地域的网络之中,关注其跨国想象,揭示文学中的跨国互动”[3]。
尽管跨国主义理论流行是近些年的事情,但跨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早已有之。生于1865年的水仙花,见证了美国对外寻求殖民扩张、对内发展西部经济的历史,敏锐地观察到日益频繁的跨国活动,并在作品中记录了当时跨太平洋和美洲境内的各类跨国实践,包括移民、跨国旅行等,展现了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联系与互动。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美华人社会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水仙花详细描写了当时华人从中国移民至北美的情况,包括人员构成和入境方式。当时正值《排华法案》实施,“黄祸论”(即东方黄种民族威胁论)盛行,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劳工进入美国,中国移民美国的人数较之19世纪中期的每年几万逐渐降至几千、几百、几十,在1887年甚至降至10人。[4]根据1882年的《排华法案》,只有政府官员、教师、学生、商人和旅游者这5种人可以获得豁免。水仙花的唐人街故事基本以商人、学者及其家人为主人公,正是这一社会背景的如实反映。水仙花刻画了不少从中国移民至美国的商人及其家人形象,如《春香夫人》中的春香夫妇,《新世界的智慧》中的宝琳夫妇。
这一时期合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数量少得可怜,与之前浩浩荡荡的华人劳动力大军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9世纪中期,美国加州发现金矿,吸引了大批为生活所迫的中国人赴美淘金。与此同时,美国和加拿大为了开发西部,发展经济,从海外引入了大量劳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雇佣的华人劳工。尽管北美排华,但19世纪末期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境况,迫使中国劳工不顾恶劣形势继续前往美国。他们发现美国禁止华人入境后,就尝试经由加拿大、墨西哥等地入境,甚至不惜以非法方式入美。水仙花在新闻报道和短篇故事中多次提及中国人从加拿大偷渡至美国的情况。1895年她在加拿大报纸《蒙特利尔每日之星》上发表《中国来客》一文,文中写道:中国人为了躲避限制法案想方设法、废寝忘食。为了绕开关税壁垒、穿越基督文明铁丝网,他们有很多现代发明。运送黑人奴隶到加拿大的地下铁路,较之这些发明而言,是小巫见大巫。[5] 三日之后,水仙花又在同一份报纸上详细报道了中国人一行14人,为了避开美国海关,如何在3名偷渡者的带领下,九死一生穿过圣劳伦斯河上的拉欣急流进入美国。水仙花关于华人偷渡的报道让我们窥见了排华时期中国人入境美国的又一方式。当时的华人社区拥有相对完善的偷渡网络。偷渡者前往何处,由谁接应,都有非常具体的安排。尽管手段非法,但还是有不少中国人不顾美国的排华政策与仇华态度陆续前往,其中有不少人遭受羁押,甚至被遣返。
除去非法的跨国移民,华人在美加之间也有合法的流动,这在《洛杉矶永兴的游记》系列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该游记共15篇,于1904年2月至7月在《洛杉矶快报》上连载。水仙花化身为在美国生活了10年的华商永兴,描述了他从洛杉矶出发,经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蒙特利尔、纽约、芝加哥,乘坐火车和轮船横跨美国和加拿大东西部、穿越美加边境的旅行。永兴的游记不仅提供了具体的行程路线,描写了旅途的风光和见闻,而且展现了华人在美加各大城市的生活状态,以及华人与当地人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流网络。通过永兴的游记,我们可以发现华人在北美活动不受国界限制,甚至在墨西哥和牙买加也不乏华人的身影,比如永兴的表哥就曾在牙买加管理农场。
跨国实践不单指跨国移民或跨国人员流动,它还包括跨国的经济、政治等联系。
第一,跨国经济联系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海外华人移民向中国汇款。他们不仅资助家乡的亲人,还支持家乡的教育,并投资建设家乡的经济。《春香夫人》里的春香先生不仅数年如一日地资助弟弟接受教育,而且为其他中国留学生提供帮助。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春香先生还建学校、投资家乡铁路等。在美华人的投资不局限于家乡中国,美洲其他地方也有华人投资者的身影。在文章《中国人在美国:2》中,商人卢石就把所赚的钱投资到墨西哥,成为当地一家铁路公司的大股东。
第二,跨国政治联系在水仙花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水仙花曾撰写过关于梁启超和中国保皇会的文章。1903年梁启超从日本经加拿大赴美,这在北美华人社会中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潮。保皇会乘势在加拿大和美国建立分会。《梁启超和妻子》就是水仙花对梁启超北美之行的报道。文章简要描述了梁启超为革命而被迫流亡的情况及其妻子的奉献与付出,同时提到了在美华人对梁的支持。在另一篇文章《保皇党》中,水仙花介绍了美国保皇党成员的情况,这些成员大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拥有开创精神,在美国各大城市中极具影响力。尽管他们身在美国,却心系祖国,对中国的未来和命运颇为担忧。水仙花所创作的短篇故事中的华商主人公很多都是保皇会成员。在永兴游记之《永兴在纽约》篇中,她还详细介绍了保皇党纽约分会的领导人、组织结构、办公地点以及发行的刊物。
无论是人员的跨国流动,还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跨国联系,都在水仙花的作品中有所描述,显示出水仙花对当时的跨国社会现象甚为敏感和关注。除对跨国实践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书写,水仙花的跨国主义思想还体现在看待问题的立场上,从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认同中可见一斑。
二、水仙花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认同
水仙花是一名纯白人长相的欧亚混血儿,她没到过中国,也不会说中文,但在排华时期却经常出入北美华人社区,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他们辩护、代言,还公开对外声称自己是中国人,以“水仙花”的笔名来发表作品。水仙花这么做并不仅仅因为她身上有一半中国血统,更是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和认同。水仙花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其作品“反映出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有相当的认识,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6] 。此言不虚,纵观水仙花的作品,她不仅客观描写了北美华人的唐人街生活,还饱含深情地描绘了华人的风俗习惯。她自视为北美中国文化的介绍者,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水仙花对中国习俗的介绍和对中国人性格的描写使其作品被冠上“人种志写作”[7] 的标签,但仅从出身对其作品进行评判失之偏颇。水仙花之所以认同中国人,深层次上是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认同。
水仙花喜欢中国经典,其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相关的引用。在《下等女子》一篇中,她借春香夫人之口引用了《诗经·小雅·伐木》。[8]在《宝珠的美国化》中,她借助班婕妤的宫怨诗《怨歌行》来刻画宝珠害怕失去丈夫林福时的心情。[9]
除了诗歌,水仙花对孔孟著作也颇为熟悉。在《阿律》中,主人公裴羽在谈及自己过去对女人的看法时引用了《论语·阳货》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0]一句,译为:“Of all people,girls and servants are most difficult to behave to.”[11]水仙花在谈及中国人自小接受的教育时,引用了《中庸》:“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12]该句译为:“Let a man who is ignorant be fond of using his own judgement;let a man without rank be fond of assuming a directing power to himself;let a man who is living in the present age go back to the ways of antiquity-on the persons of all who act thus calamities will be sure to come.”[13]
水仙花还多次引用《孟子》,在《梁启超和夫人》和《中国学生陈轩仁》中两次引用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14],译为:“The loss of the empire comes through losing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15]在《一位欧亚混血儿的心灵书签》中,水仙花借用《孟子·离娄上》中“是故诚者,天之道也”[16]一句来说明诚信的重要性,该句译为:“The way of sincerity is the way of heaven.”[17]
水仙花在《中国人在美国》一文中描写了一个叫王良的厨子对孟子“劳力者”和“劳心者”关系的反思。王良认为,既然是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那么劳力者就不应该比劳心者低劣。[18]根据学者考证,水仙花引用的孔孟之言大都出自1900年埃皮芬尼亚斯·威尔逊(Epiphanius Wilson)主编的一本中国典籍英文翻译的合集,即《中国文学:〈孔子论语〉、〈孟子名言〉、〈秦始皇〉、〈法显传〉和〈汉宫秋〉》。[19]
水仙花对中国经典的运用信手拈来,是由于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受作为中华文化精髓的儒家哲学的熏陶,因此其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人权和女权问题是贯穿水仙花故事的两大主题,她反对种族歧视、性别压迫、等级制度,主张人性至上,她多次提及“一个人的个性胜于他的国籍”[20]。她的这种观念和中国文化的“人本”思想一脉相承。国学大师钱穆曾说:“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为中心的,主要在求完成一个一个的人。此理想的一个一个的人,配合起来,就成一个理想的社会。”[21]在水仙花看来,种族、阶级、性别、国籍这种文化区隔不能作为评判一个人的依据,人的内在品质与外在德行才是区分高低贵贱的标准。
孔孟所推崇的“仁”对水仙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仁”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指人伦。水仙花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北美华人的各种人伦关系。她笔下的华人男性孝顺父母,一般在中国娶妻生子后再来美国。夫妇之间尽管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但是也不乏相互体贴与关怀,如春香先生和夫人。亲戚朋友之间互助互爱,如《复原之神》中的富商表哥大关洛从小资助贫穷孤儿表弟小关洛,即便小关洛背叛他,他依然不计前嫌地对小关洛施以援手。中国传统社会虽等级森严,但是人与人之间却不乏真情。在《蒙特利尔的女奴》中,森琦夫人和婢女情同姐妹。即便是面对非我族类的白人,中国人也没有偏狭的种族之见,依旧以仁爱待人。在儿童故事《帕特与潘》中,一对中国夫妇在帕特的白人父母去世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养育和照顾帕特的责任。
中国文化中的“仁”对水仙花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她塑造的“君子”型男性人物上。水仙花笔下的男性主人公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大都是谦谦君子,有勇有谋,有学识,有思想。众所周知,君子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有言:“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22]君子的核心人格特征即为“仁”。孟子也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23] 儒家将“仁”排首位,可见“仁”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水仙花笔下最突出的君子形象当数《一个嫁给中国人的白人女子的故事》和《她的中国丈夫》中的刘康喜。刘康喜是一位中国商人,一次回家路上救了被丈夫抛弃、准备投海自尽的白人女子米妮及其孩子。刘康喜把米妮带回家,安顿了她们的生活,米妮最终爱上了他并成了他的妻子。故事中的刘康喜为人温润如玉,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对文学艺术有一定的鉴赏力。他还热衷于政治,是保皇会的成员。相同的君子形象也出现在《华的故事》中。华是读书人之子,却来北美当了一名商人,他思想开明,并不以从商为耻。尽管他来美国的目的是赚钱,但是他不屑于赚取不义之财。他本可以通过从加拿大走私鸦片大发横财,但他拒绝这样做。他说:“我希望我的同胞站起来,而不是倒下。我在保皇会发表演说时提议戒烟。既然如此,我又怎么可以把鸦片放置在他们手上呢?那不是表里不一了?”[24]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言必信,行必果,君子之风也。华裔学者张敬钰曾在《移情的艺术——亚裔美国文学中的仁文男子气概》中谈及亚裔男子气概的一个重要标识是“仁文”,就是儒家尊重的谦谦君子。[25]
水仙花笔下仁义、友善的华人形象,未必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相符。这主要基于她个人对中国文化的美好想象。她笔下那些被美化、修饰的华人角色表明了她对当时美国社会普遍盛行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不满,蕴含了她对理想人格和美好社会的期许。水仙花塑造的这些华人形象,正是出于对中国哲学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和人格的向往。
三、水仙花对情感共同体的追求
水仙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国人的尊重体现了一种情感跨国主义。尽管水仙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与现实中国也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但她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和跨国想象表明了她在情感上认同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可见人类情感可以跨越各种藩篱,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使她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他者。水仙花的这种跨国情感还延伸至加勒比海地区。在相关新闻报道和故事中,加勒比海黑人、混血儿有着和白人相同的喜怒哀乐。水仙花在写作中总是有意突出不同国别、种族、阶级的人们的情感共通性,充分利用共情的写作策略,以对抗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表达出对跨国、跨种族情感共同体的追求。
“情感共同体”是美国学者芭芭拉·罗森韦恩(Barbara H. Rosenwein)在研究中世纪早期情感史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遵从相同的情感表达规范并推崇(或贬低)相同或相关情感的群体。[26]情感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社区、修道院、工厂等社会共同体相同,只不过它更侧重对情感系统的揭示,力图确定这些共同体(以及其中的个人)如何定义、评价有价值或有害的事物;他们推崇、贬低或忽视的情绪;他们所认可的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性质;他们期望、鼓励、容忍和反对的情绪表达方式。[27]水仙花基于人性,描写了受压迫和剥削的有色人种和女性的心理,揭示了他们对种族歧视和父权制的厌恶,倡导人们以同情和爱为核心进行情感联结。
水仙花经常在新闻报道中采用一种“特技新闻”(stunt journalism)的写作策略,即通过乔装打扮、明察暗访等方式揭露不易得到的社会真相,使观众获得关于新闻故事的沉浸式体验。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担任《盖尔每日新闻》记者期间,水仙花在诸多报道中直接用第一人称描述自己对牙买加的印象。她觉得牙买加完全不同于说英语的主流国家,它有自己的个性,是一个重视个性甚于民族性的国家。她描写了金斯顿的赛马、时装舞会以及爱好运动、讲究时尚的人们。比起加拿大、美国,她认为牙买加并不野蛮落后,牙买加与她曾经住过的家以外的地方没有任何差别。[28]采用这种手法写的报道,不仅使读者对所描述的事件和社会有直观的认识,增强报道的可信性,而且展现了水仙花对加勒比海人的理解和同情,引发读者共情。
为了抵抗主流意识形态和实现共情的目的,水仙花在作品中刻画了许多恶作剧人物。恶作剧人物是一种人物原型,他们智慧超群,可以随意变形,无视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恶作剧叙事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多种文化并存的国家很常见,它为受到孤立和迫害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提供了一种发声、获取能见度的方式,也为作者提供一种路径,将针锋相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整合为新的有机体。[29]水仙花就是一位“恶作剧作者”。她将自己化身为笔下的各类边缘人物,有时是出身低微、谋生艰难的白人女性,有时是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身处异域文化的中国妻子,有时是勤劳智慧、受歧视的华人男性,有时是被两种文化排斥的欧亚或黑白混血儿,有时是纯洁无瑕、受成人任意摆布的儿童。这些人物尽管形象各异,但都承载了作者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他们有血有肉,是真真切切的普通人,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隶属于不同的人种、阶级,拥有不同的性别,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拥有共同的人性,尤其在情感上相通。他们虽有着不同的人生际遇,遭遇不同的人生苦难,但都面临人类古老的生存问题以及原始的七情六欲,他们都对主流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在《洛杉矶永兴的游记》中,作者化身为一名华裔男子,把自己多年在美加边境穿梭,往来美国东西部的经历幻化到一个中国男人身上,并把一个中国男人旅行中的所思所想所感呈现在读者面前。中国人也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中国人也懂调侃,也会有愤怒的情绪,中国人的审美能力丝毫不逊于白人。在加勒比海故事《远在牙买加》中,她化身为一位有色人种女性。作品描写了牙买加的混血儿女性和白人女性共同面临的爱情难题。有色人种女性也希望在爱情中被尊重和关爱,在遭遇爱情背叛时也会伤心愤怒,甚至会采取谋害情敌这样的非常手段进行报复。水仙花借助笔下的恶作剧人物反抗种族和性别主义,利用共情解构种族、性别和族裔、阶级等之间的二元对立。美国学者安妮特·怀特-帕克斯(Annette White-Parks)认为水仙花借助恶作剧叙事,使受压迫的人群或个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和政治自治。[30]
除了描写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所拥有的共同情感,水仙花还表达了人类立足情感实现沟通的可能性。为此,她塑造了极富同情心,能够跨越各种藩篱,理解他者的人物形象,如在《甘蔗婴儿》中的白人记者蕾拉·卡罗尔,她基于母亲爱孩子的天性,劝说修道院的修女们把半路抢来的印度婴儿归还给其生母。《新世界的智慧》中的艾达·查尔顿和《宝珠的美国化》中的艾达·雷蒙,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新娘宝琳和宝珠的异域生存经历和父权制家庭生活表示理解和同情。
学者高晓玲在一篇分析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哲学思想的文章中提到了“同情”的作用,她说:“‘同情’,有时可以被理解为同胞感(Fellow Feeling),强调共同的情感体验,以区别于居高临下的怜悯姿态……同情则侧重于主体对他人感受的认同体验,或者说主体之间的情感流通。这种同情经常显现出比冷静和理智更为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是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31]高晓玲所分析的“同情”其实是“共情”的一种更高级形态。尽管“共情”和“同情”经常被交替使用,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共情”是通过体验他人的情感进而对其情绪做出反应,它往往是自发和稍纵即逝的;而“同情”除了对他人情感感同身受,还包含了对他人积极和持久的关注。[32]这种情感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它能产生利他和亲社会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冲突中,它能让对抗的双方从对立冲突转化为理解与尊重。水仙花设想和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以共情和同情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水仙花非常明白情感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她认为,人一旦拥有了感化世俗男女铁石心肠的能力,就可以无视批评和嫉妒者的悠悠之口。[33]她不止一次提到,她自己虽身材弱小,情感却十分强大。她极力倡导共情行为,呼吁人们去感受,运用爱的力量去克服偏见,理解、关爱他者。正是通过情感这一纽带TOWkwZ4NVBVuU/5A0Fh2fjY5Qbl0LpqoxvftPA15Ie4=,水仙花得以明白人性相通,人心相连,世界各族人民命运与共。
四、结语
水仙花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进行跨国实践,这种跨国实践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她不仅描写了中美、美加、南北美之间人员的跨国流动、经济联系以及思想流通,更是对异域特别是中国进行了跨文化的想象,寄托了一种情感跨国主义。这种不断跨越国境边界的经历促使她对地域、种族、性别等文化藩篱所带来的不公进行反思,赋予了她一种超越的视角,令她意识到人性的共通以及人类借助情感实现沟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水仙花是“华裔美国人”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她的华人书写、唐人街故事足以使她名垂北美族裔文学青史。但如果把水仙花的创作局限于对华人族性的书写,就会无法真正理解其思想的深邃与伟大。学者李贵苍认为,水仙花在作品中表达了“世界一家人”的大同社会理想。[34] 从跨国主义视角去解读水仙花的作品,更能说明她是一名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家。
参考文献
[1]Amy Ling.Edith Eaton:Pioneer Chinamerican Writer and Feminist[J].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1983(2):287-298.
[2][3]潘志明.跨国主义[J].外国文学,2020(3):94-109.
[4]李春辉,杨生茂.美洲华侨华人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217.
[5][13][28][33]Mary Champan.Becoming Sui Sin Far:Early Fiction,Journalism,and Travel Writing by Edith Maude Eaton[M].Montreal&Kingsto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16:58,229,104,112.
[6]谭雅伦.“理还乱”:水仙花短篇小说里的美国华人家庭[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4):54-63.
[7]Dominika Ferens.Edith and Winnifred Eaton:Chinatown Missions and Japanese Romances[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2:1.
[8][9][11][15][17][18][20][24]Sui Sin Far.Mrs.Spring Fragrance and Other Writings[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5:30,89-90,217,284,230,237,230,236.
[10][22]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191,83.
[12]礼记[M].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1033.
[14][16][23]孟子译注[M].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171,173,9.
[19]Mary Champan.A“Revolution in Ink”:Sui Sin Far and Chinese Reform Discourse[J].American Quarterly,2008(4):975-1001.
[21]钱穆.中华文化十二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15-16.
[25]King-Kok Cheung.An Empathetic Art:Renwen 仁文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C]//Lydia R.Cooper.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asculinity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22:301-316.
[26]Barbara H.Rosenwein.Emotional Commun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2.
[27]Barbara H.Rosenwein.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 Emotions[J].Passions in Context,2010(1):1-32.
[29]Elizabeth Ammons.Introduction[C]//Elizabeth Ammons,Annette White-Parks.Tricksterism in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4:vii-xiii.
[30]Annette White-Parks.“We Wear the Mask”:Sui Sin Far as One Example of Trickster Authorship[C]//Elizabeth Ammons,Annette White-Parks.Tricksterism in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Hanover: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4:1-20.
[31]高晓玲.“感受就是一种知识!”——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感受”的认知作用[J].外国文学评论,2008(3):5-16.
[32]Douglas Chismar.Empathy and Sympathy:The Important Difference[J].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1988(22):257-266.
[34]李贵苍.书写他处:亚裔北美文学鼻祖水仙花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