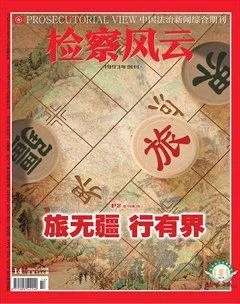数字检察建设的实践检视与完善思路

林竹静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三级高级检察官、法学博士,全国检察调研骨干人才,《世界人工智能法治蓝皮书》(2019―2024)主要撰稿人。
数字检察建设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检察机关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检察工作数字化转型发展,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的重大战略举措。当前数字检察建设中存在的理论痛点与实践难题仍需克服,应通过数字检察理念上的“法治内嵌”,加快推进新时代数字检察建设,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现代化。
数字检察建设的目标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当前,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数字化,检察工作现代化同样需要数字赋能,以数字检察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数字检察建设,即检察工作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是通过顶层设计、系统谋划来搭建一个数字检察的系统架构,从技术、制度和方向上统筹各方力量,通过科技助力新时代检察工作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数字检察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数字检察建设中的理论痛点
一是算法黑箱与司法透明的抵牾。算法黑箱是指一些算法在运行过程中,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其内部机制和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由于数据的维度和大小不断增加,黑箱算法的数量和复杂度也在不断增加。在数字检察中,司法透明性要求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公开其作出司法决策的依据和标准,在保证办案结果公正透明的同时,让公众了解和监督检察机关的工作,保障法律的公信力和人民的知情权。
二是“信息茧房”与全面客观公正的矛盾。“信息茧房”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由于自身获取信息的渠道受限,难以获取或接触到客观、全面、真实的信息的情况。在数字化时代,不同信息平台和社交媒体通过计算机算法与推荐系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可能导致信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信息茧房”现象。全面客观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司法决策和判断应建立在全面、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上。在数字检察中,由于存在“信息茧房”,算法推送给办案检察官的信息可能是片面的,这可能导致办案检察官难以获取与案件相关的全部证据和法律事实。
三是强计算主义与司法经验主义的冲突。强计算主义强调运用计算机、数据和算法等科技手段自动化地处理和分析数据,以此得出准确、客观、科学的结论和决策。司法经验主义则强调检察官和法官的实践经验及直觉判断,强调对案件的全面考虑,包括证据、法律规定、社会背景、人性因素等各个方面。这两种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往往会带来冲突:强计算主义可能会忽略案件背后的人性和社会背景,其仅仅依靠数据和算法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和客观;而司法经验主义则可能会受到自身经验的局限。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合理的平衡,才能得到更好的司法决策结果。
数字检察建设中的实践难题
一是业务办案尚未实现全面数字化。从实践来看,目前大部分检察办案行为仍然在线下进行,办案行为的整体数字化率依然偏低,没有实现全面数字化。从释放数据红利角度而言,目前文书制作、审批流转等办案行为在线上进行,而告知、讯问、送达、听取意见等高频办案行为都在线下进行,整体办案行为的不连贯性导致检察业务数据出现了断层、碎片化问题,不利于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应用。
二是数据互联共享程度有待提高。数字化时代需要较高水平的数据协作和共享,但在数据共享上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单位间的数据壁垒仍然存在。特别是与法律监督相关的数据,部分单位还存在不愿意向检察机关提供的现象。从检察机关内部来看,表现为数据整合利用率偏低。对数据的管理缺乏成体系的专门机构及专业人员进行标准制定和规范要求,缺乏相应的完整工作流程及工作机制,尚未在业务部门与案件管理部门之间形成完整、积极的双向互动。
三是法律监督的大数据赋能尚有不足。对于数据的利用能力:一方面受到数据条件的限制,内部数据不佳、外部数据缺乏使得数据挖掘的效度有限,算法学习收敛困难;另一方面,缺乏对应用场景的设计,在数据分析、挖掘中仍拘泥于小数据,使得相关工作对数据质量的依赖更大。数据的应用闭环没有形成,较少使用反馈学习,使得数字智能化的发展较慢。
新时代数字检察发展的完善路径
一是完成数字检察理念的“法治内嵌”。数字检察的发展需要依赖于法治理念的内在支撑,如何将法治理念内嵌于检察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将数字技术与法治理念、检察实践有机协调,是解决数字技术在检察应用中理论痛点的关键。首先,可通过“法治内嵌”破除数字检察背景下算法黑箱与司法透明的抵牾。检察机关可通过规定算法运行过程中的必备要求,如监督机制、鉴定、证明等,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监管,建立数字化时代的办案标准和规范。其次,可通过“法治内嵌”克服数字检察背景下“信息茧房”与“全面、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之间的矛盾。数字化带来的“信息茧房”与“全面、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之间的矛盾主要源于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和信息筛选算法的存在。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法治内嵌的框架下,通过加强法律规范和信息管理制度建设,强化对信息来源可靠性和真实性的把控,有效规范信息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和使用行为,防止信息滥用、泄露和篡改等问题。最后,“法治内嵌”可以在数字化时代弥合强计算主义与司法经验主义的冲突,建立更完善的数字检察理论框架。“法治内嵌”将法律制度、司法规范与法治价值观嵌入数字化的检察办案过程,依托信息技术实现对“办案数据”与“数字办案”的法治化监管,进而有效避免强计算主义的机械化和泛化问题。
二是明确新时代数字检察发展的具体路径。首先,形成数字检察的基本生态和基础环境。系统梳理“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全部办案流程和各个业务流程中的全部办案行为,创建“高效办成一件事”模式——从讯问、询问、听取意见等高频办案行为入手实现数字化,逐步延伸至全量办案行为,最终实现“线下办案行为全面线上化、检察业务全面数字化”。其次,探索数字检察办案新模式。数字检察为法律监督模式变革提供了可能。例如,创新以类案监督为主的新型办案模式中,可综合运用大数据思维和侦查思维,把对典型个案的监督规则梳理、提取、转化为数据模型,通过内外部数据的碰撞筛查发现异常数据,进而形成高质量的监督线索,促进社会治理深层次问题解决,落实“往前想,抓前端,治未病”的能动司法。最后,提前研究布局“数字全息”时代法律监督。未来基于数字化的应用类型丰富、参与主体多元、数据权益诉求各异,势必造成数据治理体系建立与数据治理权责划分更为复杂。检察机关应提前布局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发展可能涉及的司法办案与社会治理问题,立足检察职能提升数字治理能力,推动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