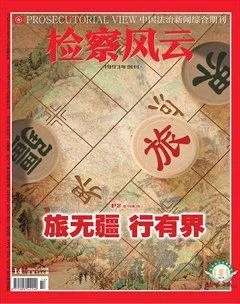1923年浙江一师投毒迷案

突发惨案
这是一起发生在1923年3月10日晚上,震惊浙江全省的特大命案。造成这一惨烈命案的犯罪手段是投毒(砒霜)。命案发生地点,是彼时已有“开风气之先”声誉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一师”)。这起惨案共夺走二十四条鲜活的生命,受伤者不下二百人。案发是在当天晚上,浙一师学生和教职员工晚餐时间。
这天晚上,浙一师住校学生像平时一样,到了晚餐时间,纷纷拿上自己的碗筷走出宿舍,和其他教职员工一起来到学校食堂用餐。然而,这顿晚饭,竟成为其中二十二名年轻学生、两名校工一生中最后的晚餐。这些中毒者有的是回到宿舍后发作;有的倒在离开食堂的路上;有的因餐后待在食堂与人叙聊,不久即直接倒下……
投毒案发生当晚,浙一师二百多名中毒者都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尤其是杭州市的医院,还派医生进驻学校,通宵观察后续情况。但即使大家再争分夺秒,经医院两天两夜奋力抢救,最后还是不幸有二十四人因中毒太深而死亡。当时的浙一师校长何炳松曾感慨道:“其余(学生、教职员工)均因本省军民长官、各界人士,奔走营救之故,得庆更生。”这就是说,如果不是社会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及时伸出援手帮助浙一师,死亡的人数也许还会更多。据查,惨案发生时,何炳松正在外面开会,闻讯后火速赶回;迅即组织抢救,四处奔波求援。
不言而喻,惨案发生,责无旁贷、最先担责者必定是校长。所以,何炳松后来回忆此事时,仍心有余悸地说,投毒案发生后,“不佞身任该校校长,朝夕奔走,寝食不安。物质精神,两受痛苦,事后回想,恍若经过一场噩梦”。尤其是在案情侦破前,人们难免会对投毒案的发生做种种猜测,有人甚至怀疑作案者下手如此狠毒,是否与何校长有什么怨仇,系冲他而来。然而,更多知道、哪怕是接触过何校长的人,则又绝不相信凶手如此丧尽天良,会是冲着受到大家尊敬和爱戴的何校长而来。由于这起投毒案毕竟与何校长有瓜葛,所以我们且先从他说起。
何炳松其人
何炳松,字柏丞,1890年生人,浙江金华人。1912年官派留学美国。1917年学成回国后,先在浙江省政府任职,很快受北大校长蔡元培所聘动身北上,尔后在北京多所高校担任教职。浙一师投毒案发生时,他刚到浙江担任浙一师校长半年。那是1922年8月,原浙一师校长马叙伦调任他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夏敬观遂聘请何炳松继任。浙一师在当时不仅以开风气之先,也是以教育质量高、进步而闻名全国,其教师阵容更堪称强大。沈钧儒、经亨颐、马叙伦、李叔同、鲁迅、叶圣陶、刘大白、俞平伯等都先后在该校任教。学校生气勃勃,学生自治会等学生社团十分活跃。何炳松上任后,继承了浙一师许多优良传统,包括支持学生自治会的活动等。投毒案发生后,有人归咎于学生自治会,认为这是学生管理食堂的结果,并且要提倡学生自治的前校长经亨颐承担责任。何炳松对此持反对意见,更不同意归罪于学生自治会。后来他更是多次递交辞呈,愿责己以谢天下。
浙一师学生热爱何校长,当然不愿意何校长离开他们。他们在所发布的《全体学生宣言书》中说,“近来外界人士,疑窦莫释,有咎何校长不知先事预防者,毋乃苛刻之至”。随即,又推举代表,到省教育厅请愿,发布《全体学生请愿书》,挽留何校长。在学生们和教育界的挽留下,何炳松这才继续在浙一师及改名后的省立第一中学,当了一年多时间的校长。但他最后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于1924年辞职,应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与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
1929年,何炳松开始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工作,先后编印出版了《万有文库》第一、第二集,《四部丛刊》续篇,《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所以,何炳松除了是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还是知名的出版家。当然,他最擅长的是西洋史研究,堪称学贯中西;也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的发小和挚友金兆梓在《何炳松传》一文中写道:“(何炳松)君性果遂而勇于负责,颇为觖望者所轧轹”;又说:“(何炳松)君为人宁静冲邈,平居绝不见疾言厉色,而处事则当机立断;故虽薄书旁午而案无留牍,猝遇大事亦一神不惊,措置裕如而事无不治。君性似冷,而实富于热情,视亲友如弟兄,遇青年如子弟;人有善不能忘,有不善则澹焉而卒忘之,不念旧恶,不修旧怨;故虽有甚不慊于君者久亦潜消其不慊而自亲于君。”这些文字足以表明,何炳松既是一位处事果断、勇于担责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待人热情、热爱青年,好与人相处的智者。对于前者,我们在浙一师投毒案发生后,他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已见识到了;至于后者,则可从他反对追责学生自治会这一保护青年学生的行为中得以体现。
但有着浓浓学者情结的何炳松,到底还是不甘长期担任校长之职,他更希望自己的工作,多少能与学术沾边。事实上,在浙一师投毒案发生前,他心下已萌生去意。他后来在回顾这起投毒案时,曾这样写道:“毒案与校长去留无关。惟此次毒案,虽属暗箭伤人,无法防止。然为校长者,职责所在,咎无可辞。社会各方面纵加谅解,而不佞则始终抱春秋责备贤者之义,屡请辞职,非客气也。惟不佞对于一师校长一席,自思去就尚属光明。”
至于坊间纷传的各种谣言,何炳松则这样告知大家:“吾国人喜造谣言,喜作诛心之论。求能平心静气,就事论事者,其数盖寡。故一师毒案发生之后,谣言风起。有谓为政客所利用者,有谓为有人与不佞为难者。五花八门,不可究诘。不佞以为此种毒案,固甚离奇,然谓其与政治或校长位置有关,则实百思不得其解。一师与政治无关系,且年来一师学生,颇能力学向上,不甚与闻外事。至于欲排斥不佞于一师之外,则真可谓易如反掌。不佞本非热衷于校长一席者,不佞非有不得已苦衷,必欲恋栈不去者。世界上又焉有此种下愚之人,下此种毒手以达其驱逐校长之目的乎?故不佞以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吾人正当平心静气,就事实上推敲之,捕风捉影之谈,大可不必也。”除此之外,何校长对当局也表示了由衷地感谢。他说:“除医生外,当推本省各军民长官。督办省长,均蒙亲身莅校,无事不帮忙。不佞人微力薄,遭此巨艰,若无贤长官之援助,真唯有坐以待毙而已。”他还特地提到了当时的警务处处长夏超和教育厅厅长张宗祥,说他俩几乎每天都会抽空来学校,询问有什么事可以帮上忙。这也让何校长心里充满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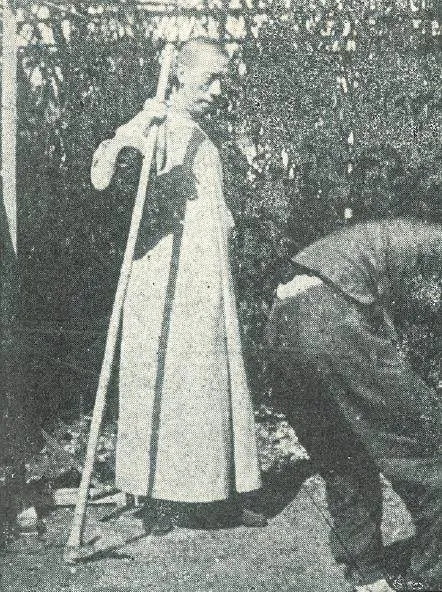

引发何炳松感慨和他想要感谢的,当然远不止这些。比如对媒体,他同样心存感念,其舆论的导向已越来越被当时的大众所认识。事实也确实如此,舆论稍有带偏,处在漩涡中的当事人别说百口莫辩,即使想辩,也是越辩在泥淖中陷得越深,甚至难以自拔。所以,何炳松当时很感谢在浙一师投毒案发生后,杭州和上海两地记者的马上跟进,及时报道真实消息——既避免了谣言纷传,引发了全社会对死伤者的同情;同时,还激起了人们对投毒者的狠狠谴责。诚如何炳松当时一语道出的,“盖此种惨无人道之毒手,绝非有人心者所忍为”。
破案后的种种疑点
很显然,浙一师投毒案发生后,人们最关注的,自然当数侦破工作了。作为涉事学校的校长,何炳松更是“深望司法官厅对于此案,不求速效,毋枉毋纵”。这应该也是他所担心的——司法机关不要因为急于平息舆情,而出现错抓错判的现象。
投毒案发生后,浙一师就像一座钟,停摆了两个星期,直到二十四日才恢复上课。毕竟不能因为投毒案未告侦破,影响学生正常上课。
又过一星期,学校为二十四位不幸遇难者举行了追悼会。当天的《新浙江报》为这场追悼会出版特刊,以表哀思。
这起浙一师投毒案,最后被杭州警方与司法机关认定宣告侦破。但据何炳松友人之子阮毅成在《记何炳松先生》一文中披露,这所谓侦破后面,显然还有种种疑点。“民间则认为并没有达到何先生所希望的:‘不求速效,毋枉毋纵。讯研不厌求祥,而证据切须确凿。’警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所认定的主犯,系一师在校学生俞尔衡;教唆犯系一师毕业学生、在省教育厅任事的俞章法。他们同是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人,且是堂房的叔侄。俞尔衡被判处死刑,执行绞决。俞章法原被判处无期徒刑,因越狱再次被捕,被改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除此之外,阮毅成还在文章中披露出了更多相关信息。如他写道:“另尚有在一师厨房担任淘米与烧饭的两名工友——毕和尚与钱阿利,警察机关认为他们从俞尔衡手中接到大量砒霜,放在饭锅中。但因为在侦讯时用刑过重,未待判决,二人已死在看守所中。故一师毒案除当时死学生二十二人,工友二人外,又死了四人,总共死了二十八人。另尚有一部分中毒学生,虽经急救得活,但因中毒已深,脑神经或心胃受到严重的损害,成为残废。”由此可见,所谓罪犯并没有留下口供。这里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侦讯时用刑过重”——这分明就有严刑逼供之嫌。不仅“用刑”,而且“过重”,最终导致受刑者死于狱中。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获得所谓供词,又怎么能不令人生疑。难怪阮毅成还在文章中一语中的地指出:“民间对司法机关所公布的证据,至感怀疑。因无论如何,一个毕业学生与一个在校学生,绝没有必须毒死全校师生的理由,而且大量砒霜的来源不明,不能使人折服。所以咸认为一师毒案是一件冤狱(案),也是一件疑狱(案)。”
还有更让外界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就在此案判决后不久,承办该案的浙江高等审判处刑庭处一名熊姓处长,竟毫无征兆地在其新市场龙翔里寓所中暴毙。认识熊处长的人都说,他正值壮年,身体很健康,平时从没听他说起过自己有什么头疼脑热,或身上有什么地方不舒服。而另一位我们前面曾经提及的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也是很意外地突然遭到逮捕,且很快被军阀孙传芳下令斩首。民间因此更是纷传,说浙一师投毒案之所以成为冤案,均与这些人有关。
浙一师投毒案事发五年多后,当时正在巴黎的阮毅成偶遇何炳松的同乡吴敬生。两人不经意间谈及五年多前那起震动全省的浙一师投毒案,吴敬生很肯定地告诉阮毅成,其中真相“只有何先生知道。但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所限,所以何先生不能宣布”。
就因为在巴黎听了吴敬生这句模棱两可的话,阮毅成一直耿耿于怀。所以,当他在1931年元旦过后回到国内,就想着一定要找机会,“当面向何先生问清楚”。只是由于两人当时并不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和生活,所以阮毅成竟足足等了六年,直到1937年4月,浙江省教育厅在绍兴县(现为绍兴市)举行中等教育研究会年会,邀请二人到会作专题演讲,阮毅成这才终于见到了何炳松,并在会后向其问出憋了许久的那个疑问。
然而何炳松给他的回答却是:并不知道那起投毒案的真相。
其实存有此疑问的,并不仅仅只是阮毅成,房鑫亮在《何炳松评传》一文中也写道:“一师毒案虽经侦讯,以处决主犯而结案,但当时就有人疑为‘疑狱、冤狱’,亦有人谓唯何炳松知道内幕,只因环境而缄口。这种说法虽然被何炳松否认,但从他为死难者所作祭文‘早知如此你们不应该欢迎我来,我亦早早应该冲破你们感情的束缚,或许不会发生这种凄惨的事情’看,似有隐衷。他的挚友金兆梓曾说,他在一师校长任内‘勇于负责,颇为觖望者所轧轹’,可为佐证。”
如今,这起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惨案,虽说已成为迷案,但当年何炳松为此发出的一些提醒和告诫,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有其警世意义。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