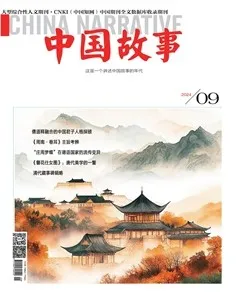君特·艾希对《列子》“役夫梦”故事的多维阐释与创构
【导读】道家典籍《列子》寓道于事,兼备哲学思想与文学价值,其中诸多故事在德语国家的流变不仅助推道家思想传播,亦丰富了德语文学表达。而德国作家君特·艾希据《列子》“役夫梦”改写的广播剧《奥马和奥马》尤为独特,在凝聚体现道家哲学思想中相对性原则和梦幻哲学观的同时,运用广播剧这一体裁进行本土化重构与演绎,使“役夫梦”在德语世界转换新生。
【关键词】《列子》;役夫梦;君特·艾希;《奥马和奥马》
“役夫梦”故事源自《列子·周穆王》。作为对“梦”进行集中论述和分析的典籍之一,《列子》是中国古代梦哲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重要对象。在代代传抄演绎过程中,德国传教士和汉学家也不时为《列子》蕴含的精神所吸引,推介其进入德语世界,对德语文学产生影响。经卫茂平教授考证,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艾希(Günter Eich),就曾受到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列子》德译本启发,于1957年改编“役夫梦”,创作广播剧《奥马和奥马》(Omar und Omar)。有鉴于此,本文首先耙梳了《列子》在德国的译介史,并以此为基探析君特·艾希对《列子》“役夫梦”故事的多维书写。
一、《列子》德语译介史述
中国道家经典《列子》在德国的传播历程已逾百年,从目前已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可视为系统翻译和诠释《列子》思想内容的西方第一人。他于1877年出版著述《古代中国泛神论和感觉论自然主义或哲学家列子著作译释》(Der Naturalismus bei den alten Chinesen oder die sämtlichen Werke des Philosophen Licius: übersetzt und erklärt),首次将《列子》介绍到德国。在他看来,列子有关“神”“自然”和“天堂”等方面的论述与基督教观点有许多契合之处,其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具有深远的思想根基,推动其教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同样以传教士身份来到德国的卫礼贤在协助花之安布道时,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研究兴趣,自觉服膺和传播中国文化到欧洲,并评价花之安《列子》译本“未有节删,但是艰涩难读,称不上是标准德文翻译”,故于1911年在青岛重译出版《列子冲虚真经》(Liä Dsï, das wahre Buch vom quellenden Urgrund),收录于迪德里希斯出版社(Eugen Diederichs)十卷本丛书“中国的宗教和哲学”(Die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Chinas)。卫礼贤译本没有明显传教倾向性,但其译文仍未脱离宗教文化的影响。此外,该译本创造性运用康德哲学概念作为文章标题,力图佐证中西哲学思想的互通之处。
此后,《列子》译介经历近百年沉寂,直至新世纪以后,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受赫尔德出版社(Verlag Herder)邀约,为摆脱和纠正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列子研究的忽视和偏见,于2017年重新翻译出版《列子:论御风而行之术》(Lie Zi: Von der Kunst, auf dem Wind zu reiten),收录在十卷本“中国古代思想经典”(Klassiker des chinesischen Denkens)中。作为面向大学师生的普及读物,该丛书仅择取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中最重要的思想予以翻译和注释。这些注释代表着顾彬在当代视角下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观照。尽管顾彬认为花之安与卫礼贤对《列子》的理解无误且深刻,但他也在译文导言中指出其译本受到批评的原因,即二者作为传教士在很大程度上以基督教为据作出阐释,缺乏客观性。综而观之,《列子》译者群体展现出以传教士和汉学家为主的特征,而其译介动因与阐释则随着时代变迁呈现去宗教化趋势。
二、君特·艾希的改编剧《奥马和奥马》
《列子》在德语世界的流播除了传教士与汉学家辛勤译述,也不乏文学家从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德国作家君特·艾希曾在20世纪20年代有汉学学习经历,其许多作品含有明显中国文化元素,例如广播剧《梦》(Träume)、《笑姑娘》(Das lachende Mädchen)等。《奥马和奥马》是艾希除《别去埃尔库维德》(Geh nicht nach El Kuwehd)和《真主有一百个名字》(Allah hat hundert Namen)之外的第三部“东方”广播剧。彼时的东方地域对欧洲来说奇幻而神秘,对欧洲知识分子有着强烈吸引力,艾希作为其中一员同样着迷于东方文化,并将中国与之联系在一起。
(一)《奥马和奥马》的文本多维接受与重构
“役夫梦”篇幅短小,仅有239字,主要围绕老役夫和周朝财主尹氏的梦展开。老役夫在尹氏手下日日劳顿,精神恍惚之下夜夜梦为国君。而大财主尹氏累于产业,夜夜梦作奴仆。最终尹氏听从友人相劝减轻仆役劳作强度和俗事困扰后,梦魇才得以纾解。而艾希的广播剧《奥马和奥马》除吸纳该故事核心主题和情节外,主要从情节内容、人物形象、哲学思想三重维度对“役夫梦”进行阐释和改写。
首先在情节上,广播剧共有十三场。艾希将故事发生地点分别设置在巴格达和中国沿海的哈纳德港。其中有两位同名主人公:富裕的哈里发奥马和贫穷的搬运工奥马,关于二者的故事交替叙述。哈里发首先出场,他如原作尹氏一般,拥有数不清的仆人与财产,却总做化身苦力的噩梦。而搬运工生活拮据,在夜间时常梦及自己成为哈里发。剧中相比“役夫梦”原篇,扩写许多全新情节,例如搬运工醒后讲述梦中判案的始末、两个奥马在巴士拉相遇并交换身份等,都使得新作剧情变化较原著更为丰富。
在人物塑造方面,艾希不仅增添大臣、奴隶、王公贵族等配角,还新增“妻子”角色对比。哈里发有365个妻子,仍旧深感孤独,他甚至“还没见到她们中大多数”,搬运工只有萨姆莎一位妻子,却夫妻恩爱,抚育六个孩子。此外,原著中尹氏仅以财主做派示人,在友人婉劝下才悟出噩梦之因,角色扁平化且缺乏主观能动性。而哈里发却是艾希心中极度理想化的统治者与完人,并被设计成一个有自觉反思意识的国君形象。哈里发在经历梦中搬运苦累后,心态发生变化。作为一国之君,他能够推己及人,主动提出改善搬运工生存状况,甘愿放弃王位和荣华,踏上去往梦中遥远东方——中国的旅程。而搬运工知足常乐,孩子们崇拜其梦中的哈里发形象,他却依旧不矜不伐。在他戴着象征王权的戒指初到巴格达时,大臣们心生短暂质疑与嘲弄,但不多久便折服于搬运工的执政智慧与宽广胸襟,承认其为国君。艾希由此对两个奥马的形象予以重塑,使之较于原著中的尹氏和役夫角色更加多维立体。
从哲学思想角度看,广播剧中两位奥马身份互换的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道家经典学说《道德经》中的表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列子》作为道家经典之一,承袭和揄扬《道德经》诸多哲思精粹。如同有无、难易和祸福可以相互转化,“役夫梦”中苦乐、贫富也相对而生:尹氏现实生活无忧,梦中就为生计奔波,役夫生活中受人差使,梦里就施命发号,正如尹氏之友所言:“苦逸之复,数之常也。”此外,剧中两位主人公相识于第七场,恰为剧场总数二分之一处,同样映射出艾希对道家相对原则的推崇,进而借此宣扬“得失相等、贫富齐一的道家思想”。
(二)跨媒介叙事中的“役夫梦”
除内容层面的接受与改写,君特·艾希亦在艺术形式上展开创造性改编,借助广播剧体裁展现他对“役夫梦”故事的化用和阐释。广播剧以人物语言、音乐和声响三部分结合为主要艺术特点,通过人物声音远近搭配、不同音响乐器高低起伏,搭建起完整的叙事空间,“进而激发听众产生巨大的想象空间,引发听众深入思考故事的内涵”。在丰富听众审美和情感体验同时,能够刺激其探索作品意旨的好奇欲。而广播剧在德国文学史上亦具有重要意义,德国纳粹政权在二战时将广播剧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这一定位间接促进广播行业持续发展,也为战后广播剧繁荣创造前提。对于处于战后废墟瓦砾、精神世界荒芜的德国民众而言,广播剧可谓填补空白文化生活的重要来源。论及艾希改编“役夫梦”的动机与目的,一方面在于这则故事情节主题简单,寓意明确却能够引人深思,适宜被改作广播剧形式播放,另一方面,艾希深切关怀社会现实,对故事中苦乐转化的思想内核适时征引,一定程度上意在为饱受战后创伤记忆折磨的德国民众指引一条解脱心灵痛苦的东方“道”路。
在《奥马和奥马》中,广播剧的音乐强度和乐器种类呈主题式分布:铜管乐为哈里发奥马的主题乐,搬运工奥马则以弦乐为主,两种乐器交互演奏。弦乐器依靠机械力量使张紧的弦线振动发音,独奏时声音柔美、婉约,而铜管乐器前身大多是军号和狩猎时用的号角,音色雄壮、热烈。这两种迥异乐器恰恰代表两个奥马不同身份和性格特征,哈里发作为君主地位显赫,对待臣仆厉声呵斥,而搬运工生活拮据却不卑不亢,面对妻子呵责也能面带笑容,柔声以待。这一声乐层面的处理将两位奥马形象塑造得更加鲜明和真实可感。
(三)《列子》梦幻哲学观对艾希改写风格的影响
不同于西方人普遍认为梦是泡影的看法,君特·艾希笔下的梦通常具有某种真实性,是人在白昼所思所历的具体表征。这种创作倾向或与其吸纳道家学说关于梦的阐释相关联。
《列子·周穆王》通篇都是对梦问题作出的诠释:在梦与觉的界定上,列子将其理解为“神遇为梦,形接为事”。精神层面接触为梦,形体接触为觉,但同时他也肯定梦与白天思虑和经历有关。在“役夫梦”中,梦的内容受到觉的干预,而觉又影响着梦,梦与觉以十分紧密的方式相互联系。役夫借梦宽慰白日劳累,以神遇之梦解形接之苦,而尹氏通过改变觉,减少思虑之事,缓解梦中之苦。在此意义上,梦与觉的分别变得扑朔迷离。列子以梦隐喻人生,在不辨梦与真实的前提下,将人生“尽幻化”,于是梦中苦乐便如同清醒时一般真实可感。
艾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淆乱梦与不梦的边际,夸大梦的真实性,甚至打通梦与现实的巨大隔阂,让哈里发醒来后身上出现梦里劳累所致的“结痂的伤痕”,并在枕下找出梦中所赚的“一百零八个第纳尔”。此外,原著中尹氏财主身份到了艾希笔下被索性改为役夫所梦的人君形象,哈里发与搬运工在梦中互相过着对方的生活,二者的现实和梦形成镜像般翻转。在广播剧末尾,艾希甚至让两个奥马身份成功互换,哈里发奥马如愿去往中国,做了码头搬运工,穷人奥马则高兴地到了巴格达,成为哈里发。这一结局同原著中贫归贫、富归富的结局相比可谓截然不同,由此将梦完全化为现实,彻底模糊梦与真实界限,充分体现不分梦醒、将人生“尽幻化”的梦幻哲学观以及“人生如梦、梦即人生”的道家思想。
此外,艾希在创作中融合德语文学的“双影人”概念与道家梦幻哲学观。“双影人”形成首先“建立在两个人物身体相似性的基础上”,而故事中的哈里发和搬运工名字均为奥马,年龄都是30岁,显然由作者刻意为之,海因茨·施维茨克(Heinz Schwitzke)也将二人看作彼此的“夜间反面形象(nächtliches Gegenbild)”,身体上的相似特征为他们现实中身份转换提供了暗示。值得注意的是,广播剧中关于主题音乐的描述也足见艾希对道家梦幻哲学观的强化,他强调第九场前音乐“应该是遥远而不真实的”。这场以搬运工妻子与孩子对话为主要内容,孩子们在担忧失踪父亲同时亦对父亲的梦念念不忘,其中两个孩子甚至还分别梦到远在巴格达已然成为哈里发的父亲和正在驶向哈纳德船上的“父亲”。殊不知,他们所梦亦为现实所发生,艾希在此却又用音乐暗示其乃“不真实”,就此将梦与现实再次混淆在一起。究其深意,作为四七社成员之一,艾希将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暗含于广播剧《奥马与奥马》之中,在寄予美好理想的同时,流露出对战后社会改革的无力之感。
三、结语
君特·艾希的广播剧《奥马和奥马》虽取材于道家经典《列子》中的“役夫梦”,但并未全盘照搬这一故事,而是从情节编排、人物塑造、哲学思想三个层面对原著进行程度各异的改写与创新。此外,艾希还借用广播剧这一跨媒介叙事形式,融通《列子》中蕴含的梦幻哲学观对当下社会予以观照,借以表达对战后德国进行理想社会改革的诉求。
参考文献
[1] 范大灿,李昌珂. 德国文学史(第5卷)[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 李雪涛. 与顾彬对谈翻译与汉学研究 [J]. 中国翻译,2014(02):52-60.
[3] 列子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孙立新. 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J]. 史学月刊,2003(02):45-54.
[5] 田源,等. 广播剧:声音的艺术 [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2.
[6] 王弼注,楼宇烈.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7] 卫茂平. 君特·艾希与中国:君特·艾希作品与中国精神界关系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8] 卫茂平. 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9] 张东书. 两个世界之间的文化桥梁——卫礼贤和迪德里希斯出版社 [J]. 国际汉学,2010(02),114-128.
[10] 魏义霞.《列子》梦幻哲学释义 [J]. 延边大学学报,2012(06):23-30.
[11] 吴沐潇. 基于多维视域下的音乐艺术与器乐鉴赏研究[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1.
[12] Eich, Günter. Omar und Omar, hg. v. Karl Karst, Günter Eich. Die Hörspiele 2 [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1.
[13] Frenzel, Elisabeth. Motive der Weltliteratur [M].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2008.
[14] Kubin, Wolfgang (Hrsg.). Lie Zi. Von der Kunst, auf dem Wind zu reiten [M]. Freiburg: Verlag Herder, 2017.
[15] Schwitzke, Heinz (Hrsg.). Reclams Hörspielführer [M]. Stuttgart: Reclam-Verlag, 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