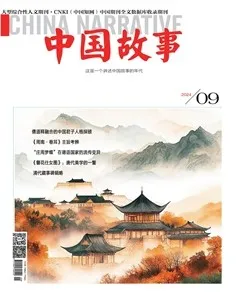从“卦兆皆反缪”再探《轮台诏》
【导读】汉武帝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轮台诏》,检讨晚年对匈奴战事之过失,痛言“朕之不明”“今计谋卦兆皆反缪”,与战前战中多方卜筮者“皆以为吉”的结论截然相反。《史记》与《汉书》对此一系列史事的记载总体上一致,细节处偶有不同,二者都有意醒喻武帝晚年政治行为,体现了史官一脉相承的史学传统和历史责任感。
历来有关汉武帝战略政策及《轮台诏》的研究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以来,田余庆先生对武帝之“政治转向”作了总括性的积极评价,辛德勇先生则提出质疑,指出司马光对营造“汉武帝”积极形象的史料有所择取、有意加工,足见其从史学理论角度审视和运用史料的意识;其后有赵永磊、陈金霞、杨勇等学者着重在“知人论世”的史学史视角基础上,对司马迁及历代史家和政治人物的观点作分析,推进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研究;刘哲、王锐等学者则通过梳理学术史上的既有成果,对近现代以来相关学术观点所反映的史学思想作了考察和反思,具有理论层面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从“卦兆皆反缪”和“皆以为吉”之强烈反差入手,试以此进一步探微。
一
匈奴是西汉最大的对手,军事实力强悍,与其他诸胡“连兵为寇”袭扰汉地。汉自立国以来长年征劳,百废待兴,国力空虚,无以为战,只能守边防御以避战。匈奴还在致文帝的国书中自称“天所立……”“天地所生、日月所置”这样“受命于天”式的尊号,挑战皇帝的统治权威。
汉武帝对攻打匈奴的战事十分重视,难免托于天意。当时巫卜盛行,“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轮台诏》中更明言:“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匈奴亦信仰巫卜,除了《史记》中多次出现的“胡巫”事迹,还有单于遗天子马裘、缚马等诅军事之举。为何胡巫的卜筮符合战争结果,汉朝却“今计谋卦兆皆反缪”?
二
在以李广利为主将攻打匈奴的战争中,“卦兆皆反缪”应在两人身上:一是李陵,相者望气见其家眷“无死丧色”之兆。二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多方卜蓍皆称“贰师最吉”之卦。
(一)李陵之降
李陵是匈奴惧怕的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后。“李广难封”,将门光环落在李陵身上,武帝安排他屯守边塞,长期配有精良装备和辎重补给,颇有当作“第二个霍去病”培养之意,但仅“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李陵鲜能亲至前线,久无用武之地,直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叩头自请,愿得自当一队,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武帝安排李陵为李广利之“后军”押送辎重,或许反映了武帝对这支精兵的爱惜之心,但毕竟远离前线、难以立功扬名,可想而知李陵“叩头自请”时所想,武帝也有意检验这支精兵,欣然应许。
老将路博德“羞为陵后距”,暗中上书诡言,“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即便李陵带着亲训士兵“横挑强胡”,交出一份优秀“答卷”,但书奏之后他也不得不遵照路博德的指挥,还“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才得以在武帝心目中恢复了好印象。而后匈奴大军围攻主将李广利,万分危急,汉朝派李陵步卒长途跋涉去助军解围,但力尽粮绝,被匈奴单于亲率主力围困。武帝召来相者望气,说从李陵母与妻身上没有看出死丧之兆。在李广利、公孙敖两位将领所率大军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李陵部仅五千步兵就杀伤万余人,出色完成了任务。李陵最好的结果是生还回朝以壮汉军威气,但他没有生还,也未死战,而是投降。汉武帝的投入和期望皆毁于一旦,食不知味,郁郁不欢,极度失望和懊恼。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群臣对李陵的责骂基本是次要的道德评价,武帝作为君王则看重历史评价(类比于后来苏武出使匈奴时,单于派卫律劝降,苏武骂道:“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背主衅亲,为降虏于蛮夷”,即可知李陵之降在武帝看来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董仲舒改造儒学,吸收阴阳家天命谶纬之说,加之公羊派“《春秋》之义,原心定罪”理念,提出天子对臣子“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拥有定性的至高解释权、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李陵之妻并“无死丧色”,说明天不亡他,而他却违背天道、忤逆圣意,实有损天子威权。司马迁受武ROc6eHfHEC6ScNCFQGJeTlmAABHY8PJIuX8nSidwFB4=帝召时,以为武帝会综合道德层面与历史层面的考虑,给有功之臣留一条活路,让降将、逃人们还能有心重新归汉、继续效力,便“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但在武帝看来,司马迁一介太史,竟然僭越权柄,妄揣圣心,故严重治罪。
武帝专遣李广利为主将,扶持升擢之意十分显见,《史记》未提,但《汉书》直言不讳“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李陵的功勋注定要被李广利“压一头”,但在战略调动中将领们互相争功,极难配合,致使李陵落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后来武帝“悔陵无救”,两次派军去迎,最有成功可能的首次营救,带队将领却是怀有私意的路博德,最终李陵再未归汉。《汉书》中记路博德“生奸诈”,或正是武帝事后对其“圣裁”。
司马迁对外戚、依靠宫内裙带关系的人士并非怀有成见,因为当时的察举征辟制度势必造成如此局面,自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又如其将卫青、霍去病写入《佞幸列传》,不见贬低之辞,而是对他们的才能给予了肯定。但有德不能居其位,有才不能尽其用,仍是不少见的情况,司马迁在诸多列传中有所暗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除了个人的敬佩和同情,更多是站在一种非道德化的历史评价角度。他更在意事件本身、以及事态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故推测李陵或假意投降。但这些不仅没有挽回武帝对李陵的爱惜之情,司马迁自己也被认为是“沮贰师”而下狱遭刑。
《史记》和《汉书》对“收族陵家”的记载有差:《史记》中载“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武帝在得知单于将女儿嫁给李陵后,将其长安的家人诛杀。《汉书》中载“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一家被诛是因李陵在为匈奴实际效命。从两书的记载来看,事件的结果一致,而导火索不同。汉朝方面早就得知“李少卿教匈奴为兵”,但在司马迁笔下没有记载这一信息,从司马迁下狱以及撰写《史记》的年限来看,这些内容当是其出狱后补录的,应有两种情况:
一是司马迁并不认为这是激怒武帝的根本原因,而是单于嫁女。在武帝看来,这意味着以留在长安的家人控驭臣下的手段,不再绝对有效。甚至,李陵与单于女之子有望成为下任单于,可能凭借旧时影响与长安亲眷里应外合,后果极为严重。
二是司马迁当时已知这一消息,但据他看来,这是未经证实的传言,并非“事实上的真”,便不载录,此种可能性最大。《汉书》的说法是“性质上的真”,符合班固所处东汉时期的定论认识。
(二)贰师之败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武帝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人北伐匈奴,匈奴方诅咒汉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满朝上下人心惶惶,武帝召集巫卜测卦问吉。
1.战争结果:
“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又卦诸将,贰师最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
孟康曰:“其繇曰‘枯杨生华’,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谓匈奴破不久也。”孟康之语在《史记·天官书》中多次出现,“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此太史公指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专管文史星历,家学渊源,近乎卜祝之间。西汉朝廷的天象灾异、占卜、祭祀等记录,应也在司马氏父子关切的范畴之内。但史笔所见,当时能进言于上的是孟康,而非司马迁,孟康才是当时直接向武帝汇报和解读卜筮结果的人。但“卦得大过,爻在九五”真的是吉利之辞吗?
《杂卦传》云:“大过颠行,泽灭木也。”卦象描绘了形势已达顶峰,洪水滔天汹涌、断木浮沉无定的动荡之景。此卦的意义历来有诸多观点,不外乎过盛、过失、过咎三个层面。汉时盛行的“卦气”说,更是直谓“大过”乃“死卦”“大灾卦”,暗示某人之“过”致“失”而为“祸”。大过,其中大即为太(阳),也同泰(一),象数意义即武帝之“过”。
2.吉将人选:
“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卦诸将,贰师最吉。”
《汉书》中仅记载了两件同样卦为“大过”且“爻在九五”的事件,一是《轮台诏》中所提,二是一百多年后的哀帝婉娈董公事:“《易》大过卦:栋桡,凶。言以小材而为栋梁,不堪其任,至于折桡而凶也。”此评放在李广利身上也颇合适。
从大宛之役和战事中可见,李广利的军事才能难堪举国之重,劳师过费、遭逢失败是情理之中。除了孟康所言吉利,其他的解读皆难以看出汉军此役之吉。如此将不吉的主要因素隐而不谈,过度发散吉的次要因素,这是专门顺着武帝心思而说的“空话”,又将“吉将”精准指向李广利,于是武帝满意地借着吉卦亲发贰师。在战中,李广利的家人因长安巫蛊事受株连,他急于求功赎罪,违逆武帝“必毋深入”的圣旨。部下不愿为他莽撞送死而哗变,李广利临急斩将、撤军无方、劳困轻防、降于匈奴,成为武帝用兵以来最大失败。
“洎贰师不利,汉始不复出兵。”武帝发布《轮台诏》,反思对匈奴作战的失败,但除了“朕之不明”这样模板化的语词,未再有深刻的反省,而是诿过他人。“今计谋卦兆皆反缪”一句,便颇有对卜筮者们的埋怨意味,但从天人感应的意义上也直指武帝专断好胜之过。
三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司马氏作《史记》,孔子作《春秋》,是刺讥世道时政的“衰世之作”,寓示王道不彰、世道昏昧。《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淮南子》“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仪坏而《春秋》作……皆衰世之造也” 均表明了这种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他自己与壶遂的一段对话,将《史记》自比《春秋》,其著史的发心可见一斑。孔子与司马迁都有良好的易学功底,强调忧患意识,从史事中探知历史规律的用意实发一心。《史记》直书其事,有许多对武帝针砭之处,也常发剖析汉朝之弊的评论。司马迁久为太史,巫祝星历亦是其专业,为何不见他的占卜见解?
试析情况,或是司马迁对当时众多卜筮之人的结论持保留意见,有意“阙笔”,事后“沉默”,反衬出时弊丛生、个人力量难以改变的境况,其意不言自显。另外,《史记》受武帝审核,一度被称为“谤书”。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痛呼“唯在择任将相哉!”《孝武本纪》中载武帝受方术之士欺骗等事,婉转批评其过,是史官手中有限的履责方式。班固在《汉书》中记载了另一件同样卜为“大过卦”的史事,虽未事无巨细地记录卜筮内容,而事件主角之身份、利益牵涉之关系、卦辞吉凶之内容,都与前文对应,班固对司马迁颇为崇敬,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应也是同样“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的心怀。
四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盛行谶纬之说,武帝高压统治,存在用人过失,并将决断失误的责任推诿他人。但他在位期间大兴征伐,客观上为经营西域做了必要的历史积累。历代史论频频提及,既在历史层面承认其政治意义、历史影响,又常在道德层面批判其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汉武帝决策依赖于巫蛊卜筮,最终自陈“卦兆皆反缪”,其功业“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贵不能久、无咎无誉,正如大过卦所示。
《史记》与《汉书》,对客观历史的记述总体上一致。虽因时代背景不同,作者的具体表述、对事件的认识评价存在一定差异,部分文句被认为或是“曲笔”,但这并不使他们的直书精神和历史使命感“失色”,反而折射出史家传统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田余庆. 论轮台诏[J]. 历史研究,1984(2).
[2] 王子今. 西汉长安的“胡巫”[J]. 民族研究,1997(5).
[3] 胡平生. 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J]. 出土文献研究,1998(2).
[4] 余江. 谶纬与两汉经学[J]. 天府新论,2002(1).
[5] 赵永磊. 关于《史记》“贬天子”问题的解读[J]. 史学史研究,2008(3).
[6] 陈金霞. 汉武帝《轮台诏》并非罪己诏[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7] 尹冬梅. 从《史记》对汉武帝的批评看司马迁对秦文化率直求真精神的继承[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2).
[8] 辛德勇. 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9]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0] 杨勇. 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6(2).
[11] 田志宇. 周易中的“过”[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6).
[12] 刘哲. 读《论轮台诏》所引发的史学反思[J]. 生活教育,2021(1).
[13] 黎镜明,王欣. 巫风笼罩下的西汉与匈奴关系从“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说起[J]. 史林,2021(4).
[14] 任蜜林. 论谶纬之学与两汉今古文经学之关系[J]. 清华国学,2023(2).
[15] 王锐.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
[16]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
[1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1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0]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国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