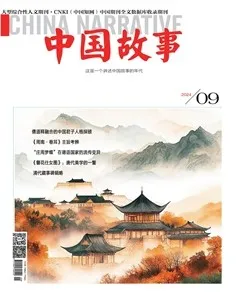隋唐慕容氏的华夏认同
【导读】吐谷浑族、豆卢氏和河南慕容氏源自游牧民族慕容鲜卑。隋唐时,三支在祖源、血缘、郡望和姓氏来源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汉文化认同,但在融入汉文化的过程中各有侧重。
隋唐时期处于民族融合高潮期,慕容氏作为鲜卑族一支,曾建立了前燕、后燕政权,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吐谷浑族、豆卢氏、河南慕容氏三支。传世文献往往是叙写宏大历史,着墨于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历史细节关注不够,墓志则可以进行弥补。慕容氏三支墓志保留了诸多重要历史信息,墓志文字展现出慕容氏三支当时的汉化进程及其内部差异。
一、氏分三支,族分两地
慕容氏源出鲜卑,分为三支,三支居两地。
其中一支远居边地,为吐谷浑族。《魏书》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后吐谷浑因与慕容廆发生马斗,西上阴山。分裂出来的吐谷浑,不断融合羌、氐等其他民族,形成一个地方政权。吐谷浑之孙叶延,“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遂以吐谷浑为氏焉”。新族名标志着吐谷浑一脉在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下,形成了区别于原慕容鲜卑的吐谷浑族。
隋唐时期,一直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慕容氏分为两支。一是保留着慕容姓氏的皇室后裔,以“前燕文明皇帝之第四子太原王恪之七代孙”慕容三藏为代表;一是改姓的豆卢氏。后燕覆灭后,为了逃脱北魏的政治迫害,部分族人改姓豆卢氏,历经沉浮,以慕容精的后人豆卢勣、豆卢贤、豆卢钦望等为代表。改姓的历史在豆卢氏的墓志之中也有所体现,豆卢愿墓志中写道:“在北为慕容氏,后魏改为豆卢。”豆卢贤墓志中关于这段历史描述更为详细,“既而时遭崇替,运属推移,改族豆卢。”
二、墓志中的文化融合
虽然三支同出慕容,但是吐谷浑族早已分化出去,形成了独立的民族,与留在中原地区的慕容氏两支截然不同。尽管如此,慕容氏三支在自我推动与外部影响下,不约而同地走上汉化道路。
(一)丧葬细节变迁
书写墓志,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据文献记载,作为游牧民族,早期慕容鲜卑流行“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这种潜埋虚葬的习惯。中原地区的汉族习惯于墓前立碑,碑大体繁,耗资甚多。在朝廷禁止之下,地上之碑转为地下墓志,盛行依旧。慕容鲜卑跟随汉族丧礼撰写墓志,或亲人撰写,或请人代写,于墓志之上描刻具有汉族文化内涵的缠枝、四兽等图案装饰。
根据出土的墓志可知,慕容氏在葬地方面逐步向洛阳和长安靠近,如慕容怀固“葬于洛州洛阳县界北邙山”,豆卢逊“窆于万年县少陵原”。在早期,洛阳与长安并非慕容氏的理想葬地。同汉人死后归葬的观念一样,慕容鲜卑同样有着死后回归祖辈发源之地的愿望。这种愿望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减淡,一方面是由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推动鲜卑汉化,实行“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之令,入仕北魏的慕容氏难以回到祖源之地;另一方面是慕容氏入唐之后,为了表示忠心并发展家族,势必选择政治经济地位非凡的两都洛阳与长安,作为家族葬地。豆卢贤墓志中写道:“归葬于京兆郡泾阳县之洪渎原。”归葬二字的使用表明,豆卢氏一支在心理上已将长安视为新的祖茔。
(二)祖源记忆重构
墓志的撰写往往会突显出家族荣耀和文化传统,以此来塑造逝者的形象和家族的声望。
慕容祖先是鲜卑的中部大人,他的身世却在墓志之中发生了转变。慕容琛墓志中写道:“其先出自有熊氏之胤”,慕容珣墓志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有熊氏即为黄帝,并非炎黄子孙的慕容氏这样书写,正是出于民族认同心理。慕容氏受汉人影响,积极追溯民族历史,意识到汉文化的优越性,产生华夷共祖的书写意识,将自身历史置于中华民族历史框架之中,希望更好地被中原汉族接纳。慕容氏同时也积极地用汉文化来解释自己姓氏由来,慕容二字在墓志中解释为“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
慕容氏三支虽然同出慕容鲜卑,但由于早期的分裂与后期的改姓流散,各支系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祖先的追溯往往是向上三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祖源的记忆会越来越模糊,但三支的墓志里都表现出对慕容鲜卑的认同。作为保留姓氏的皇室后人,慕容三藏一支出现这样的行为合情合理,为何更改族名的吐谷浑与改姓的豆卢氏也这样做?归根结底,仍是出于融合的共同体意识。家族与出身在唐朝仍是评判个人的重要标准,游牧民族并没有像汉族清河、陇西经营上百年的郡望,于是要回顾先祖历史,追寻显赫之人、显赫之地,突显门庭。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是游牧民族积极汉化的代表,早在慕容廆时期,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对汉文化的认同,推崇儒学,提拔重用汉臣,通过移风易俗的一系列措施推动民族汉化进程。慕容氏三支对慕容鲜卑的认同即对汉文化的认同。因此,豆卢氏墓志提到:“昔燕武皇帝以雄踞海朔,开建宝图。文明皇帝以长驱蓟城,兴崇大运,此则君之先也。”吐谷浑墓志中写:“当十六代祖,前燕析居白兰之阴,遂为东西慕容”。为了更好地在唐朝发展壮大,慕容氏三支都积极突显先祖与郡望。
(三)胡汉互通婚姻
慕容鲜卑在婚俗方面经历了一系列转变。
起初,慕容鲜卑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存在着古老的血缘群婚习俗。进入中原后,慕容鲜卑的婚姻制度逐渐趋于稳定,尽管一些旧俗仍然存留,但整体上已经接近汉人社会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
在婚嫁对象上,初入中原的慕容鲜卑一方面仍保持着嫁娶同族人的传统,同时开始强化与汉族之间的通婚制度,尤其是皇族与汉人之间的婚配更为自由。这种现象在隋唐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慕容三藏,他前后娶了两位夫人,“夫人叱李氏,齐武威王国妃。后夫人虞氏,隋河内郡夫人”。前者为胡族,后者为汉人,慕容三藏的子孙后辈在婚姻对象上也大多为汉人女子,如京兆鱼氏、陇西李氏、太原郡君武氏、河南韦氏、博陵崔氏、北海唐氏,仅有河南源氏与费氏为胡族女子。
族际通婚是密切的族际交往活动,文化融合对族际通婚具有正向作用。在通婚过程中,个体之间不仅分享家族资源,也将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带入彼此的家族中,从而又促进文化交融和共生。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间推移,原本鲜明的民族文化边界会逐渐模糊,个体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央王朝的认同,塑造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墓志中的汉化差异
慕容氏三支在隋唐时期主动融入汉文化圈,寻求唐王朝接纳,但由于生存状况与家族积累不同,三支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差异性。
家族郡望深刻影响着墓志书写。隋唐时期的慕容三藏一脉,是皇室后裔,最早受到汉化政策影响,自慕容三藏始,就表现出对慕容鲜卑建国之地昌黎棘城的认可。慕容三藏一脉强调自己为前燕皇帝慕容皝之后。但仕宦洛阳几代人后,慕容知敬墓志中出现了两种身份认同,“其先昌黎榖城人……今为河南洛阳人也”。随着时间推移,后辈墓志中只剩下了一种身份认同,即慕容相墓志中的“其先河南人也”。
对于豆卢氏,改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慕容鲜卑的认可。另外,豆卢氏处于政治高层,融入汉文化圈的需求迫切,豆卢氏墓志中对昌黎棘城的提及频率,远不如慕容三藏一脉,他们更偏向于称自己为河南洛阳人。
吐谷浑一支更是鲜少提及自己为昌黎棘城人。唐前期,吐谷浑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因此在墓志之中称自己为阴山人。比如慕容忠墓志中写道:“王讳忠,阴山人也。”但是随着政权灭亡,失去属地的吐谷浑族人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慕容威、慕容环墓志中称自己为昌黎棘城人。此后,为了寻求认同,更好地在唐朝发展,吐谷浑一支之后直接称自己为长安人。
通婚是汉化方式之一。根据墓志记载,慕容三藏一脉与皇室联姻只有一例,即慕容真如海,族内其他子弟的婚姻对象虽有大姓,如陇西李氏、博陵崔氏,但对妻子家族男性官职记载甚少,应为大族的支系。豆卢氏与吐谷浑的婚姻对象则显赫得多。豆卢钦肃之女为唐睿宗贵妃,豆卢通娶隋文帝之妹昌乐公主,豆卢宽娶隋观德王杨雄之女,豆卢怀让尚唐万春公主,豆卢勣之妹为周齐王宇文宪之妃,女为隋汉王杨谅之妃,可见豆卢家族与皇室联系紧密,这也是他们能够取得重要政治地位的原因。吐谷浑更是频繁地与唐朝联姻,弘化公主、金城县主、陇西李氏女李深、姑臧县主、金明县主,皆是和亲代表。婚姻对象家世的区别,折射出隋唐时期慕容氏三支汉化过程中的地位差异,三藏一脉地位明显下降,成为一般士族,豆卢氏、吐谷浑则通过与唐朝王室联姻,获得政治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吴刚. 全唐文补遗[M]. 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4] 柴怡,赵兆,杨永刚,等.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隋唐豆卢贤家族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22(1).
[5] 徐吉军. 中国丧葬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6] 齐运通. 洛阳新获七朝墓志[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7] 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G].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 顾雪军,屈昆杰,高向楠,等. 洛阳唐豆卢恕墓发掘简报[J]. 中原文物,2018(3).
[9] 西安市长安博物馆. 长安新出墓志[G].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10] 慕容浩. 浅析慕容鲜卑的汉化[J]. 北方经济,20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