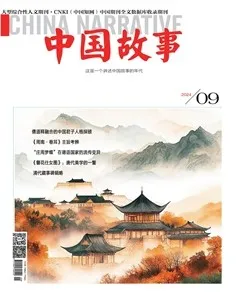解读民国文人笔下的“扬州梦” 邱源
【导读】拉康的镜像阶段论揭示了“主体”如何通过“镜像”与“他者”确证自我的存在,并在三者交融共生的关系中形成稳定的主体间性,这一理论为民国扬州游记散文的文化隐喻与转型提供了恰当的视角。“扬州梦”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经世代积淀的文化符号,代表了风花雪月、诗情画意的人间天堂,却在古今转折的民国时期,因城市的衰败而成为文人们抒发兴衰更迭、怀古情愫、家国悲怆等感伤情愫的载体。通过分析承载着文人真情实感的游记散文,从对于古代繁盛景象的追思和现代断壁残垣的唏嘘中,可以窥见“扬州梦”无形中应和着风雨飘摇中文人的末世心态,亦象征着二十世纪面临现代转型的中国,亦可以挖掘出扬州城市文化重构与新生的可能性。
1949年7月17日,拉康在苏黎世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镜像阶段的概念。通过比较猴子与6个月大的婴儿,在镜子前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和思考模式的实验,揭示出人类对于自我的认知是从镜子的影像中获得的,也即镜像中的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主体自身的特质。他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精神分析经验所揭示的一个阶段》一文中,将这种由镜像带给主体的“认同过程”视为“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进而认为这种“主体”与“他者”的辩证关系,使得“主体”更加客观化,此后“语言才给我重建起在普遍性中的主体功能”。
语言建构使人类具有如观“镜中之我”的类似体验。由此,拉康的镜像阶段论将语言作为媒介,推演出“理想我”的存在。本文将尝试运用拉康镜像阶段论,分析中国历史上“扬州梦”这一文化符号,何以成为文人心目中关于诗意古韵生活的全部想象,继而经由“他者”确证成为自我幻想中的“主体”,又是何以在民国时期遭遇“主体”坍塌,而在另一种程度上成为文人时代情绪的载体。从“镜像”建构到“主体”确立,再到“镜像”破碎,“扬州梦”成为二十世纪之交时代情绪的文化隐喻。
一、“扬州梦”的生成机制与文化建构
杜牧《遣怀》中“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可谓是首次命名了“扬州梦”,除此之外,杜牧亦创作了大量有关扬州的诗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将他的诗酒风流与扬州的城市文化几乎画上等号。历代文人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对于扬州城市风貌的溢美之辞,化用杜牧“扬州梦”的典故,元人乔吉《杜牧之诗酒扬州梦》与清人嵇永仁《扬州梦》更是强化了世人对这座文化名城纸醉金迷、歌吹沸天、莺歌燕舞的拟想。“扬州梦”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突出的文化符号。
一座城市让文人墨客魂牵梦萦,在中国古代并非新鲜事,自古便有“长安梦”“秦淮梦”等。这些占据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的城市,因具有实现功名利禄或文化雅集的功能,而成为文人或士大夫普遍追求的理想之城。“扬州梦”的产生自然与扬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休戚相关。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使得扬州整座城市成为交通枢纽,乘运河之利,一跃为中国当时最为繁华富庶的大都会。经济繁荣带来的便是物质的富裕,思想文化的兴盛使得络绎不绝的文人汇集扬州。可以说,隋唐时期扬州成为文人墨客心驰神往、醉生梦死之地,他们在诗句中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流露出发自内心的赞叹。扬州虽然从未成为政治中心,无法安放文人追求经国济世的传统抱负,但提供了另一种风流潇洒、声色犬马、逍遥自在的生活体验。
这种文人世代积累的文化符号,带有深刻时代烙印,也保存了文人对于扬州的集体记忆与原始想象。中国历代文人通过诗词歌赋构筑起的扬州印象,也成为扬州具有代表性的一面文化镜像。这种由文人书写的“镜像”并建构的“扬州梦”甚至遮蔽了扬州真实“主体”和历史变化,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们对于扬州的惯性思维与全部幻想。
二、民国扬州游记散文中的文人心态
作为一种叙事文体,游记散文古已有之,其主要按照一定的时间或空间顺序,真实记录游览过程中的所见、所想,蕴藉着作者的真情实感。本文通过分析民国扬州游记散文中不同的文人心态,从文学文本中发掘民国时期文人笔下扬州的历史风貌,以及“扬州梦”的古今转变。
(一)流连美景的赞赏之情
扬州的旖旎风光古来便享誉盛名,到民国初年仍保留原本独特的风景,于是便有易君左在《闲话扬州》中总结了以八个字为代表的扬州风景——“清新、幽丽、柔和、纤细”。尤其在民国初年,战争还未侵扰至扬州时,其美景仍犹如江南的风景画,令人流连忘返。“惟自拱辰门来……步步引人入胜,真是人间天上,此隋炀帝、清高宗所以流连忘返也”。李根源的《扬州游记》如是说。甚至,扬州的繁华富贵气息仍未消散,并未与诗词歌赋中有二致:“余观扬之富庶,不减苏州,风俗习惯,人物服饰,亦多于苏同。然余于两地,终嫌文胜于质耳。”
哪怕战争摧毁了这座城市诸多名胜古迹,但是其间隔出现的自然风光,仍然让游人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和涤荡心灵的喜悦,如舒新城《瘦西湖里三小时》记叙了匆匆一览自然景观的惊艳:“……而路左有很多古老参天的松柏,松涛壮美,最足以洗涤我们枯居城市的烦虑,于是决定不去刹中,而向松林中觅乱石静坐。”
(二)兴废沧桑的盛衰之感
正因为扬州历史上曾有过极度繁盛之时,并经由文字代代相传、层层累积,所以当想象中的扬州和现实中的扬州发生错位时,便会产生理想幻灭之悲怮,生发人世沧桑之痛惋,恨昔日之景荡然无存。尤其是郁达夫所写,“回想起两百年前……黄旗紫盖,翠辇金轮,妃嫔成队,侍从如云的盛况,和现在的这一条黄沙曲路,之见衰草牛羊的萧条景象来一比,实在是差得太远了”。朱偰在《扬州纪游》中看到断壁残垣、废池乔木也不禁抒发感慨:“盖维扬一隅,今日而登临游览,诚有不胜古今盛衰之感者矣。”
“扬州梦”营造的诗意生活与民国的萧条落魄有着天壤之别,美梦破碎,留下的便也是无尽的失落与惆怅。除了战争的创伤,亦有人事变幻带来的物是人非、人走茶凉,这是比废墟残骸更令人心酸的悲凉。正如洪为法《扬州续梦》云:“据云抗战以后,已经换了主人,或者新旧主人的心襟互异,这才使绿杨村大异旧观,固不仅因为乱离的关系罢!”
(三)凭吊追思的怀古之思
大多数文人墨客来到扬州如非匆匆一瞥,一定都要游览扬州的名胜古迹。这一方面是为了抒发迁客骚人幽微的怀古之思,追随古人的脚步,感受古韵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印证“扬州梦”的美名,那些诗词歌赋里确有存在的遗迹,以便于亲眼所见两相对照。
瘦西湖、五亭桥、小金山、天宁寺、二十四桥、平山堂……扬州的景点不仅集中,而且连贯,并且处处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典故。它们既是乾隆下江南的必经之地,有着隋炀帝看琼花的瑰丽传说,也孕育了欧苏文化、扬州八怪,在古时真可谓一块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民国年间文人也基本上遵循着旧时的记载,描绘出一幅民国扬州风景地图。朱偰在《扬州纪游》中写道:“入城已黄昏,乃于翌晨烟雨中,发自城南,举目长垣,不胜依依之感。”虽然扬州的许多人文景观在民国年间已经呈现出颓败坍圮之色,却并非完全一片荒凉,仍让人心生依恋、念念不忘。
(四)贞烈忠骨的缅怀之叹
如前所述,“扬州梦”并不单纯局限于歌舞升平、夜夜笙歌的缱绻,也有义薄云天、保家卫国的忠烈。明末史可法在扬州顽强抵御清兵,他不屈就义的故事也为扬州这座城市赋予了一层英雄的色彩。故而许多文人慕名来到史公祠,在堂前缅怀这位忠正公的英灵,如李根源《扬州游记》中“今亲至其地,则诸公当日飞檄讨贼,婴城致命之英风浩气,愈想象得之”,追忆当年史可法与敌人激战的景象。
三、民国时期“扬州梦”的文化隐喻
民国游记散文无一例外都是先表达对于扬州充满朦胧美丽的想象,继而才来扬州旅行,在看到实景之后,罗曼蒂克式美梦幻灭。文章往往大量引用唐宋时期对于扬州吟咏称赞的诗句,并且提及的典故和意象都极为相似,如“二十四桥”“烟花三月”“绿杨城郭”“梅花岭”,等等。可见在大多数文人眼中,诗情画意的扬州似乎已经存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模式,并非先有实践,而是先有想象。
民国游记散文中多篇提及“扬州梦”,有直接以“扬州梦”为题的,如郁达夫《扬州旧梦寄语堂》、洪为法《扬州续梦》,有的则是在文章中表露出对于“扬州梦”的向往,如范烟桥《绿杨城郭的一瞥》中“这个扬州梦,我已经做了好久了”,张慧剑《扬州漫游记》中“瘦西湖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瘦西湖,而湖畔的绿杨村,却俨然就是我曾做梦来过的绿杨村”,更有如芮麟《扬州纪游》将扬州比作“人间的天堂”。这些文人大多只是游客或过客,从未见识过真正的扬州,对“扬州梦”的美好想象却深深地镌刻在这些游记散文的字里行间,这也代表着民国新旧交替时期文人内心根植的对传统所建构理想之处的崇拜,以及梦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
除了充满“盛唐气象”的“扬州梦”,南朝鲍照的《芜城赋》与南宋姜夔的《扬州慢》又增加了由盛而衰的苍凉之感。扬州因其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为由北入南的关键闸口,故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时常受到侵袭,屡遭兵火洗劫,亦有着“黍离之悲”的文化意蕴,折射出人事沧桑变幻的深刻哲理,也蕴藉了文人深切的家国情怀。民国时期因近代铁路势头高涨,运河已经江河日下,城市便也无可挽回地又一次衰落萧条。当亲临其中的人,对比今昔,便也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惋惜、感伤与落寞之感。这既是“黍离之悲”在民国时分的再次重现,也正好击中了处于二十世纪之交风云激变时分文人的内心,引发文人们共通的时代情绪。想象的破碎与文人、士大夫的处境不谋而合,又与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何其相似。正如郁达夫在《扬州旧梦寄语堂》的最后说:“枕上的卢生,若长不醒,岂非快事。一遇现实,哪里还有Dichtung!”这正是对于沉溺“扬州梦”的批判与反讽。
朱自清在《说扬州》中从扬州人的视角出发,凭在扬州丰富的生活经历,道出对于扬州的客观评价:“也不是说得太好,他没有去过那里,所说的只是从诗赋中,历史上得来的印象。这些自然也是扬州的一面,不过已然过去,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美梦。”朱自清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地揭示出“镜像”只是“扬州的一面”,繁华旧梦并非扬州的全部面貌。只有从根底里迸发出来的,那些真正属于扬州民间的,才能成为这座城市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所在。
四、结语
自民国年间历经现代转型后,扬州原本给人们留下的纵情声色的印象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荡然无存,然而一种有别于现代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气质,以及幽深的古韵却日益突出。朱自清《扬州的夏日》的最后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傍晚回来,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一手微微摇着扇子;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在这样一幅极为悠然闲适的氛围里,作者油然而生“这时候可以念‘又得浮生半日闲’那一句诗了”的自在逍遥之感。这也是为何许多文人纵然破除了对于扬州原本美好的想象,而仍在不经意之间发现了始料未及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感受一种独属于扬州的韵味。
“理想我”在现代转型与时代巨浪的冲击下走向毁灭后,关于扬州的文化想象将如何重新建构?拉康认为“镜子阶段是场悲剧”,其原因在于“建立起异化着的个体的强固框架,这个框架以其僵硬的结构将影响整个精神发展”,在内外世界建构的循环中“导致了对自我验证的无穷化解”。因而,在证明镜像阶段所带来的幻象只是虚妄之后,对其破除以及重新审视便迫在眉睫。“扬州梦”的现代转型便是镜像阶段走向终点的预兆,也是扬州城市文化重构与新生的起点。
参考文献
[1] 拉康. 拉康选集[M]. 上海:三联书店,2001.
[2] 刘训扬. 民国扬州风情[M]. 扬州:广陵书社,2009.
[3] 宗金林. 民国扬州旧事[M]. 扬州:广陵书社,2009.
[4] 苏保华. 扬州文学镜像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 韦明铧. 扬州传:绿杨明月映珠帘[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6] 金晶. 扬州园林文萃[M]. 扬州:广陵书社,2018.
[7] 安东篱. 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