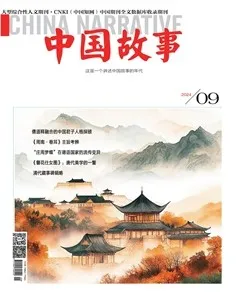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残雪小说的读者接受研究
【导读】20世纪80年代残雪小说的读者接受活动主要受到作家圈子、报刊媒介、文学批评与文学选本的影响。残雪借助作家圈子与报刊媒介,获得了文学场的“入场券”,作品得以发表与传播。文学批评与文学选本对残雪的小说进行了筛选与定位,通过将其纳入流派群体加以传播与接受,并逐渐实现了“经典化”。残雪小说的读者接受情况是其作品内在艺术特征与外在场域状况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文学活动离不开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在接受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姚斯看来,文学史不应是作家作品的编年史而应是读者接受史。以姚斯、伊瑟尔等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在继承现象学、阐释学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接受美学,将文学研究的重点从作品内部研究转移到外部的接受史、影响史之上,从而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社会学视野。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残雪始终是独特的存在。残雪自1985年发表《污水上的肥皂泡》以来,已经创作了七百多万字的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多个方面。残雪小说的读者接受活动与其创作活动相伴而生,并形成了独特的“残雪现象”。“残雪现象”的产生既与其小说的艺术特征紧密相连,也与特定文学场域中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机制密不可分。本文借鉴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范式,通过回归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场,进而探究影响残雪小说传播接受及其“经典化”的多重因素。
一、文学场域与残雪小说的传播
残雪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根据其哥哥唐复华的说法,残雪第一个正式完成的作品是中篇小说《黄泥街》,写成于1983年底,“这个十来万字的作品断断续续反复写了好几年,抄在好几个笔记本上,在一些人中辗转流传,还被带到了海外”。《黄泥街》的第一稿完全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残雪并不满意,1983年流传的是采用现代主义手法改写之后的版本。但是,《黄泥街》的发表却费尽了周折,经多方努力,最终于1986年发表在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残雪发表的首篇小说是《污水上的肥皂泡》,1985年发表在湖南《新创作》杂志第1期。为何残雪的小说在1985年发表而不是1983年?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既与残雪小说的艺术特征有关,也与当时的文学场域状况密切相连。1983年左右“改革文学”等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的作品方兴未艾,而1985年却呈现了不一样的“风景”,正如吴亮所言“1985年对残雪而言肯定是个十分要紧的历史机会”。不仅仅是残雪,对很多作家都很重要。争夺文学场“入场券”是残雪也是每一位作家创作初期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残雪是幸运的。
残雪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本身就具备较多的文化资本。残雪的父亲邓钧洪总是将一些书籍带回来给残雪姊妹们阅读,哥哥姐姐也总是将别处借来的书放在家里任由残雪翻阅。由此,残雪幼年时便已接触了《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等大量中外文学作品,从而具备了较好的文学素养。而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就是“作为资本的文化”,文化资本的传承深受家庭和学校影响。残雪的家庭无疑使残雪具备了更多的文化资本。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现代派”文学相同的兴趣,残雪与何立伟、徐晓鹤、王平形成小圈子,不定期开展文学沙龙活动。残雪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得益于这个圈子,正是何立伟、王平等人向《新创作》杂志的张新奇推荐了残雪的小说,并得到了后者的认可,《污水上的肥皂泡》才得以发表。而《黄泥街》的发表曾得到谭谈、韩少功等多位湖南作家的帮助,虽未成功,但对于残雪小说的传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此外,在蒋子丹和吴若增的帮助下,残雪的《阿梅在太阳天里的愁思》最终发表在《天津文学》。
残雪正是借助《人民文学》与《中国》杂志逐渐走向“新时期”文学场域中心的。在文学场域中,不同传播媒介占有的文化资本是不同的,每种传播媒介都有着自身的“场”,有着一定范围的作者、读者与批评传播力量。换言之,在何种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直接影响着作者所能获得的文化资本,从而影响作品的传播与接受。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场域中,《人民文学》与《中国》杂志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地位。《山上的小屋》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8期,是残雪发表的第二篇小说,这对于一般作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作品的发表离不开编辑的作用。王蒙于1983年8月至1986年12月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山上的小屋》必然得到了王蒙等人的认可,这与王蒙对于“新潮小说”的支持有重要关系。《人民文学》1986年还刊发了残雪的《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由此观之,王蒙对于残雪具有重要的“知遇之恩”,不仅发表了其作品,在1988年残雪作品被批评之时,王蒙撰写了《读〈天堂里的对话〉》,较为客观地分析了残雪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局限,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丁玲主编的《中国》杂志对于残雪,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86年《中国》发表了残雪的三篇小说和一篇散文,残雪的代表作《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均在其中。《苍老的浮云》曾遭到《收获》《钟山》等杂志退稿,后在李陀、牛汉等人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发表。正是通过湖南作家圈子与《人民文学》《中国》等杂志创造的平台,残雪的小说得以发表与传播,从而进入读者的接受视野。
二、文学批评与残雪小说的接受
文学批评是文学接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学者蒂博代根据文学批评的不同特点,将其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与大师的批评三种类型。文学批评具有较强的“在场感”,是对于作家作品最为直接的接受活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阐释与定位,为作品的有效流通实现更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创造了条件。考察20世纪80年代残雪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情况,需要重返文学现场全面梳理读者对于残雪小说的评价,从而呈现文学现场的丰富性。
残雪小说发表之后,便进入了读者的接受视野,面对残雪小说独特的艺术特征,读者产生了不同接受现象,在“数一数二”与“一无是处”之间,残雪的小说面临文学批评的检验。正如李建周教授所言,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文学批评是作家作品能否有效流通的隘口,“被文学新潮卷入文坛的残雪面临批评圈子的严格检验”如果不能通过文学批评的检验,作家能否继续创作都将成为问题。残雪1983年年底完成了《黄泥街》的修改稿之后便在邓晓芒、何立伟、王平等人之间传阅并作出评价。此时对于残雪小说的文学评价与接受活动便已经开始,而依托纸质媒介发表的评论,可追溯至1985年。1985年第9期的《作品与争鸣》杂志选载了《公牛》,并且配发了多篇评论文章。正是在《作品与争鸣》杂志的规划意识之下,围绕《公牛》的讨论得以展开,代表文章包括:沙水(即邓晓芒)《〈公牛〉与时代意识》,伍然《对〈公牛〉与时代潜意识的质疑》,洲石《重要的它是一头公牛》,陈家琪《另一世界的一道紫光——〈公牛〉再评论》等。沙水认为那道神秘的紫光是命运的象征,公牛实际上就是深深埋藏在人心之中的自我象征,是被压抑而渴望觉醒的自我。伍然则认为《公牛》是精神病人的呓语,是精神病人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根本不是文学作品,整个“新潮小说”只是对于西方的拙劣模仿,毫无新意,甚至不能称作文学。洲石与陈家琪的文章只是以《公牛》为引子,逐渐谈到了其他方面。围绕《公牛》的讨论只是表象,背后是不同创作技法与文学认知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的背后则是20世纪80年代不同文学观念的具体呈现。
如果说围绕《公牛》的讨论是“新”与“旧”不同文学观念的呈现,那么围绕《突围表演》的讨论则是前者内部的差异与分歧。在短暂的热潮之后,“先锋小说”迎来了瓶颈期,如何避免作品的重复、不断超越自己成为“先锋作家”思考的核心,在此背景下残雪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突围表演》。《突围表演》发表于1988年的《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该作发表以后,随即获得了评论界的关注。唐俟、吴亮、沙水、郜元宝、舒文治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其是“偏窄的个人情绪的外化”,也有的学者认为其是“向生存边界的冲击”。唐俟、沙水与吴亮的通信则将讨论推向高潮。残雪的哥哥唐俟与沙水,对于残雪的小说始终秉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彼此相近的生命体验,使其更容易理解残雪小说的内涵。而吴亮对于残雪的小说呈现了较大态度的转变。在对1986年小说回顾的过程中,吴亮认为残雪的小说“把我们带入一个内在的关于世界本相的境域”,而在1988年则宣布“残雪的小说却悄悄地透露出衰竭的信号”。在《关于残雪小说论争的通信》中,双方也逐渐从学理讨论转向了意气之争,正如李建周教授所言,双方的分歧在于生命经验与知识谱系的分歧,通信的背后是残雪哥哥为残雪争夺更多象征资本而采取的策略。吴亮的态度转变也并非个案,回归历史现场会发现,曾经大力支持“先锋小说”的批评家们,纷纷转向了批评,甚至怀疑是否存在“先锋小说”。这无疑与“先锋小说”的普遍困境紧密相连。当“怎么写”取代“写什么”的文学实验陷入重复与极端境况之时,“先锋小说”越来越脱离读者,变成为了实验而实验。“先锋小说”所具有的表演性,使其获得巨大声誉的同时,本身也具有危机。作为“旗帜”人物的马原,在声誉鹊起之时却选择了“封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而文学界对于残雪小说态度的转变,便是“先锋小说”命运的具体呈现。
三、文学选本与残雪小说的“经典化”
文学选本对于作家作品的筛选、定位乃至“经典化”,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选本背后蕴含着编选者文学观念与规划意识的差异,而在文学场域中,文学选本往往与文学评论联动,文学选本既是对于作家作品的筛选,也是对于文学评论成果的确83ACucpbXfZLq8eyLJrO2w==认。通过选本的筛选与传播,单个作家变为作家群体而具有重要的“集群”作用,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考察20世纪80年代残雪小说的接受情况,对于不同选本的比较研究是重要的切入点。
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残雪的小说共入选了6个选本,具体情况为:《公牛》入选吴亮与程德培编选的《新小说在198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山上的小屋》入选程德培与吴亮编选的《探索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天窗》入选莫应丰编选的《湖南实验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苍老的浮云》《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天窗》《旷野里》入选吴亮、章平与宗仁发编选的《荒诞派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入选吕芳编选的《褐色鸟群 荒诞小说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给有人》入选程永新编选的《中国新潮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这些名称中标识有“新”“探索”“实验”“荒诞”字样的批评与思潮类文学选本,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作家作品的初步定位与筛选,并深度参与了先锋文学的群体建构与“经典化”。选本编撰者具有很强的规划意识,但是并非所有选本选入的作家都成为了“先锋派”,其中呈现了动态的筛选与确认过程。《天窗》《山上的小屋》与《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分别入选了两个选本,侧面呈现了残雪小说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呈现的差异性,以及编选者的不同编选趣味,《山上的小屋》等也成了残雪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
在以上选本编撰者中吴亮的参与率最高,参加了三个选本的编撰,对于“先锋小说”的筛选与“经典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早期的文学选本中“新”“实验”“先锋”“探索”等名称具有相似的内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命名者的意图,而“先锋”的提法并非一开始便被广泛使用,正如程光炜教授所言,“先锋”是“追授”的概念,“先锋派”是从“新潮”“探索”等作家群体中进一步剥离的结果。而在陈晓明教授等看来,先锋作家群体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与余华、苏童等稳定的“先锋派”不同,残雪则成为难以简单归类的作家。通过分析选本,残雪小说入选最多的则是书名中带有“荒诞”字样的选本,吴亮、章平与宗仁发编选的《荒诞派小说》最具有代表性,该书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编选者试图以思潮流派的方式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筛选与甄别。在开篇导入部分,章平撰写的《“荒诞派”在中国》对于“荒诞派小说”概念进行了解释:“‘荒诞’既是‘存在’的状况,又是对这种状况的理解、感受和态度。”编选者认为开启“荒诞派小说”思潮的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而残雪是最重要的代表。根据《“荒诞派”小说》收入文章情况也可看出编选者对于残雪小说的态度,本书共收录十七篇小说,而残雪独占四篇,由此可见在编选者眼中残雪小说的代表性意义。经过文学选本的编撰,残雪小说逐渐实现了“经典化”,但文学史往往将其纳入“现代派”作家序列加以考察,从而呈现了两者间的联系与差异。
四、结语
残雪的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被纳入“新小说”群体“冲击波”中被传播与接受,正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使其作品走入读者接受视野,但其独特的艺术特征以及读者“期待视野”的差异,使残雪的小说既给读者带来惊喜也带来困扰。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文学场在整体社会场域中的位置逐渐边缘化。文学场域内部也在重演着布厄迪尔所指称的“老化逻辑”,新的文学思潮不断兴起,残雪逐渐淡出了20世纪90年代读者的视野。但残雪是一位“孤勇者”,时至今日仍在坚守“新实验文学”的探索,营造自己的“文学乌托邦”,由此残雪小说的读者接受研究仍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萧元. 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 吴亮. 一个臆想世界的诞生——评残雪的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1988(4).
[3] 李建周. 批评的圈子与尺度——以残雪的接受为例[J].文艺争鸣,2011(17).
[4] 舒文治. 伪造形式的迷宫——读残雪的《突围表演》[J]. 文学自由谈,1989(3).
[5] 郜元宝. 向生存边界的冲击——评残雪的《突围表演》[J]. 当代作家评论,1989(1).
[6] 吴亮. 告别1986[J]. 当代作家评论,1987(2).
[7] 吴亮,章平,宗仁发. 荒诞派小说[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