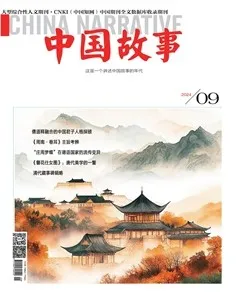唐诗中的“电影思维”及其当代价值
【导读】电影思维是与电影银幕形象有直接关联的思维活动,最大程度地体现着电影的特性。电影思维特征与唐诗的艺术特色存在共通之处。本文围绕“视听综合”“时空意识”“镜头运用”三方面探讨了电影思维在唐诗中的体现。
文学语言有电影性,电影语言也有文学性。电影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有继承关系。诗歌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集中体现,与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国平在《论诗与电影》中指出,诗歌系统与电影系统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和渗透性。目前,在诗歌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学界已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研究也渐次深入,但主要集中于蒙太奇镜头与诗歌艺术手法的讨论,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扩展。
韩世华教授在《论电影思维》中界定了“电影思维”的三种运行方式:一是视听综合——影像思维线,二是时空综合——情节思维线,三是蒙太奇与长镜头——构剧思维线。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富于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样式,“电影思维”在唐诗中有较为显著的体现。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唐诗作为研究对象,从视听综合、时空意识、镜头运用三方面探讨“电影思维”在唐诗中的表现,旨在促进唐诗的电影化传播,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学在新时代闪耀光辉,同时也为当代电影的艺术表现提供某些启发。
一、视听综合:余音袅袅中的兴象玲珑
“兴象玲珑”是唐诗重要的艺术特色。“兴象”并非只是单纯的视觉意象,也包括声音意象。唐诗运用色、声、形的技巧创造了无数脍炙人口的美诗,这种视听结合的艺术特色,正与电影的艺术理论不谋而合。在电影的视听理论中,声画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类:声画同步与声画分离。唐诗中的声画关系,恰与此相类。
首先是声画同步。声画同步表现为声音和画面的形象、情绪色彩的一致。在电影拍摄中,导演经常通过“声画同步”的技巧塑造电影的意境。如日本电影《情书》,电影开头以一段轻柔而悲伤的音乐伴随女主角,在茫茫雪原中漫步。女主角在镜头中渐行渐远,音乐声也逐渐消失。雪景、孤独的背影、伤感的钢琴音,视觉感受与听觉感受达成了和谐的统一。唐诗中,也有雪景与声音的音画同步建构,如“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两句描写在风雪交加的夜里,羁旅归家的游子踏雪而行,四周皆静,凸显出声声犬吠与归家的身影,凄凉落寞的意境便在声画同步中油然而生。
此外,乐器之声与画面的配合也是唐诗声画同步的表现形式之一。白居易的《琵琶行》就是体现声画同步的典范之作,“浔阳江头夜送客”的离别愁绪与江上传来的悠扬琵琶声相交映,加重了诗人的伤感情绪,于是“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悲切之境也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同样,蝉声、雨声等自然之声也是唐诗塑造声画同步协调意境的经典声像。杜甫写“何限依山木,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树木葱茏的古寺中响起阵阵蝉声,蝉声之中飞鸟划过寒塘,自然之趣在自然之声中彰显。李群玉写 “春灯含思静相伴,夜雨滴愁更向深”(《长沙紫极宫雨夜愁坐》),寒夜之中,紫极宫中一盏春灯摇曳,诗人独坐拥衾的画面与滴答作响的雨声同步出现,苦寒清冷之境便随之而来。
由于形式的限制,唐诗中不可能出现电影的音乐配音,但是唐诗却通过对动物、乐器、自然界之声的描写营造出类似电影声画配合的效果。
其次,声画分离也常在唐诗中出现。声画分离指的是影视作品画面中的声音和图像相互分离的情况,这种关系中的声音基本是通过画外音的形式呈现的。如电影《半生缘》中,当祝鸿才与顾曼桢抛下恩怨,为了孩子重新组成家庭时,导演把镜头对准了他们琐碎且温馨的日常生活,餐桌上是丈夫留下的早餐,清晨的阳光洒满卧室。此刻,电影画外音徐徐响起:“要永远爱一个人,跟永远恨一个人,是同样困难的。”导演借助画外音,潜入角色内心,展现人物心理,暗传哲理思考。唐诗之中的“画外音”基本上是作者之声。例如杜甫的《新安吏》,全诗描写了作者行至新安县,目睹征兵的故事,当“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的人间惨剧在诗中展现之后,诗人随即配上画外音:“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诗人以旁观者透视这出征兵的悲剧,一句劝慰更添无奈。
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声画分离的情况也常有出现。例如《太行路》借夫妇之爱写君臣不终,诗人极力叙写色衰爱弛,不论妻子如何梳妆也无法赢回丈夫的心。当读者与妻子的哀怨强烈共鸣之际,画外音响起:“行路难,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在前诗对妻子之苦的极尽叙写下,“人生莫作妇人身”的劝诫就更具说服力。同时,该句与后文“近代君臣亦如此”的主旨相呼应,为诗歌增添浓郁的政治意味。《五弦弹》描写琵琶演奏家赵壁的高超技艺,诗中亦有画外音:“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作者之声以画外音的形式展现,将恶郑之夺雅,赞正始之音的意图尽然显露。在叙事画面之外,诗人之声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构成声画分离的现象,大大增强诗歌“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劝诫功能。
声音与画面的配合是唐诗中常出现的艺术手法。唐诗以意境营造见长,“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浑融的意境应当是情、景、声的三位一体。可见早在唐代,诗歌中就出现了诗人不自觉的“电影化想象”。
二、时空意识:时空交错间的独特诗境
时空综合是电影艺术的根本特征,以摄影为基础的放映技术将银幕形象展现给观众,银幕形象包含着时空综合的四度空间性。诗歌无法像电影一样构建银幕造型,但是经过诗人的妙笔书写,文字也能够搭建起想象的空间,让时间在诗句中流淌,形成时空交融的效果。因此,本文所说的“时空意识”是在传统电影思维之时空综合概念上的延伸,其内涵是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在诗歌中的想象化运用。
电影本身是时间与空间组合的艺术,电影将时间与空间组合使用,能够达到互相作用之和大于整体的效果。汤姆·提克威是电影界中最善于拼接错位时空的导演之一,他的代表作《罗拉快跑》如一场时空交错间的绚烂游戏。电影将“罗拉拯救男友”的故事置于三段重复的叙事之中,二十分钟的故事时间内罗拉在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中展开营救。错位的时空扩展了承载信息的容量,大量的信息在短暂的叙事时间内向读者涌来,牢牢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形成独特的快节奏审美感受。
中国古代虽没有提出明确的时空理论或范畴,但文学作品却有强烈的表现。唐诗中常常有时空倒错、跳跃的书写。李商隐的诗以雾里看花的朦胧美感著称,其诗歌中跳跃的时空叙述是形成这一特点的重要原因。如《夜雨寄北》一诗短短28个字内就包含了三次时空的跳跃:首先,“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两句,昔日友人(一说妻子)提笔盼问归期的画面与此刻凄凉的雨中巴山在同一联诗中展开,诗人轻轻一笔就带出了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流动;其次,“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两句是未来与当下的对比书写,“何当”是诗人对未来能与友人共剪烛火的期望,“却话”转而落到现实的时空之中,期盼中温情与现实的冰冷形成强烈的对照,将思而不得见的心情推向顶峰。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再从未来到现在,利用三次反复横跳的时空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起单一的线性叙事,交错的非线性的结构让原本凝滞于同一平面内的意象、事象在时空拼接内流动起来,如同电影快速切换的镜头,既丰富了承载的叙事信息,又加快了叙事节奏。
除了时空快速切换的艺术技巧,“融化的时空交错对举”这一时空综合方式也在唐诗中有所体现。杜甫《登高》是时空交错对举的经典之作。前半段写“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对当时之景的描述,诗人目之所及是江边肃杀秋景。后一联宕开一笔抒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既是对自身遭际的感叹,也是“百年”来文人的普遍命运。诗人笔势大开大合,将当下时空与百年历史长河并举,诗歌境界豁然开阔。杜甫长于律诗,律诗的平仄对仗往往导致时间意象与空间意象相伴相随,时空渗透融合,形成四维度的时空结构。
唐诗中出现时空综合的现象并非偶然。唐诗讲求意境,“意象”是构成意境的关键要素。莫砺锋教授在《论唐诗意象的密度》一文中指出:“正因为古典诗歌篇幅相当有限,而作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承载更多的意蕴,所以不能容忍芜辞赘句的存在。”当诗歌中堆砌的意象越来越密集,诗人一不小心就会失去把握意象疏密有致的分寸。如何既保持足够的意象密度,但又不流于板滞呢?这时候,时空综合的艺术手法就能帮助诗人走出困境。时空的交错相融,从物理层面上扩大了诗歌的容量,再将密集的意象置于其中,就不会显得逼仄拥挤。比如王勃的“杏阁披青磴,雕台控紫岑”(《游梵宇三觉寺》)与李商隐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相比,同样是两句四组意象,但王勃之诗囿于同一时空之内,李商隐则跳出平面时空,在虚实相生的交错时空里铺开意象,诗境也随之变得阔大邈远。
由此看来,时空综合的电影思维与唐诗中时空交错的艺术手法确有共通之处。诗歌虽无法以直观的形象感人,但是诗歌中的文字经诗人精妙排布,一样能够打破时空界限,穿越古今,在构建的想象时空宇宙中调动观者的情感。
三、镜头运用:长镜头中的“凝视”艺术
镜头语言是电影主要的表达方式。长镜头是电影艺术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和流动性。长镜头作为电影的一个视点,具有“凝视”的功能,好像创作者是站在摄影机的后面平视生活、人物、人生,表达一种平和冷静的观察。
在电影艺术中,长镜头分为固定长镜头和运动长镜头两种。固定长镜头是指机位固定不动、连续拍摄一个场面所形成的镜头。由于机位的固定,镜头中的凝视视点不会变化。李白的《长干行》就运用了一组以商妇视角为支点的固定长镜头,如“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若将其转化为电影机位,即是少年骑着竹马徐徐而来,二人绕着井栏,互掷青梅为乐。当这组以固定视角展开的长镜头作为被看客体落入读者之眼时,“看与被看”的交互关系就产生了,少女的“凝视”为这个两小无猜的故事奠定下纯净浪漫的基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是王国维对古典诗歌中“有我之境”的论述,西方的“凝视”理论在诗歌解读上的运用恰与此相类。
除了单纯美好的“我之色彩”,以固定长镜头中的视点展现百姓悲惨境遇的唐诗也不在少数。白居易《新乐府》中,《杜陵叟》以农夫视点看横征暴敛的酷吏,《母别子》则巧妙地设计了“母亲”这个视点,以固定长镜头展现了将军娶新妇的一系列画面,以喜衬悲,抒写了骨肉分离的悲痛。白居易之前,杜甫“三吏三别”中几乎每首诗都运用了固定长镜头。《新安吏》以“客”的视角看征兵的残酷,“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在残忍的征兵制度之下,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兵力。以“客”为视点的固定长镜头充满凝视意味,“客行新安吏,喧呼闻点兵”,客者只是路过,毫无人情的官吏、与家人生死离别的壮丁,征兵的景象却接连落入他的眼中,从侧面反映征兵的惨剧在那个时代常有发生。《无家别》以“回乡老兵”视点看飘零的故乡,“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老兵的凝视让这组长镜头更添萧条凄惨的氛围,兵败归家,故乡却已成空巷。战争不仅摧残个人的身体健康,连精神支柱也一并摧毁,在固定视角的呈现下,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显得真实又无奈。杜甫之诗被称为“诗史”,他笔下的人物好像用眼睛充当着摄像机,记录下当时的社会图景。在杜甫诗中,固定长镜头的运用以不同身份人物的视点展开,以真实的细节补足历史的空白,也让读者感同身受。
此外,运动长镜头在唐诗中也有所运用。运动长镜头是指摄影机用推、拉、摇、移、跟等运动拍摄的方法形成多景别、多拍摄角度(方位、高度)变化的长镜头。运动长镜头中的视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视点的切换往往会带来双重的凝视意味。例如骆宾王《畴昔篇》的前半段就是以运动长镜头建构的。首先,长镜头以少年的视角作为观察点,“遨游灞水曲,风月洛城端……掩映飞轩乘落照,参差步障引朝霞”极力铺陈年少时意气风发的生活。随后,镜头变化角度,以壮志未酬的中年人的凝视展开“意气风云倏如昨,岁月春秋屡回薄。上苑频经柳絮飞,中园几见梅花落。当时门客今何在,畴昔交朋已疏索”,昔日繁华已落幕,此地空余飘零的残梅,读者的视线随着视点转移而变化,凝视的意味就呼之欲出了:少年既是看者又是被看者,少年的目光给这首诗的长镜头增添了强烈的主观意味,以少年之眼观物,则所看之物尽着蓬勃的意气。而当诗歌以中年人视点去看时,少年人眼中的景物也被“嵌套”进这组长镜头之中,少年时富丽自由的生活,在中年人的凝视下更添一层年华已逝的伤感情绪。少年时意气风发,中年时落寞失意,通过长镜头中的视点变化,诗人揭示了真实、普遍的自然规律。长镜头带来的凝视意味,也传达出中年人对时光流逝的真实感叹。
唐诗中不仅有以看者身份变化构成的多角度运动长镜头,还有以视点推拉变化构成的运动长镜头。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就是典型的例子,“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以一个全景镜头写早春时节纷纷细雨中的长安街道,雨雾迷蒙了视线,远远望去,初萌的小草连成一片朦胧的绿。随即诗人又拉近了镜头,近景之下原本盎然的绿意竟成了稀疏零星的几点。诗人对小草的凝视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这组长镜头的流动过程也符合人的行为逻辑:远看时朦胧一片,想要凑近了细细赏玩却发现生机勃勃的绿变成零零星星的几根小草。当读者的目光随着诗人视线的运动轨迹变化,诗人旺盛的探索欲与愉悦的心情便与读者产生了共鸣。
传统电影与传统诗歌一样,往往采用全知全能的方式叙事或抒情。这带给了观众理性思考的空间,以呈现(showing)而不是讲述(telling)的方式隐藏起叙事行为和符码痕迹,无形间在读者与故事间建造起“第四堵墙”。而以凝视视角出现的长镜头,则打破了“第四堵墙”,以情感的共鸣连接起看者与被看者的双向互动。
四、文化增殖:古典诗歌的现代性光彩
唐诗彰显着中国古典文化的不朽魅力,令人惋惜的是,古典诗歌在现代语境下始终面临着“小众化”的困境,因此,如何让古典诗歌焕发现代光彩是学界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电影是大众化、通俗化的文艺形式,古典诗歌可以借助这种艺术形式获得更广泛的传播。目前,诸如《长安三万里》等呈现古典诗歌魅力的电影,已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热点,这足以证明将电影与古典诗歌结合是可行的。唐诗在视听综合、时空意识、镜头运用三方面都与电影思维有着相通之处。诗歌借助电影可以实现文化增殖。
首先,电影带来的文化增殖将会扩大古典诗歌的接受群体。作为一种聚合性媒介,电影本身就有着“合家欢”式的接受群体。当古诗与电影结合,古典文化构建的桥梁连接起所有观众,古诗就成了群体欣赏的对象。不仅如此,电影运用视听艺术将复杂的文化背景融入文化故事,带给观众直观呈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古典诗歌的难解性。例如追光团队等电影制作团体巧妙地利用“动画电影”这一形式,让承载古典文化的电影呈现出“强类型、重感情、年轻向”的特点,诗歌接受群体也随之变得年轻化。
其次,诗歌与电影的结合能让外国民众了解到中国诗词的魅力,使中国诗词走向世界。诗歌的传播有赖于传诵与阅读,语言文化的差异是古诗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难题之一。电影与诗歌的结合,使纸面上的文字变得可视化,直观的形象更便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古诗爱好者感受诗歌魅力。迪士尼以民间乐府诗《木兰辞》为蓝本改编的电影《花木兰》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自1998年上映以来,《花木兰》一直深受各国观众的喜爱,迪士尼更将电影中的木兰作为经典形象,打造成与“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一样的中国籍“公主”。
再次,电影为中国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成功的电影改编能够赋予古典诗词新的时代内涵,引发新的探讨交流热潮。以《长安三万里》为例,电影以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诗人的交往为线索,展现了盛唐时期的文化气象、文人气度。其中,少年杜甫的形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杜甫一直以忧国忧民的形象为大家熟知,但是《长安三万里》却塑造了一位活泼可爱、热情开朗的少年杜甫。形象认知的差异带来了反思,杜甫早年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成为最近的热点话题。
五、结语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当大工业化时代到来,古典艺术的“光晕”便会随之消失。然而,笔者认为,古典艺术的光晕始终以自己的姿态照耀着现代技术。诗歌叙事与电影叙事相似的根本原因是人之思维模式的相似性。机械艺术本质上仍然是人的艺术,人的思维光晕不会因为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而消解。
20世纪20年代以来,“诗电影”成为先锋电影的代名词。法国电影先锋派认为,电影应该像诗歌一样,发挥表意和抒情的双重功能。彼时,诗歌为电影提供了形式的创新,完成了电影的先锋性转向。21世纪,古诗元素在中国电影中频频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构成了内容上的“诗电影”。诗歌不仅带给电影内容上的创新,也为电影注入了中国文化内涵,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构建电影体系中的中国价值。诗歌中的“电影思维”是古典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相互交融,是跨越时代的思维光晕的融合。
参考文献
[1] 孙晶. 跨越文字与影像的疆域[D]. 长春:吉林大学,2011.
[2] 林年同. 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有关古典美学问题的探讨[J]. 当代电影,1984(2).
[3] 韩世华. 论电影思维[J]. 中山大学学报,1995(2).
[4] 郭波. 论唐诗的声音艺术形象[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2).
[5] 魏陆. 论声画关系对电影意境的建构作用[J]. 大众文艺,2020(14).
[6] 周远哲. 电影声画关系与审美体验[J]. 传播力研究,2018(19).
[7] 吴丽斌. 影视艺术中的声画关系浅析[J]. 东南传播,2014(11).
[8] 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四库唐人文集丛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9]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李易. 浅论导演思维[J]. 电影文学,2011(9).
[11] 赵原. 克里斯托佛·诺兰电影时空叙事研究[D]. 浙江大学,2020.
[12] 杜松梅. 论杜诗中的时空艺术[J]. 唐都学刊,2022(2).
[13] 李浩. 论唐诗中的时空观念[J]. 唐代文学研究,1993.
[14] 莫砺锋. 论唐诗意象的密度[J]. 学术月刊,2010(11).
[15] 王阳. 电影镜头语言与情感表达深层探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5.
[16] 陈旭光,李雨谏.“长镜头”的“似”与“非”:语言、美学与文化——侯孝贤与贾樟柯比较论[J]. 电影新作,2013(2).
[17] 王国维. 王国维全集·人间词话·三[M]. 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
[18] 朱立国. 影视作品“凝视”的美学特征及视点差异[J].电影评介,2010(16).
[19] 陈超清. 中国元素在追光动画系列作品中的应用研究[D]. 南昌:南昌大学,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