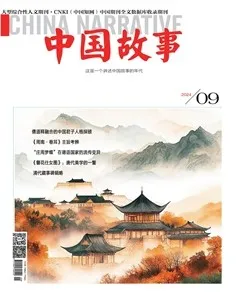北魏云冈石窟造像:农牧文明交融下的艺术典范
【导读】云冈石窟蕴含着印度佛教文化、鲜卑游牧文化和中原汉文化,是一座反映北魏时期各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丰碑。云冈石窟因建造、形制与风格不同,可分为三期。早期石窟造像有鲜卑游牧民族和古印度佛教的文化特色;中期石窟造像中鲜卑文化与汉文化高度交融;晚期石窟多由民间出资建造,体现了世俗化的特点。云冈石窟造像艺术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寺遗址。开凿时间长达60多年,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一直持续至孝明帝正光年间。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云冈石窟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史。早期石窟以昙曜五窟为代表,造像既有鲜卑游牧文化特色,又有印度佛教文化色彩。中期石窟受孝文帝汉化改革影响,造像艺术体现了汉化之风。晚期石窟多为中小窟,佛像容貌清秀,举止潇洒飘逸,体现了世俗化的特点。从云冈三期工程看,云冈石窟造像是北魏时期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交融的重要见证,更是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迁移的例证。本文在梳理云冈石窟建造背景、造像演变进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云冈石窟造像演变的成因及蕴含的农牧文化交融之风。
一、云冈石窟的建造背景与概况
(一)云冈石窟的建造背景
佛教发展是北魏建造云冈石窟的直接原因。史载:“魏先建国于玄朔,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拓跋鲜卑初期因地理位置偏北,与西域等国未有接触,真正接触佛教文化是在“至神元与魏、晋通聘……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定都平城后,北魏统治阶层开始接触佛教,并借佛教维护统治。北魏高僧宣扬:“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皇帝即如来”的主张迎合了当时统治者的需求,也调和了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与中华文化的矛盾,为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北凉佛教东传后,平城地区僧人集聚,北魏佛教迎来了发展高潮,但佛教盛行导致寺院经济膨胀,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太武帝发动灭佛事件,“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然毁之愈烈,求之弥切,文成帝拓跋濬为政治需要,也为太武帝灭佛行为做出忏悔,下令恢复佛教,建造云冈石窟。
北魏徙民政策为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技术保障。北魏迁都平城时,平城地区经济萧条、人烟稀少,为巩固政权并加强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统治者开始推行徙民政策,“迁山东六州的人民、高丽杂役三十六万人”,将大量僧人与工匠汇聚平城,迁河北技工约十万人,在平城兴建寺院,开设讲堂,使北方佛教势力与造像力量集于一处,为平城佛教文化的传播奠定基础。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将三万凉州吏民迁至平城。河西佛教整体迁徙平城,中华佛教中心也由凉州转移至平城。中原与西域联系日渐紧密,西域各国纷纷遣使北魏,开通了西域佛教文化东传道路。平城地区汇聚了各国能工巧匠、佛教高僧,曾参与敦煌莫高窟修建的凉州僧匠,为云冈石窟的开凿提供技术支持,成为云冈石窟建造的主要力量。
(二)云冈石窟概况
云冈石窟早期的重要代表为“昙曜五窟”。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采纳佛教高僧昙曜的建议,在京城西的“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具体开凿时间为公元460—465年,五座主佛造像分别对应北魏的五位皇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将佛与帝合而为一。昙曜五窟位于云冈石窟西部,是编号第16、17、18、19、20的五个窟,自东向西依次排开,气势磅礴,规模宏大,东西绵延约120米。昙曜五窟佛像造像带有印度佛教的印记,大佛身着宽大厚重的袈裟,模拟的材质似毛纺织品,体现了龟兹、印度与希腊的文化特色,同时保留了鲜卑族自身的游牧风格。
云冈石窟中期是北魏皇家开窟的鼎盛时期,也是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高峰期。开凿时间为465—494年,代表性石窟有雕凿于东部的1-3窟和中部窟群5-13窟。石窟造像展示了主佛释迦牟尼由出生至涅槃的整个过程。石窟建造风格既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又表现出汉族审美意识。造像风格与雕刻手法显现出程式化倾向。造像设计健硕美观,内在的刚毅个性却逐渐丧失,佛像面容不似之前庞大严肃,而是清秀儒雅、面容适中,雕琢精细。公元486年,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受魏晋玄学之风影响,中期佛像出现了汉族“褒衣博带”的服饰形式,直接影响了后来龙门石窟的造像风格。
云冈晚期石窟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时间在公元494—524年,主要分布于第20窟以西地区。北魏统治集团南迁后,平城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但依旧为佛教文化中心,石窟开凿主力为留守平城的贵族、中下层官吏信众以及北上的徐州僧匠。石窟中大型洞窟开凿数量减少,中小型石窟开凿数量增加,西部山崖成为民间造像的乐土。晚期石窟作为云冈石窟修建的尾声,再未出现像早中期的大像窟,开凿规模大不如前,早期佛教文化“改梵为夏”的历史进程就此完结。值得注意的是晚期石窟雕饰比中期更加丰富精美、清秀脱俗,整体上比较规整,窟顶样式也比早中期更加多样。
二、云冈石窟造像演变的进程
(一)云冈石窟造像的早期形成
云冈石窟早期造像服饰多为袒右肩式和通肩式。袒右肩是印度佛教礼佛礼仪。第17窟主尊为交脚弥勒佛,头顶戴冠,袒露胳膊,服饰为袒右肩式样,左肩上斜披带有雕饰的络腋,右边可见佩戴项链,左边被衣服遮挡,两边各佩戴一条似龙莽兽形的胸带。这类双龙装饰是北魏较为常见的习俗。第18窟正壁上方有十尊比丘,即主尊佛像的十个弟子,相貌特征颇具异域风格。第20窟整体风格偏向印度犍陀罗式,主尊佛释迦牟尼佛像高大雄伟,服饰为袒右肩袈裟,右肩搭有偏衫,面容庄严肃穆,神态坚毅有力,身躯挺拔壮硕,肩膀宽厚挺拔,透露出“胡貌梵像”的特点,展现了鲜卑游牧民族强壮剽悍的尚武之风。
云冈早期洞窟有西凉乐舞的遗迹。北魏强迁十万凉州民众至平城,许多凉州僧匠参与了云冈石窟的建造,将凉州乐舞风格遗留在云冈石窟。第16窟为娴雅婉约的西凉风格。洞窟南壁上方雕刻有乐伎,这是云冈石窟中最早有伎乐雕刻的洞窟。乐伎手持横笛、筚篥、琵琶、胡笳、箜篌、齐鼓等乐器,齐声演奏宫商乐舞,南壁上方雕刻的舞人双手插胯、形体强健、上身袒露、舞姿迷人,有浓重的西域之风。第20窟墙壁上雕刻的“飞天”形象可见许多外来因素,其体态丰腴且丝带飞扬,手臂佩戴钏镯,头戴花蔓宝冠,颇有古印度贵族的装饰风格,体现了北魏工匠对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借鉴。
(二)云冈石窟造像的中期融合
云冈中期石窟造像逐渐汉化,佛像服饰由早期“袒右肩”式转为中晚期“褒衣博带”式。具体表现在佛像服饰从厚重的毛织物变为轻柔的丝绸,由“袒右肩”变为宽博飘展、双领下垂,接近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带”的风格。太和年间,石窟造像受江南顾恺之和陆探微影响,佛像面容由早期威严肃穆转向清秀慈祥,整体造型转向儒雅精致,不似之前雄伟庞大。中期出现了“龙图腾”,第6窟南壁上刻画的龙图腾面部表情生动,造型为龙首反顾;北壁上龙与天人的组合画面极富生机。“龙图案”表明了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成功,又凸显了云冈石窟作为皇家洞窟的超然地位。石窟造像的演变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交融,也反映了鲜卑族加速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
云冈石窟中期乐舞雕刻数量有所增加。第12窟被称为音乐窟,是保留北魏音乐资料最丰富的一座窟,有着丰富的乐伎形象和乐器形式,窟中展现伎乐演奏的乐器既有汉族传统的琵琶、横笛、筝、古琴等,也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胡琴、胡笳等,体现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乐舞文化的交融。云冈中期“飞天”形象的外来因素有所淡化,窟中雕刻的飞天形象与西方的天使形象不同,主要靠展开的裙裾和肩上的飘带,给人以回翔飘逸、迎风飞舞之感。中期飞天形象是北魏工匠借鉴印度佛教文化造像艺术,进一步升华的产物。云冈中期石窟造像蕴含的元素反映了北魏时期西域文化、鲜卑文化、汉文化等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融。
(三)云冈石窟造像的后期汉化
云冈晚期孝文帝迁都洛阳,皇家工程基本结束。晚期石窟主要由北魏民间开凿,风格逐渐本土化和世俗化,造像面容风格呈现瘦骨清像、褒衣博带的模样,外来文化完全淡化。晚期石窟整体上造像不再如早中期一般雍容尔雅,题材更加简单,模式化倾向突出。菩萨造像多有帔帛交叉,服饰褶纹繁复重叠,造型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传统的神仙模样。云冈晚期石窟具有清新典雅的艺术表现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龙门石窟中的宾阳三洞,并逐渐成为南北方统一的技艺风格。
云冈晚期石窟佛教造像经历了由“胡貌梵相”至“改梵为夏”的演变,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融入汉族的世俗生活,更贴近百姓日常生活,这也有民间开凿的原因。北魏时期,百姓容纳百川的性格促进了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交融,这一时期石窟造像风格在借鉴外来技术的基础上有新变化。晚期石窟中乐舞雕刻风格更自由洒脱不受约束,第38窟背壁上雕有表演“倒挂”“鸟飞”动作的伎乐图;北壁上雕凿有“爬杆倒舞”的浮雕图。这一民间百戏浮雕图,是云冈石窟后期雕刻风格世俗化的重要体现,是北魏工匠根据本民族文化特色所创作出的艺术佳品。
三、云冈石窟造像演变的成因探讨
(一)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
云冈石窟造像艺术是在东西文化、农牧文化和南北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兴起的。石窟工匠多来自凉州和中原,凉州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互鉴,共同创造了不同于凉州石窟的新样式,即“云冈模式”。张绰先生曾言:“云冈石窟初期造像的粉本,主要来源于西域诸国。”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西域诸国纷纷与之交好,西域商人和佛教僧人在平城汇聚,石窟艺术经新疆,到河西、关陇地区,至平城而兴盛。北魏文成帝任命的佛教领袖师贤、高僧昙曜均来自西域。早期昙曜五窟由昙曜主持修建,造像风格自然会有西域样式。云冈石窟除西域佛教文化特色外,还可见鲜卑游牧文化的痕迹。拓跋鲜卑早中期以游牧和畜牧为主,到中晚期逐渐转为以农耕为主。云冈石窟造像蕴含了草原文明特征,如其中身着鲜卑族服饰的供养人,面容、纹饰都有明显的鲜卑特色,这说明当时社会已经习惯游牧文化的鲜卑服饰。
北魏在文明太后冯氏和孝文帝执政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政策以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孝文帝亲政后,为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积极与南朝互动,促进南北方交流,南方文化逐渐成为北魏社会文化的主流。佛像造像由昙曜五窟时期佛陀形象的王者形象转向“痩骨清像”;造像服饰变为双领下垂式袈裟,特征为胸束博带、系结下垂、下摆向外展开,即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服饰样式;石窟中的供养人造像转变为汉族士人形象,造像服饰由鲜卑族服饰转为汉族服饰,还出现了“龙图腾文化”。北魏政权推行的汉化措施,对云冈石窟造像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使造像艺术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
(二)信仰观念的交融与碰撞
北魏时期的思想文化没有独尊儒术的禁锢,在崇尚佛教的同时,与儒教和道教的渊源同样深厚。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后,接受佛教文化并开凿石窟,将西域文化、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共同汇聚于石窟建设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贡献,使中华文明更加包容与多元。云冈中前期佛像造像风格主要受印度、敦煌与龟兹之风影响,自身风格并不突出。其与中原文化交融后其风格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中原道教文化使石窟造像艺术别具一格。汉代道教就有对自然与生命的思考,北魏时期“崇奉天师,宣扬道教,传布天下,道业大行”,甚至出现了道教神仙体系。这些反映在石窟中,主要表现为云冈“飞天”样式的变化。早期“飞天”头后有圆光,戴王冠,身材短粗,神情庄严,俯视众生;后期“飞天”身形清瘦,轻柔飘逸,塑造了道家仙风道骨的飞仙形象,蕴含着对长生的渴望、对美好和谐的期盼。
北魏统治者借佛教维护统治,使传统儒家文化受到冲击,但北魏社会仍深受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尚儒崇佛是当时的主流。在此背景下,云冈石窟造像也兼顾了儒教和佛教文化。作为北魏皇家主持修建的大型工程,云冈石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石窟造像风格大都“雅丽精致、至正大气”,尽显皇家风范。云冈早期受犍陀罗文化和鲜卑游牧之风影响,石窟造像高大庄严、至正肃穆,带有俯看众生的神圣之感,造像服饰是印度风格的袒右肩。云冈中期正值北魏汉化改革,石窟造像汉化特征明显,佛像面容由早期的庄严肃穆转向清秀慈祥,形态更加丰富飘逸,造像服饰由印度风格的袒右肩转向汉族风格的通肩、褒衣博带,凸显了封建礼制文化的规范性,是儒家礼制文化在石窟造像中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更是鲜卑民族的形象史碑。造像艺术受长期以来多元文化交融的影响,既有西域文化的印记,又有鲜卑游牧文化和中原汉文化的特色。云冈石窟不仅为研究宗教、历史、乐舞以及雕刻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更是追溯北魏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物佐证。
参考文献
[1] 彭栓红. 云冈石窟造像的鲜卑特色与文化多样性[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2]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杨伟笑. 北魏平城时期鲜卑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研究[D]. 成都:西南民族大学,2022.
[4] 何兹全,张国安. 魏晋南北朝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 刘芳. 试论北魏佛教服饰的世俗化表现——以云冈石窟为中心[J]. 美术大观,2019(12).
[6] 李娟.云冈石窟器乐图像考述[D]. 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6.
[7] 杨洋. 从云冈石窟造像看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4).
[8] 范鸿武. 云冈石窟建筑与佛教雕塑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2012.
[9] 赵萌. 云冈石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J]. 晋阳学刊,2022(4).
[10] 青岛出版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 云冈石窟全集[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
[11] 刘小旦. 北魏云冈石窟艺术发展源流探析[J]. 晋中学院学报,2020(5).
[12] 寇福明. 云冈石窟蕴含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意识[J].民族学刊,2023(7).
[13] 张月琴,李文慧. 云冈石窟的域外艺术特征探微[J]. 云冈研究,20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