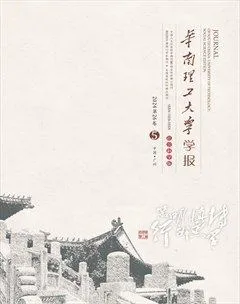数字秩序:数字社会的新型秩序形态
摘 要: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社会秩序的维系,“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数字技术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形塑了数字社会这种新型社会形态,而如何认识和理解“数字秩序何以可能”就成为社会学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概念层面,数字秩序是因应数字社会衍生的新型秩序形态,是数字社会、数字空间、数字生活能够聚集联结的基础。数字空间是数字秩序的运作基础,数字交往是数字秩序的实践基础,数字关系是数字秩序的传递基础,数字规范是数字秩序的逻辑基础。在特征层面,数字秩序是有序性与无序性、流动性与静态性、自由性与规训性以及虚拟性与现实性的辩证耦合统一。在类型层面,数字秩序包含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权力型秩序、以数字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型秩序、以数字资本为基础的资本型秩序、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主体型秩序。在价值层面,数字秩序对确保数字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数字生活需要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秩序;数字社会;概念阐释;特征类型;意义价值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24)05-0148-09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24.05.013
收稿日期:2023-12-18
基金项目: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19JJD840003)。
作者简介:管其平(1993—),男,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
一、引 言
社会学自诞生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深刻复杂的研究范式和多元辩证的理论体系。无论是主张用自然科学方式阐释社会运行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还是尝试以人文科学方式理解社会行动意义的人本主义社会学,抑或用唯物辩证方式寻求人类自由解放的批判社会学,均认为社会学自诞生之初的使命就是对工业技术引发的社会危机进行深刻地反思和批判,并思考如何确立工业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型秩序。社会秩序在最根本层面上代表着人类社会运行的稳定性和方向性以及社会生活的连续性和确定性。进而言之,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既是社会学兴起的重要缘由,又是社会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因此,探寻社会秩序如何恢复、重建及其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学家不懈追求的问题。正如亚历山大所言:“正是个体的自主性使‘秩序’成为问题。正是这种秩序问题使得社会学成为可能。”[1]9
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任何社会形态都为自己铸造了适宜的社会秩序。反过来讲,社会的现代化存在于稳定且特定的秩序中,并表现为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进而言之,要认识和理解一种社会形态就必须认识隐藏在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秩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认识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生活。“现代性自称为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合理形式,却是建立在被合理地设计的技术人造物和由合理的技术规训所赋予的制度基础之上。”[2]ix时至今日,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中观层面的数字生活以及微观层面的数字交往均发生数字转向之时,数字秩序就成为认识和理解数字社会的重要切入点。确切地说,数字社会越发展,数字生活越普及,数字交往越理性,对数字秩序的要求也就愈迫切。显然,社会学必须回答数字社会的“数字秩序何以可能”这一核心问题。本文尝试借鉴传统社会学对社会秩序的研究,对数字秩序“为何”“是何”以及“何用”的元问题展开探讨,进而展示数字秩序作为新型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二、数字秩序的理论追问
“数字秩序何以可能”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延伸、拓展和深化。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的探讨既是佐证数字秩序之所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亦是阐释数字秩序有异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现实基础。进而言之,我们不能脱离传统社会秩序抽象谈论数字秩序,而须通过对社会秩序何以构成、何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来追问和回答数字秩序凭什么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一)数字秩序是否必要
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础,如何建构社会秩序就成为任何一种新型社会出现之时首先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越高,社会分工越精细,社会群体越庞大,社会生活越个性化,人类对社会秩序的需求也就越强烈。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将社会秩序视为如同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的社会联系,并指出:“秩序是进步的基本条件,所有的进步最终都趋向于巩固秩序。”[3]37立足非理性实证主义,社会秩序等同于社会变迁,社会秩序是处于变迁中的秩序,而社会变迁也意味着秩序的变迁[4]。实质上,每种社会组织形态中都拥有一定未经刻意创造的情况下存在的秩序形态与之相匹配[5]7。凡是在人类建立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都积极确立了适合社会生产生活的社会秩序形式,以防止混乱现象的发生。相较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数字社会具有新的空间场域、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社会分工以及新的主体属性,原有的社会秩序形态难以契合新的社会组织形态,自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秩序来维系数字化的生产和生活。与此同时,数字社会本身是原先社会秩序受数字化影响而变迁形成的必然结果。数字社会是按照数字秩序组织起来,按照数字秩序运行的新型社会组织系统。如是而言,数字秩序之于数字社会是必要且必需的,其既彰显数字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标识数字生活的主体性和确定性。
(二)数字秩序是否可能
对于社会秩序是否可能的问题,社会学家们是以社会是否真实存在为前提开展讨论的。社会唯名论主张社会只是单纯的名称,真正存在的是真实的社会个体,强调社会秩序仅仅是社会成员依靠概念性思维和语言符号生成的主观意象。而社会唯实论主张社会是由各种制度和规范构成的有机整体,强调社会秩序普遍存在且不可被还原为个体意志[6]55。在此语境中,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的探讨可分为社会冲突论、社会互动论和社会结构论三种主要视角。具体来说,社会冲突论主张社会冲突是社会系统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并非仅具有分裂社会团结的破坏性功能,事实上还能促进社会重组、社会变迁并增强社会的适应性。“社会始终处于变迁之中,又普遍存在着对立和冲突;社会冲突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中每一个要素都可能引发冲突、变迁甚至社会解体”[7]198。社会数字化过程也是传统社会资源在数字空间中重新分配和调整的过程。一般来说,地方性生活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往往具有较强接受并学习数字知识的意识和能力;而身处较低社会地位的个体、群体和组织接受并学习数字知识的意识和能力较低,难以掌握重要的数字资源。显然,数字化将在场弱势群体间接转化为缺场弱势群体,存在引发矛盾和冲突的可能,因此产生了数字秩序需要。社会互动论主张社会秩序是社会成员交往中形成的一系列潜意识规范[8]135。数字社会的社会交往是社会成员借助数字空间在非共同空间中开展的数字交往。社会成员在长期交往中会形成被其潜意识所认同并内化为自身生活规范的一系列秩序意识,并用以指导数字实践。社会结构论强调秩序源于组成社会系统的各部分在发挥各自功能过程中的耦合。事实上,结构也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内在秩序[9]5。进而言之,社会秩序是社会结构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数字社会由不同数字系统按照特定逻辑整合而成,各部分之间的稳定状态亦需稳定的社会秩序予以保障。
(三)数字秩序何以实现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秩序是人们在集体活动中形成的共有集体观念,是被社会群体所共同遵守的一系列社会规范。当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受到侵犯时,集体表象会以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引导、牵制和限定个体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意志。情感既是社会秩序的对象,又是社会秩序的形成因素[10]。鲍曼将文化视为由权威认可的压力、内化的价值观和规范以及习惯所组成的系统,并考察了文化试图生产与维持秩序的事实[11]12-13。传统社会秩序形式除了包含感性的集体表象,还包含权威的集体表象。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家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具有阶级性和权威性的法律法规。接续思之,数字秩序既可以是国家颁布实施的强制性法律法规,也可以是被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内在的、非强制性的道德规范。现实中,数字秩序是法律、制度等权威性强制规范以及道德、伦理等非强制性规范的耦合。
三、数字秩序的内涵阐释
数字秩序是社会成员开展数字交往、拓展数字关系遵循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的总称,是人、媒介与社会在数字时空中的互嵌融合,是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是数字要素相对稳定和均衡的状态。更细致层面,数字空间是数字秩序的运作基础,数字关系是数字秩序的传递基础,数字交往是数字秩序的实践基础,数字规范是数字秩序的逻辑表现。
(一)数字空间是数字秩序的运行基础
社会是存在于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而作为黏附于社会形态的社会秩序自然也需以空间为依托。“我们首先关注的领域是物质(physical)领域,即自然、宇宙;其次是精神领域,包括逻辑与形式的抽象;第三是社会领域”[12]18。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新型空间并未脱离空间的本质内涵,始终凝聚人类思维方式、承载人类社会关系、表达人类情感意志、铭刻人类未来理想。数字空间既是建构数字社会的基本要素,又是承载数字生活的基本场域。数字社会的首要外在表征便是基于各类数字应用程序(Application,简称App)空间搭建的数字网络,没有数字空间在特定秩序中的聚集和排列,数字社会就失去了表征方式。同时,数字生活依赖于各种类型的数字App空间,没有各种差异性的数字空间,数字生活就会沦为空谈且逐渐迈向单向度。有什么样的空间形态就会建构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模式,而不同空间组织形式蕴含差异性的空间秩序[13]。数字空间形态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数字秩序,而不同主题和内容的数字空间也蕴含着不同形式的数字秩序。进一步说,无论是国家制定的强制性数字秩序,还是道德规范代表的软性数字秩序,均以技术性方式黏附于数字空间中引导数字社会的运行、规范数字生活的形式。数字空间对数字秩序的生成、维系和变革发挥着积极的建构作用。各类数字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数字秩序的延展过程;而数字秩序亦是确保数字空间生产公平正义的基础。
(二)数字交往是数字秩序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501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实践形式,而数字秩序的奥秘亦需在数字实践中得到合理认识和解释。或者说,以数字交往为形式的数字实践是考察数字秩序的逻辑起点。“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层面引发的最具革命性改变在于为人创造了新的身份,或者说创造新的交往主体。”[15]2借助数字技术,在场生物人获得了缺场数字身份,这拓宽了人类交往的广度,为人类跨时空交往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在前现代社会,受地理空间限制,人类的社会交往通常局限在其所在的地域性空间,形成强烈的地方知识和地方精神。在数字社会,人类能以数字身份并借助数字媒介持续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在更广阔的数字时空中开展数字互动,建立社会关系,丰富日常生活。数字交往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基本、普遍的交往形式。数字秩序因人们的数字交往而生成,也始终随着数字交往的变化而变化,唯有如此,才能纾解数字交往中潜在的数字冲突,促进美好数字生活的实现。总体来说,人类借助数字媒介以数字身份在数字空间展开的数字交往过程,也是人类不断生产和塑造数字秩序的过程。同时,数字秩序也是维系人际交往信任和本体性安全的重要保证。
(三)数字关系是数字秩序的传递基础
社会秩序是社会关系的属性和状态,社会关系的变迁将促使社会秩序转型。或者说,基于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秩序存在的基础,脱离社会关系的社会秩序将失去根据。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501数字关系是社会成员在数字交往中建构的基于媒介符号的新型社会关系形态,包含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成员和“智能体”之间的关系两种关系。一方面,数字生活中的交往对象首先是真实存在的,于我们而言或是熟悉的,或是半熟悉的,抑或是陌生的人。借助各类社交类数字空间,我们能够快速和身处不同地理时空的他者建立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在生活节奏加快以及高度竞争的现代社会,社会原子化和生活孤独化成为重要的社会事实。在此基础上,很多人开始和互联网集团(公司)生产和再造的各种陪聊机器人开展互动交往,寻求情感寄托,实现自我慰藉。显然,数字交往还可能和非人类性质的“个体”建立数字关系。当然,无论哪类数字关系均需数字秩序的维系,而不同数字空间的技术特性为这些数字关系的转换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成为数字秩序传递的基础。在数字生活中,社交类空间形成的关系秩序也适用于娱乐类空间,而和智能体形成的某些交往秩序也适用于人类在场交往。总体来说,数字关系的建构是数字秩序的现实化过程,且场域之间便捷转换为数字秩序传递提供了途径,而这样的数字秩序又保证了数字关系的稳定有序。
(四)数字规则是数字秩序的逻辑表现
秩序是人类保有惯常性和规律性的一种制度设计[16]57。数字时代的数字规则既包含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又包含技术精英通过程序设定而建构的各类场域规则。这些黏附在数字空间中的规则是人类进行数字生活、开展数字交往和拓展数字关系必须遵循的规则。比如,使用某种数字空间首先必须下载该类空间的App,并通过手机号注册且同意相关数字条款。在具体使用中,也须遵循技术精英预先设定的技术程序。有些App只有获取相册权限才能转发和分享相关照片,只有同意获取通讯录权限才能轻松添加可能认识的好友。久而久之,这些被技术精英生产且掌控的数字规则就成为重要的数字秩序来引导、调节和规范人类的数字实践。更重要的是,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已将这些规则发展成了社会成员的自我约束。“任何社会规范都包含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规范的形成往往伴随着旨在维护这些规范的规范。”[17]和传统在场社会规则有所差异,数字规则更多表现为具有社会性属性的技术规范和代码规范,它们既是数字空间有序生产的基础,也是开展数字生活需遵循的秩序规则。
四、数字秩序的基本特征
数字秩序作为数字社会的社会秩序形态,既具有传统社会秩序的共性,也蕴含着自身特性。结合社会秩序的特点,数字秩序是有序性和无序性、流动性和静态性、自由性和规训性、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一)数字秩序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
立足人类社会生活史,社会秩序要么是有序的,要么就是无序的。人类通常抱着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来描述某种社会形态的秩序状态。但鲍曼强调:“秩序和混乱都是现代之孪生儿,无序是以所有元素的流动性、无定型性、不确定性、无差异性和整体的混乱为特征。有序则是在一个情境中,某些事情比其他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其他事情更不可能发生,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18]84显然,要坚持辩证法观点审视社会秩序而不能将其绝对化。任何有序的社会秩序中都潜藏着走向无序的因素;而无序的社会秩序中也蕴含促使无序转化为有序的因素。因此,对于任何社会形态都不应该简单地用有序或无序来描述其状态。数字社会的数字秩序亦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辩证统一。前者表现在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的单一性、稳定性以及可预见性;后者则彰显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的非规范和例外,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简而言之,数字秩序并非绝对均衡状态,而是动态的、内在的非平衡状态。数字秩序可能包含诸多促使其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危机因素,同时也可能存在促使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因素。
(二)数字秩序是流动性和静态性的统一
在原始社会,人类因狩猎或躲避自然灾害而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在农业时代,人类因日常生活同土地紧密结合而流动性相对较弱。但随着农业的商品化,人类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人类的流动意愿与频率明显增强。当然,虽然流动性是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的重要状态,但因社会整体性的社会分工较低且较为松散,流动并未影响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确定性。显然,社会包含流动性和静态性两种相互嵌合状态,而社会秩序也必然具有静态性和流动性两种特性。可以说,社会秩序是流动性和静态性的统一。我们不应将社会秩序视为固定的和静态的,而应将其视为始终随社会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数字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流动社会,数字空间是超越地方空间的流动空间,数字生活是液态流动生活。数字秩序亦不可避免处于流动之中,并在流动中进行规则的传递。与此同时,数字秩序亦表现为明显的静止性。数字秩序的流动性并不否定静止性,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静止性的意义和价值。数字社会以及数字生活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特定的静止状态,而数字秩序也会因这样的暂时静止而出现静止状态。
(三)数字秩序是自由性和规训性的统一
秩序是蕴含自由的秩序,自由也是秩序之内的自由,秩序与自由始终存在着不言自明的辩证张力。任何社会形态中的任何秩序类型,无论蕴含怎样的流动性、动态性,都始终蕴含秩序之所以被称为秩序的日常性、标准性。过于自由的社会秩序极有可能威胁社会的有序运行;而过于规训的社会秩序极有可能压抑社会生活的活力。滕尼斯[19]52-54认为,共同体和社会这两个范畴适用于一切类型的结合体,古代社会的秩序是具有共同体特性的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的秩序则是社会特性的秩序。宏观方面,得益于数字秩序的自由性,全球性数字社会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体或群体能实现跨地域联动开展数字实践,建构社会关系,拓展数字资源,争取数字权益。同时,数字秩序又是约束数字生活的准则。社会主体在数字空间中的数字轨迹隐含着自身的行为特征、兴趣爱好、社会习惯以及情感意志。如果借助数字技术对社会主体在不同数字空间遗留的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就能很好地挖掘数字主体的活动规律,从而以更细致、更隐蔽的方式影响甚至支配主体的数字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数字技术持续创新所营造的单向度社会中,这种规训逐渐演化为个体的自我规训,从而使数字生活陷入社交控制和监视的泥淖。
(四)数字秩序是虚拟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正如数字社会和在场社会、数字生活和在场生活之间虚实共生的辩证关系一样,数字秩序和传统社会秩序亦存在明显的辩证关系。如前所言,任何社会秩序都深深根植于特定的空间结构,而空间结构也必然要求社会秩序予以同步回应。数字空间并非没有社会性、生活性的技术性空间,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社会性空间,而建立在数字空间基础上的数字生活也是虚实共生的生活。各种类型的数字秩序并不能被触摸,只有当数字生活中的具体数字实践受到程序阻拦时才能被感知。同时,数字秩序又并非完全抽象的秩序,数字秩序所维系的数字生活本质上也是传统日常生活的延伸和拓展,且数字秩序的内涵常常源于人类在场社会生活实践。可以说,数字秩序和在场秩序互通共融、相互影响。
传统社会秩序是数字秩序的重要来源;数字秩序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拓展和深化,维系着数字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在数字生活蓬勃发展的数字时代,数字生活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很多社会主体甚至以数字秩序隐喻的社会事实开展社会生活。
五、数字秩序的基本类型
数字社会蓬勃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人类抛离了之前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轨道,并赋予我们数字化的社会生活形态。立足社会学家对社会秩序的划分,秉承数字秩序的基本特征以及数字生活的基本体验,数字秩序在理论层面包含以下四种类型。
(一)政治权力主导的权力型数字秩序
权力型数字秩序是政治组织设定运行的带有强制性功能的秩序规范。为促进全球数字社会的稳定运行和有序发展,同时也为解决国家内部数字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各种潜在数字问题,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世界许多国家均制定并颁布了促进数字社会稳定运行的法律法规。例如,我国于201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美国于2022年颁布了《加强美国网络安全法》。实质上,权力型数字秩序是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按照维护阶级利益、促进社会发展进行理性谋划进而实现其意志行为的结果。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主导的数字秩序依然存在,并表现为对数字社会、数字空间和数字生活的制度性安排、设计以及规训。但这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数字秩序存在着根本差异。我国建构的各种形式的权力型数字秩序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数字权益,规训的是少数不遵守数字规则的社会个体或群体。
(二)技术精英主导的技术型数字秩序
技术型数字秩序是掌握非一般性数字知识的数字空间生产者制定的一系列显性或隐性的数字程序。在数字社会,知识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掌握技术知识的群体可以通过掌握的特定知识影响和支配数字社会。但在数字社会运行和数字空间生产中,并非所有社会成员都拥有生产数字空间所需要的专业性数字知识。掌握数字技术知识的技术精英常常会依据自身数字诉求,并结合互联网集团(公司)实现资本增殖的目的生产和再生产各种类型的数字秩序。与此同时,承载数字生活的数字空间又被数字技术划分为不同的数字模块,在这些空间中也具有各种技术规范予以支撑,主体须接受这些技术规则才能获得更好数字体验。
(三)资本集团主导的资本型数字秩序
资本型数字秩序是互联网集团(公司)进行资本增殖、获取数字利益而制定的一系列数字规则。剩余价值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空间则是资本进行积累和增殖的重要场域。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尝试创造新的生产场域满足增殖的需要,而异质空间则创造了生产场域基础。传统地方性空间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本快速流通,不利于资本的运行和发展。但数字空间本身就是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束缚的流动空间,这为资本的全天候、全时空增殖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基于数据占有进行资本积累的数字资本也已产生。在此意义上,生产和再造数字空间的互联网集团(公司)就通过制定特定的数字秩序支配数字生活,并将数字生活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生活。
(四)数字主体主导的主体型数字秩序
人是社会的主体,其必然要依据社会的运行制定符合自身日常生活的秩序,用来规范和衡量与他人的关系,指导日常生活实践。因此,任何社会秩序都有一定人类主观意识的介入和塑造,这是秩序的内在属性。在数字化过程中,不仅法律条文发生了变化,而且社会个体的心理结构也承受剧烈动荡。正因如此,在数字生活中,社会成员亦会建构自己的数字秩序,并用以指导数字生活,维护自身数字权益。主体型数字秩序源于社会成员在数字交往中形成并内化为潜意识的一系列规范。当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存在于个人头脑中的规范,而是作为数字群体所共有的集体规范。在数字生活中,主体型数字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制约着个体的数字行为。
总体来说,数字秩序的四种类型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制约。一方面,权力型数字秩序、技术型数字秩序、资本型数字秩序以及主体型数字秩序均是影响数字社会、数字空间、数字生活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型数字秩序是保障主体型数字秩序的根本,其往往通过规范技术型数字秩序、资本型数字秩序来促进主体型数字秩序的发展。
六、数字秩序的意义
关于数字秩序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还须认真思考数字秩序在现实层面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建设好数字中国是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采取有效措施将数字秩序中无序因素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发挥其有序性因素的作用,才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数字生活需要。
(一)数字社会良序运行的基础
数字社会的良序运行是确保我国数字社会蓬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数字社会的稳定和数字空间的稳定有序紧密相关。这就需对各类数字空间进行有效治理,而数字空间治理必然离不开数字秩序支撑。
首先,数字秩序是打造数字空间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如前所言,数字空间是一种典型的流动空间,其既是数字社会的外在表征方式,也是数字生活的承载者,还是数字秩序黏附的场域。从空间社会学立场出发,空间治理将空间本身既视为治理对象又视为治理工具,并以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精神空间三个维度为切入点,强调以空间的方式治理空间并实现碎片化空间的深度整合。和传统在场社会的空间治理有所差异,数字空间的空间治理在治理结构、治理形态上均是一种纯化的空间治理。通过对技术型数字秩序和资本型数字秩序的规制,发挥国家权力型数字秩序的积极作用,合理监管和规训数字技术精英群体以及互联网集团(公司),推动不同数字App空间的高效聚合。同时,只有人类参与的社会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数字社会活力的根源是社会公众的数字生活,社会公众应是数字空间治理的主体。因此,数字秩序应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数字参与权,充分整合分化的数字空间,聚合空间治理资源,打造空间治理共同体。
其次,数字秩序是形塑数字结构共同体的前提。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20]。社会秩序是现实社会结构所具有的一种常规性或恒常性特征。相应的,秩序问题也被视为社会结构如何具有或获得秩序性特征的问题。数字秩序是数字社会结构状态和社会关系状态的哲学表征,是调整或协调数字结构各部分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有效工具。在数字时代,传统社会结构向去中心化数字网络转变,而数字秩序多面辩证的特征发挥着“安全阀”功能。在科塞[21]23-36眼中,
“安全阀”能够维护冲突各方之间的关系,能够阻止或者减轻其他方面的冲突,没有“安全阀”的制度或“安全阀”制度不完备的社会结构既是僵化的又是充满危机的。
数字秩序能增强数字社会各系统之间的韧性和弹性,确保数字空间内部各类模块之间高效有序衔接,能很大程度上避免互联网集团(公司)野蛮式的数字空间生产,确保数字社会的生产结构和生活结构保持良序运行,从而打造数字结构共同体。
(二)美好数字生活的基本条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2]。美好数字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美好数字生活难言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
首先,数字秩序能推动形塑脱域生活共同体。人类既有的数字生活并不会自发形成生活共同体,需要数字秩序将散落在差异空间中的个体凝聚起来。任何共同体都需建立一种它们赖以存在的内部秩序[23]。
数字秩序保证社会主体基于强连接的熟悉交往、基于弱连接的半熟人交往以及临时连接的陌生交往稳定开展,使数字个体能很好凝聚起来,继而建构跨越地方空间的生活共同体。
其次,数字秩序有助打造信任生活共同体。信任最初源于人类本体性安全需求,在数字生活以及社会秩序扩展中起着本源性、基础性作用。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信任通常可分为基于血缘、亲缘以及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以及一般关系的普遍信任。在数字时代,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消解。失去信任的社会将会变成没有凝聚性的一盘散沙而失去生机和活力。数字秩序使人类能在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中开展交往行动,提升共有的数字生活体验、道德情操和理想信念,增强既有数字生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增强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屏幕中他者所具有的信心,形成信任生活共同体,降低存在性焦虑。
(三)数字空间公平正义的保障
任何一个社会“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上社会公平与正义”[24]39,且“最发达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完成建设公正的使命”[25]345。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实现公平正义既是数字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数字秩序最重要的价值体现。
首先,数字秩序能保证数字空间资源的分配正义。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生活资源和社会资源。但是,社会的数字转向并未消弭传统社会阶层的差异,反而一定程度上以数字形式复制并延伸了现实社会差异,隐性地产生了以数字鸿沟、数字区隔为表象的阶层差异。数字秩序能保证社会个体不因权力、地位以及身份差异公平参与数字空间的生产再造,让任何数字阶层群体均能表达数字利益诉求,营造更加包容、公正和可持续的数字空间。同时,数字秩序还能让社会成员在数字生活中按照自己意愿改变数字空间,以保证成员不会因权力的差异而带来生活体验的差异,增强数字生活的主体内涵。
其次,数字秩序能保证数字生活的差异性。生活世界具有本源性,是人类一切有意义活动的发源处,是一切客观知识的来源[26]。数字秩序是社会主体开展数字行动的必要条件,也是数字生活的核心和灵魂。各类互联网集团(公司)和技术精英群体在数字化过程中联合起来,生产和再造了诸多类型的数字空间。但仔细审视不难发现,这些数字空间在应用功能和模块设置上具有显著的同质化倾向。譬如,购物类数字空间京东和淘宝,两者虽由不同互联网集团(公司)设计和生产,但两者在主要程序和模块设置上大同小异。差异性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特性,人类生活也应是基于个性差异的差异生活。但同质数字空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同质数字生活,违背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政府主导的权力型数字秩序通过有效调节,能将资本型数字秩序和技术型数字秩序约束在合理范围之内,鼓励它们生产和再造多向度数字空间,释放社会主体的个性,避免数字生活的标准化和程序化。
(四)数字空间认同的内在要求
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承认和认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孜孜不倦地探索“我是谁”“我与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将成为谁”等问题的答案。对这些问题追问和回答反映的是人类的自我认同以及对他者的认同。在数字时代,数字生活的发展也意味着人类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数字化转向。可以说,数字认同是自我和他者认同的空间呈现,并表现为个体对“媒介自我”和“媒介他者”的信任感。
首先,数字秩序有助于塑造数字成员的情感认同。数字媒介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使“恋网情结”成为新型情感体验。所谓“恋网情结”即人类对数字空间的情感连接。时至今日,我们的喜怒哀乐已经和数字生活紧密相连。我们不仅从数字生活中获得情感认知和情感体验,而且会以当下的心情和情感开展数字行动。“恐惧的感觉是主观的,不过,有些恐惧显然来自对个体具有威胁性的外在环境,包括警觉和焦虑。”[27]202数字秩序能重建“我们”的空间和“我们”的空间归属感,减少脱域交往中潜在的恐惧,使源于不同疆域和圈层的成员相互依赖、相互依恋以及相互投合,并真实地表达自我和展示生活,建构以兴趣、感情为纽带的情感生活共同体。
其次,数字秩序有助于塑造数字个体的自我认同。数字生活中数字身份的易得性与多元性为社会个体畅游数字空间、获得超真实的精神体验提供了绝佳场所。
然而,在数字场景中,我们也可能被虚假的生活需要蒙蔽双眼而造成现实生活中自我感知的模糊,甚至走向身份迷失的认同危机。
数字秩序的稳定有序发展能将不同的个体固定在特定场域位置,增强生活场景的真实性和数字交往的确定性,继而塑造健康人格,营造和谐宁静的心理秩序,使个体真正体验到真实生活需要的存在,也真正理解自己的数字行为及行动背后的深层次意识。
七、结 语
总体来说,社会秩序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属。本文秉承社会学传统社会秩序的理论知识,对数字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了初步探讨,虽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在全球数字社会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于完善传统社会秩序论,正确看待和评价数字生活以及预测数字社会变迁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只有掌握秩序变化发展脉络,人类才能了解社会转型和发展的真实面貌。数字秩序一经生成便成为特殊的客观存在,成为数字社会运行和数字生活遵循的特定规则,乃至被当作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固定下来。或者说,数字秩序要在与传统秩序发生断裂的过程之中完成对数字社会的重新建构。当然,数字社会的动态性和流动性意味着数字秩序也必将随数字社会以及数字生活发展而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数字化转型中,数字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鲜明特征之一,这既对中国社会学界提出了严峻挑战,又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社会学界应充分结合传统社会学理论知识、立足中国式数字社会的基础,全面总结中国式数字生活的集体表象,努力构建立足中国经验、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也是我国打破西方社会学理论支配,并在社会学理论方面为全球社会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的理论发展[M].贾春增,董天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 芬伯格.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M].上海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团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3] 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邱淑莉.和谐社会的价值:对秩序与公正的追求[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5):24-27.
[5]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6]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7]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8] 埃尔斯特.社会的粘合剂:社会秩序的研究[M].高鹏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9]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 武中哲.罗斯的社会控制观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学刊,2006(6):75-77.
[11] 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13] 褚尔康.“数字空间”的秩序形态与运行特征[J].未来与发展,2023,47(7):54-57,22.
[1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6] 高春花.诗意栖居:城市空间伦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17] 杨金颖,邵刚.社会秩序的生成问题论析[J].前沿,2011(11):8-10.
[18]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9]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0] 陈曲.吉登斯对行动理论构成性要素及其关系的阐释[J].天津社会科学,2020(1):75-79.
[21] 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23] 周光辉.政治文明的主题: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J].社会科学战线,2003(4):186-190.
[24] 斯坦,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5]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2版.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6] 战迪,季瑞宁.重返“生活世界”:技术具身的空间性辨析[J].未来传播,2023,30(2):87-94,140.
[27] 郭文.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流动中的文化古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Digital Order: The New Order Form of Digital Society
GUAN Qiping
(Law School,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Anhui,China)
Abstract:All social developments need a stable social order.“Why the social order is possible”is one of the core issue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The rise and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shaped the new social form of digital society,and how to understand “why digital order is possible”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problems of sociology. At the conceptual level,digital order is a new social order derived from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basis of gathering digital society,Digital Space and digital life together. Digital space is the basis of operation of digital order,digital communication is the practical basis of digital order,digital relationship is the basis of transmission of digital order,and digital norm is the logical basis of digital order. At the characteristic level,digital order is the dialectical coupling unity of order and disorder,static and fluidity,discipline and freedom,virtual and reality. On the type level,the digital order can be divided into power-based order based on political power,technology-based order based on digital knowledge,and capital-based order based on digital capital,a subjective order based on intersubjectivity. At the level of value,the digital order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nsuring equity and justice in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relie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digital life.
Key words:digital order;digital society;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feature type; meaning and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