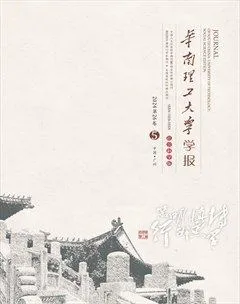商标许可人未进行品质监督应承担产品责任吗?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为商标许可人的“应当监督”条款增设处罚规定,将该条款理解为强制性规范,实为对该条款规范属性的误读。基于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权利保护法定位及商标法律体系自洽要求,“应当监督”条款理应界定为倡导性规范。我国司法适用的经验也表明“应当监督”条款不具有强制性,违反该条款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产品责任,印证了该条款的倡导性规范属性。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可删除“处罚规定”,以回归“应当监督”条款倡导性规范属性,促进知识产权充分运用。对于被许可商标商品的产品责任,应依据产品责任制度确定:商标许可人如果未进行品质监督就不应承担产品责任。
关键词:商标许可;“应当监督”条款;倡导性规范;产品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24)05-0086-10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24.05.008
收稿日期:2023-11-13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商标注册确权制度改革研究”(2022-JCZD-25);河南省民法学会项目“商标品质保障功能的恰当定位及其立法设计研究”[HNCLS(2024)038]。
作者简介:张德芬(1966—),女,硕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安新源(2001—),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
① 《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十条第四款规定:“许可人、被许可人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对消费者造成损害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以下简称“应当监督”条款)。2023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六十条第四款对违反该款规定,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行为课加行政处罚(以下简称“处罚规定”)①。这一举措虽是我国维系商标品质保障功能的新尝试,但也要理性分析对许可人给予法律责任的正当性。
商标品质保障功能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该功能存在于商标权利人与实际或潜在消费者之间[1]22-23,向消费者传达使用相同商标的商品或服务具有相同的品质的信息[2]489-490。换言之,它只是确保商品或服务品质的一致性,而并不能保证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依此理论,美国法院进一步推动了商标财产化发展——商标权利人得以合法地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前提条件是商标品质保障功能未被破坏[3]162-164。因此,这种授权通常伴随着商标许可人的品质监督。
商标财产化理论催生了商标许可人与产品生产者的分离,并由此引出商标许可人是否应当承担产品责任以及如应承担应依何规则承担的问题。“应当监督”条款仅规定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并没有言及判断标准及法律后果。对于如何理解许可人能否被视为生产者进而承担产品责任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任何将自己的姓名、名称、商标或者可资识别的其他标识体现在产品上,表示其为产品制造者的企业或个人,均属于“生产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批复》(2020年修正)(法释〔2002〕22号)。。这一观点实质上将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拓宽至商标许可人,将“应当监督”条款作为商标许可人承担产品责任的法律依据。理论界也存在将商标许可人违反“应当监督”条款的法律责任理解为产品责任的观点,其主要理由是:第一,基于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合理信赖及商品质量外部化的趋势,应将该条款视为商标许可人的法定义务,商标许可人应当连带承担由贴附其商标的产品缺陷导致的赔偿责任[4]。第二,商标许可人与商品制造商具有表见代理关系,依据“应当监督”条款,应被包括在产品责任主体当中[5]。第三,正因商标许可人从许可行为中获利,故其理应履行品质监督之法定义务,承担产品责任[6]。《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设“处罚规定”正是上述观点的反映。
本文认为,“应当监督”条款实为不完全法条,不应作为请求权基础,商标许可人不履行监督义务的行为不产生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商标许可人对被许可人贴附其商标的商品是否承担产品责任,其法律依据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而非《商标法》。《商标法》中的“应当监督”条款属于倡导性规范,而非强制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既不是请求权的基础,也非行政机关实施惩罚的依据,对此我国司法实践已有印证。正确认识“应当监督”条款的倡导性规范属性,恰当处理商标许可与产品侵权之间的关系,是判断商标许可人是否承担产品责任的前提。
二、属性明确:“应当监督”条款为倡导性规范
所谓倡导性规范,即提倡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法律规范[7]。该类规范是基于降低风险、节省成本、减少纠纷的目的而提供给当事人的一种风险较小的选择。“应当监督”条款作为倡导性规范,不仅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符合《商标法》作为权利保护法的价值定位,而且是实现法律体系自洽的要求。
(一)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
“应当监督”条款涉及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利益安排,故其规范性质属于民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应当根据民法价值判断的实体性规则予以确定[8]。换言之,应探寻《商标法》在商标许可使用关系中规定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商品质量之目的。笔者认为,采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讨论“应当监督”条款的规范属性更为准确。《商标法》中设立“应当监督”条款之目的是维系商标品质保障功能。“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相同商品大量出现在市场上,消费者关注的重点转向商品的质量和特性,而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降至次要地位。”[9]然而,这一规制目的的实现并不必然需要为商标许可人设定品质监督义务。
一方面,对品质保障功能的保护只需使现行商标制度正常运行即可,单独对其进行保护可谓多此一举。随着商标财产属性的逐渐放大,商标权利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往来不再是“一次性生意”。作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无论是商标权利人还是消费者,他们均会基于对行为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考量而作出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商标的价值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者评价[10]。对消费者而言,如果贴附某一商标的商品品质一向令人满意,他们便会选择重复购买该商品或服务。反之,消费者就会拒绝选择此类商品或服务,而且如果这一信息在消费市场传播,那么其他消费者也会相继拒绝购买。对商标权利人而言,为使其商标不被市场淘汰,他便会选择维持其商品品质的一致性。正如美国学者所认为的,商标具有自我执行(self-enforcing)特点[11]168。如此,商标品质保障功能实为激励商标权利人维持商品品质一致的市场手段。换言之,商标权利人之所以有动力维持商品品质的一致性,是因为担心丧失市场而非害怕法律制裁[12]。基于此,如欲通过商标制度激励商标权利人维持商品品质的一致性,须确保商标与商品之间正确的指向关系,即须保障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13]16。有学者便认为,美国《兰哈姆法案》确立的质量控制义务,事实上仍是预防识别来源功能受损的措施[14]。只有在识别来源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下,商标才得以发挥其竞争工具的社会属性,帮助商标权利人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并未要求建立商标许可使用关系必须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法》一直使用“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用语(横线为笔者所加)。。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程序也只要求报送许可人、被许可人、许可期限、许可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范围等材料,而并未设置强制报送品质保障条款。可见,立法者设立“应当监督”条款只是为了提醒商标许可人重视商标许可使用中的交易风险,并没有为其安排具体利益分配内容。这说明该条款仅仅是指引双方当事人行事,并无强制之意图。同时,商标许可使用合同未经备案的法律效果也只是该法律行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并无诉讼法上的效果。违反某一法律规定而不产生诉讼法上的效果恰恰是倡导性规范的特点[15]。
(二)符合《商标法》的权利保护法定位
立法目的体现法律的宗旨与精神,对于规范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6]。《商标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其关于立法目的条款正顺应时代发展与经济理念变化作出“定向”调整,为实现《商标法》立法目的所制定的规范体系蕴含其价值宗旨,尤其是其保护倾向。因此,对“应当监督”条款的属性界定须符合《商标法》立法目的转向趋势以达至其贯穿始终的价值宗旨。
依据立法目的的抽象程度,《商标法》的立法目的可以分为具体目的与抽象目的。《商标法》的抽象目的乃其所欲实现的秩序价值,主要体现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句中;而《商标法》具体目的则体现为实现这一抽象目的的实践手段。需要指出的是,具体目的并非独立于抽象目的,而是内化为抽象目的的衡量标准[17]。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身便以具体目的之实现与否为其现实衡量尺度,对于《商标法》具体目的的研究更能体现立法者赋予《商标法》的价值宗旨。
《商标法4dae47a4fbff183b9307b5c4fe5dc2749272a7400afcb8ad933700f7f4b7ea3a》立法目的条款在“变”中延续“不变”,其抽象目的始终为经济发展服务[18],这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然而,立法者欲实现这一秩序价值的手段顺位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商标法》逐渐从“商标管理法”转向“商标权保护法”[19]。虽然商标权的取得涉及行政程序,但行政程序服务于商标权保护[20],最为典型的便是此次《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一条明确将“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列为《商标法》实现秩序价值的首要手段,而将“加强商标管理”作为实现该目的的手段之一。可见,“商标管理”由现行《商标法》中的首要目的转换为“保护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手段,二者在立法目的上发生次序逆转,以“顺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突出产权保护,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大便利”参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商标法作为“权利保护法”的定位更为凸显。
“应当监督”条款的规范性质自然应符合《商标法》立法目的转变的最新趋势。商标权保护的实质便是实现公平竞争与自由竞争的平衡[21]。过强的商标保护虽然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却也会限制相关竞争者的竞争空间,进而危害自由竞争[22];过弱的商标保护固然有利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却会造成“搭便车”“滥用商标权”等不公平竞争现象,亦会危害自由竞争。前面已经论及商标品质保障功能依赖于识别来源功能而发挥作用,保证商标制度的正常运行便能够促使商标发挥品质保障功能。如若将“应当监督”条款理解为强制性规范,增设“处罚规定”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商标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之目的,却无意间束缚了商标权利人的手脚,不利于自由竞争。需要说明的是,当消费者利益与商标权利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优先考虑保护消费者利益[23]。然而,“应当监督”条款是对商标权利人市场激励的体现,旨在提醒商标权人控制商品质量,而非对消费者进行保护[24]。如若商标权利人未能保持商品品质的一致性,其会自食其果——丧失消费者对贴附该商标商品的满意预期。
一言蔽之,作为倡导性规范“应当监督”条款,更有利于在公平竞争与自由竞争间寻得平衡,公允地加强对商标权利人合法利益的保护,以实现其权利保护法目的。
(三)符合商标法律体系自洽的要求
法律是由一系列规则组成的体系,体系性是其本质属性[25]。《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从强制性规范出发,增设“处罚规定”,不利于法律体系自洽。“处罚规定”的适用前提是“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依据《商标法》对商标的两种分类,此处的损害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贴附许可商标的产品所致的损害;其二是依照《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使用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商品未达到其使用管理规则要求,而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
如果对“损害”采取第一种解释,则“处罚规定”与产品责任归责体系存有龃龉。商品质量不属于《商标法》的规制范畴[26],应由《产品质量法》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规制。1982年颁布的《商标法》曾将商标使用人“商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列入调整范围,这混同了产品责任与商标品质保障功能。直至2013年《商标法》修改,有关部门提出商标的注册、保护与商品质量无关,这才删除了此项规定[27]277-278。商标许可人在市场中具有多重身份,既有可能是商标许可人也可能是商品生产者。作为商标许可人,其应遵守品质监督要求,但其是否应当承担产品侵权责任,应由《产品质量法》调整。“应当监督”条款不能作为其承担产品责任的法律依据[28]。我国立法机关同样指出,“对有关商品质量问题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相关法律处理”[29]13。事实上,试图在《商标法》框架内规定属于《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内容本就难以实现。例如,美国《兰哈姆法案》规定了商标许可人应进行品质监督,否则将可能构成裸许可产生失权效果;然而,该规则一直难以执行,几乎沦为一纸空文[30]。故而,只有将“应当监督”条款理解为倡导性规范,才不会破坏现有法律体系的逻辑体系。
如果对“损害”采取第二种理解,则“处罚规定”与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体系价值存有差异。《管理办法》之所以对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人施加更为严格的义务,是因为在《商标法》体系中存在的并非普通商标使用中注册人与消费者之间点对点的线性关系,而是注册人、使用人与消费者相分离的网状关系[31]。在这种复杂关系中,任何符合使用条件的市场主体均可申请使用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而注册人无法拒绝。普通商标所具有的权属局限被突破,这使得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利益均衡价值更加凸显,法律介入以实现价值平衡具有正当性基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便有观点指出,“倘若使证明商标的使用脱离注册人的管理监督,那就瓦解了证明商标法律制度的有机体,证明商标法律制度的生命力便荡然无存”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5)粤知法商民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普通商标使用过程则不具备此特点。另外,如果立法者试图要求商标许可人承担未履行品质监督要求的责任,增加“对消费者造成损害”条件反而增加了处罚门槛[32]。如果要求商标许可人承担违反品质监督要求的责任是试图将规制关口前移,那么便不应当以造成消费者损害为条件。
这两种解释均表明,如果把“应当监督”条款误读为强制性规范,就会给商标权利人造成不必要的法律负担,从而削弱商标品质保障功能本应在市场自由竞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利于实现法律体系自洽。
三、实践印证:“应当监督”条款的适用经验
自1982年颁布《商标法》以来,我国司法审判实务中已经审理了较多涉及“应当监督”条款的司法案件,为探究该条款的性质提供了实务支持。为此,本文以“应当监督”条款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进行检索,经过筛选得到81例涉及“应当监督”条款和实践中商标许可人如何承担产品责任的案件,并对其进行了整体研究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法院认可“应当监督”条款作为倡导性规范,并正确认定了商标许可使用与产品责任间的关系。
(一)“应当监督”条款适用概况
从地域分布、诉争事由、审理程序等对这81例案件展开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地域分布来看,此类纠纷在我国不同地域发生的概率较为均衡,呈现多点并发态势。河北、辽宁、江苏、山西、河南、四川、重庆、青海、山东、湖南和天津各1例,上海和海南各2例,浙江和北京各3例,湖北5例,广东7例,福建48例。具体如表1所示。其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案件1例,由于北京市并非该案发生地,故笔者将该案二审审理法院所在地河北省作为其分布地域。需要说明的是,福建省涉及的48例案件中有46例为以某教育公司为被告的合同纠纷案,这些案件中,原告均以被告未履行教育培训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教育服务所贴附商标的权利人依“应当监督”条款与被告承担产品瑕疵担保责任,法院均驳回原告该项诉讼请求。因北大法宝数据库无法检索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纠纷案例,故在应能检索到的31个省级行政区内,半数以上地区的法院涉及该条款案件。
从诉争事由来看,原告认为商标许可人违反品质监督要求的责任承担不局限于产品责任,在其他纠纷中也存在着以该条款作为判请依据的情况。具体类型为:合同纠纷57例,侵害商标权纠纷10例,不正当竞争纠纷5例,产品责任纠纷3例,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3例,侵害著作权纠纷2例,商标权属纠纷1例。涉及“应当监督”条款案件诉争事由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其中,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侵害著作权纠纷主要涉及原告主张商标权人应与著作权侵权人或专利权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法院在判决说理部分涉及了“应当监督”条款性质,故笔者将其纳入考虑范围。例如,在王某诉深圳某电子有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王某主张被告销售产品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并要求被告产品上贴附商标的权利人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侵权产品上虽然贴附商标权人商标,但该标注方式并不足以
证明商标权人直接参与了侵权产品的制造、销售、许诺销售行为,故判定商标权人不承担连带责任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453号民事判决书。。在司法实务中真正以产品责任诉至法院的案件并不多,仅占3.7%。
从审理程序来看,一审审结案件67例,占比82.72%;二审审结案件13例;进入再审程序案件数量只有1例,具体如表3所示。进入二审和再审程序的案件在关于商标许可人违反“应当监督”条款方面的论述都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观点。
(二)“应当监督”条款不具有强制性
判断“应当监督”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关键在于对“应当”一词含义的界定。在我国立法技术中,法律在表述义务性规范时,一般使用“应当”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印送〈立法技术规范(试行)(一)〉的函》(法工委发〔2009〕62号)。。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义务”“要求”等词汇描述“应当监督”条款,甚至把该条款理解为强制性义务条款。但从审判实务来看,凡涉及被许可商标商品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例,法院都没有把该条款作为强制性义务规范,要求商标许可人承担产品责任,而是依据商标许可人是否参与被许可商标商品的生产经营,按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判定其是否承担产品责任。
上述81例案件中,涉及产品责任承担的案件有10例,占分析样本总数的12.35%。其中,有4例案件分别是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2)渝0192民初747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20)粤0307民初2776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终29057号民事判决书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4906号民事判决书。法院最终认为商标许可人未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不应承担连带产品责任;有6例案件分别是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2048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583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2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8)海南民二终字第7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923-1号民事判决书和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则相反。在处理上述纠纷时,各地法院均未径直认定未进行品质监督的商标许可人承担产品责任,而仅仅是在产品责任制度下依据商标许可人是否参与被许可商标商品的生产来认定其是否承担产品责任。例如,在罗某某与中山市某电器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在认定商标许可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时指出,不能因存在商标许可使用关系直接认定其为产品制造者,更不能推定其与被许可人共同实施了侵权行为参见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2民终1027号民事判决书。。在北京某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诉湖南某数码公司等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法院同样认为不能因存在商标使用许可关系直接认定商标许可人为产品制造者,更不能推定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共同实施了侵害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参见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2)渝0192民初7474号民事判决书。。在某科技有限公司诉中山某电器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只有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形下,商标许可人才应对使用其商标的产品承担相当于产品制造者的法律责任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终2048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在沧州市某饲料开发有限公司诉天津某科技有限公司等产品责任纠纷案中述及产品侵权责任时也并未论及商标许可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申字第923-1号民事判决书。。
也就是说,法院在判定商标许可人是否应当承担产品责任时,均遵循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即由缺陷产品的销售者、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二条、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而非适用“应当监督”条款。法院判断产品责任主要认定焦点在于能否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关系径直认定商标许可人为产品制造者或生产者。一般情况下,商标许可人无法越过商标被许可人而成为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只有在涉及生产过程,商标许可人将自己置于生产者地位时,才可能承担产品责任。这种情形事实上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只是纯粹的产品责任关系,而非商标许可使用关系。
由此可见,在审判实务中,“应当监督”条款不具有制裁要素,并非强制性规范,而仅仅是倡导性规范。
(三)“应当监督”条款仅适用于产品责任
如果依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商标许可人需要对被许可商标商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那么其责任范围是否仅限于产品责任?对此,绝大多数法院认为违反品质监督要求的责任范围仅限于产品责任,商标许可人无须对被许可人的其他商业活动所致损害负责,此类案件占比高达93.83%。只有5例案件法院认为应将该责任扩张至不当使用商标及商品包装设计侵权责任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合同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2015-2019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知民终204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1民初14716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知)初字第39327号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8民初21285号民事判决书。。例如,在吴某诉山西某工程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参见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晋05民终1467号民事判决书。中,吴某在山西某工程有限公司购买家居产品后,该公司未能如期交货。吴某诉至法院,以商标许可人某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义务对商标被许可人进行监督为由,要求某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该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义务对自己商标的使用者进行监督,但该监督义务是指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而并非对商标被许可人的其他商业活动负责。正是由于法院认为违反品质监督要求的责任范围限于产品责任,故多数法院在说明该点后,即以原告诉请的责任请求属于被告在商业活动中产生的责任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此外,即便商标许可人对于被许可的商标商品进行了品质监督,法院也没有为商标权人苛加过高的品质监督义务,而仅是将该义务标准解释为《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义务。例如,在某工业株式会社诉江门某摩托车有限公司等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法院根据被诉侵权摩托车产品系经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后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这一事实,认定商标权人对被许可商标商品的质量监督尽到了注意义务参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0620号民事判决书。。从法院表述可以看出,法院认为商标权人履行品质监督义务的标准不以其是否对产品质量一致性进行控制,而只是要求贴附商标的产品经过国家质量监管部门审批。
四、应然选择:商标许可人未进行品质监督不应承担产品责任
如前论述,“应当监督”条款作为倡导性法律规范,不需要也不应该有制裁要素。《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增设“处罚规定”不符合倡导性规范的特征,亦不利于知识产权运用。商标许可人是否承担被许可商标商品的产品责任,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参与被许可商标商品的生产经营。因此,商标许可人对被许可商标商品的产品责任应回归产品责任制度本身进行判断。
(一)可删除《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处罚规定”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可删除《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处罚规定”,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作为倡导性规范的“应当监督”条款并非用来直接表达法律规范,故不需增加制裁要素。“应当”的词义含有倡导性的规范样式,其本身便蕴含着提倡、鼓励行为人的意图[33]。这类条文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较为常见,如对合同形式的规定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八条、第七百零七条、第七百八十九条、第八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等。、对法律行为内容的规定主要体现为规定合同内容。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条、第五百九十六条、第七百零四条等。等,又如在我国教育法、环境法体系中,亦存在倡导性规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四款等。。相关立法多在总则部分宣示国家政策或倡导公民响应政策。此类条文属于非规范性条文,不是直接用来表达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起到倡导的效果[34]36-38,故此类条文语句结构上并不需要制裁要素。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由假定、处理、制裁三要素构成。假定是指出适用这一规则的前提、条件或情况的部分;处理是具体要求人们做什么或禁止人们做什么的部分;制裁是指出行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的部分[35]116。“处罚规定”实际上填补了“应当监督”条款的制裁要素。然而,如前所述,“应当监督”条款为倡导性规范,只是采用非具体的肯定表述指引当事人在作出法律行为时注意所需回避的风险,更多地体现原则性的倡导,立法不应对当事人是否为该项行为作出评价[36]。
其二,增设“处罚规定”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的充分运用。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经历了从创造为主向运用为主的转变[37]。具有合法垄断性质的知识产权,只有与市场相结合并进行充分地转化与运用,才能真正释放知识经济的能量,促进社会效益增值[38]。知识产权的运用,就是通过商品化等手段使法律所保护的智力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39]。商标许可使用属于知识产权运用的一环。商标权人有时囿于自身能力或商业规划选择许可其他市场主体使用其注册商标,以充分发挥商标的经济效益。增设“处罚规定”意味着商标权人在许可他人使用时,需在品质监督成本与许可收益间进行充分考量。如若前者经济成本过高,尤其是商标权人以非独占许可的方式许可商标时,商标权人可能基于风险分配的考虑而减少商标许可甚至不进行商标许可。长此以往,注册商标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不利于实现知识产权的全链条运用。
(二)回归产品责任制度判断被许可商标商品的产品责任
本文认为,对被许可商标商品产品责任的判断应回归产品责任本身,即商标许可人只有在真实有效地参与产品生产、制造等过程时,才可能作为产品责任的主体。
其一,在商标使用许可关系中,即便该产品的消费者出于信赖认定商标许可人为产品生产者,但由于该商标权的许可人并未“将他人制造的产品作为自己的产品销售或分销”,因而其并非产品责任中的生产者,自然无须承担产品责任[40]。有学者根据产品责任的举证责任规则,认为受害人只需提供购物发票、收据、产品相关标志标识等及损害即可,商标许可人应证明缺陷产品并非自己生产的[41]576。该观点实质上仍是将“应当监督”条款作为强制性规范而得出的结论,未在产品责任话语下考虑证明标准。此种观点所确立的标准过于宽泛,以此标准衡量,任何商标许可人都将被视为潜在的产品生产者而面临承担产品责任之风险,不利于维系和谐的市场竞争秩序。本文认为仅凭此证据不足以证明商标许可人为产品责任主体。此类证据仅能证明存在民事主体将某标志贴附于侵权产品之上,以试图表明该产品来源于商标所有人。例如,在广东某五金有限公司与温州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案中,广东某五金有限公司主张温州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其提供的证据仅为贴附商标许可人商标的侵权产品包装。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仅凭该证据难以认定商标许可人系侵权产品制造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211号民事裁定书。。商标许可人是否真实有效地参与了生产制造过程,以至能将其置于生产者地位,亦难以证明[42]。
其二,在商标许可使用与产品责任关系中,商标许可人、商标被许可人及消费者形成复杂的多重关系。商标许可人只有以实际行为真实有效地参与产品的生产、制造等过程,其才能越过商标许可使用关系,成为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具体而言,一方面,商标许可人真实有效地参与产品生产之判断多见于双方的许可使用合同中约定条款。例如,在德国某公司与上海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即认为商标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在商标许可合同中约定,被许可人应将授权商品及其包装样品交予商标许可人审查,经商标许可人书面核准确认后,商标被许可人始得正式量产、上市及销售。故而法院认定商标许可人真实有效参与贴附商标产品的生产过程,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前提下,可以将其认定为产品责任承担主体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7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书。。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商标许可人对被许可人的资本控制能力为准。如在广东某五金有限公司与谢某某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商标许可人作为法定代表人及股东,也是商标被许可方的出资人,同时其与商标被许可人的生产经营范围存在一致性,故应当将其认定为产品生产者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583号民事判决书。。
五、结 语
商标许可人未进行品质监督不应承担产品责任,“应当监督”条款作为倡导性规范不应作为商标许可人承担产品责任的规范基础。在判断商标许可人是否应当承担产品责任时,应分别处理商标许可关系与产品责任关系,回归产品责任关系确定商标许可人是否承担产品责任,我国司法实践也采取相似做法。只有当商标许可人真实有效地参与了产品生产过程时,才可能被纳入产品责任主体。该规则的明确有助于澄清“应当监督”条款的倡导含义。对《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处罚规定”作出否定性评价,有利于保障商标权人合法权益,避免仅依据商标许可关系而径直要求其承担产品责任。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斯.商标法:实证性分析[M].马强,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7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3] 朱冬.财产话语与商标法的演进——普通法系商标财产化的历史考察[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
[4] 冯辉.外部性视野下商标许可人监督义务的重构[J].知识产权,2013(9):32-37.
[5] 李继伟,王太平.产品责任法中的表见制造者研究[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37(6):71-79.
[6] DESCHAMP J R.Has the law of products liability spoiled the true purpose of trademark licensing? Analyz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trademark licensor for defective products bearing its mark[J].Saint Louis University Public Law Review,2006,25:247-276.
[7] 王轶.论倡导性规范——以合同法为背景的分析[J].清华法学,2007(1):66-74.
[8] 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4(6):104-116,206.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2013年修改).[EB/OL].(2013-12-24)[2024-07-12]http://www.npc.gov.cn/zgrdw/npc/flsyywd/minshang/node_22754.htm
[10] 余俊.商标本质基础观念的重构[J].中国法学,2023(5):211-228.
[11] LANDES W M,POSNER R A.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12] 彭学龙.商标转让的理论建构与制度设计[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29(3):132-141.
[13] 杜颖.社会进步与商标观念:商标法律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 LEMLEY M A, MCKENNA M. Irrelevant confusion[J].Stanford Law Review,2010,62(2):413-454.
[15] 贺剑.民法的法条病理学——以僵尸法条或注意规定为中心[J].法学,2019(8):75-91.
[16] 杨铜铜.论立法目的司法适用的方法论路径[J].法商研究,2021,38(4):86-100.
[17] 戴津伟.立法目的条款的构造与作用方式研究[J].法律方法,2016(2):217-228.
[18] 余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商标法治[J].知识产权,2023(5):3-26.
[19] 邓宏光.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J].现代法学,2010,32(2):143-148.
[20] 孔祥俊.论我国《商标法》的私权中心主义——《商标法》公法秩序与私权保护之定位[J].政法论丛,2023(3):41-54.
[21] 王太平.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相似性与混淆可能性之关系[J].法学研究,2014,36(6):162-180.
[22] 黄汇,徐真.商标法公共领域的体系化解读及其功能实现[J].法学评论,2022,40(5):114-125.
[23] 邓宏光.论商标法的价值定位——兼论我国《商标法》第1条的修改[J].法学论坛,2007(3):88-94.
[24] 梁志文.商标品质保证功能质疑[J].法治研究,2009(10):3-11.
[25] 刘小妹.法律体系形式结构的立法法规范[J].法学杂志,2022,43(6):85-101.
[26] 刘维.论商标权穷竭的功能虚置与价值回归[J].知识产权,2023(1):87-108.
[27] 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8] 魏宁.论商标许可人的严格产品责任[J].电子知识产权,2020(7):37-47.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解读》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30] CALBOLI I.The sunset of “quality control” in modern trademark licensing[J].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7,57(2):341-407.
[31] 牛玉兵.证明商标制度的价值与实现[J].知识产权,2010(6):71-75,81.
[32] 刘筱童,陈珍妮.商标许可中的产品质量责任承担[J].电子知识产权,2023(5):16-30.
[33] 吴永科,张丽.“应当”词义考[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5(3):14-17.
[34] 雷磊.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35] 张文显.法理学[M].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6] 李楠.论消费者受教育义务的误读与澄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3条第2款之解释与适用[J].经济法论丛,2022,39(1):250-263.
[37] 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现代化的实践与发展[J].中国法学,2022(5):24-43.
[38] 吴汉东.试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法治观和发展观[J].知识产权,2019(6):3-15.
[39] 吴汉东.新时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试论习近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4):31-39.
[40] 冉克平.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J].科技与法律,2013(5):60-68.
[41] 程啸.侵权责任法[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42] 杨存吉.商标所有人不应被推定为专利侵权行为人[J].人民司法,2012(10):4-7.
Shall Trademark Licensors be Liable for Products if They Fail to Con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Comments on Article 60(4) of Bill to Revise the Trademark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osure Draft)
ZHANG Defen AN Xinyuan
(Law School,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Henan,China)
Abstract:
Bill to Revise the Trademark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posure Draft) adds a “penalty provision” to the “shall supervise” clause for trademark licensors. This is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noramtive attributes of the clause as a mandatory norm.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rational person” in economics,the legislative purpose of Trademark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rights protection law and the self-consistent requirements of trademark legal system,the “shall supervise” clause should be defined as an advocacy norm. Chinas judicial experience has also shown that the “shall supervise” clause is not mandatory,and the liability for violating this clause is limited to product liability,which confirms the advocacy nature of this clause. Therefore,the Exposure Draft should delete the “penalty provision” and return to the “shall supervise” clause of the normative attributes of advocacy and to promote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product liability of the licensed trademark goods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liability system,and the trademark licensors should not be liable for the product liability if they fail to conduct quality supervision.
Key words:trademark license; “shall supervise” clause; advocacy norm; product li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