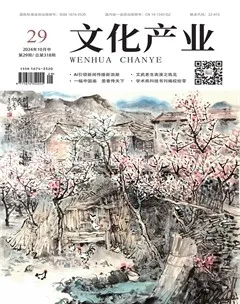新媒介艺术重构审美体验
摘要:新媒介交互艺术不同于传统艺术的生产模式,而是造就了新的审美活动,其所诉诸的具身性审美方式在多重意义上重塑了审美经验。新媒体交互艺术的内在结构本身就是对体验的一种强有力的召唤,交互艺术中交互形式对体验形式的扩展和延伸,交互场景对生活世界力量的显现和澄明等都体现了新媒体交互艺术对审美经验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唤醒和还原。
审美经验的建构内在于审美活动中,而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而是体验活动。哈贝马斯认为,艺术作品不是“认识或理论的对象化把握的整体”,而是“具体生活的非对象性整体”,它不能被认识思维分割成知识片段,它的存在本性需要有情感的审美参与者在体验中把握和揭示。新媒介交互艺术所生发的审美活动不同于传统艺术注重认识过程,它强调的是为审美参与者提供多通道的审美体验路径,在审美参与者的具身性审美方式中实现审美经验的建构。因此,新媒体交互艺术在审美经验的建构上具有独特的方式和意义。
新媒体交互艺术对审美体验的召唤
“体验”的德语原文(Erlebnis)与“经历”(Erleben)共享着同样的词根,“经历”与生命、生存、生活(leben)联系在一起,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经历”。因此,“体验”是与生命、生存、生活等需要不断显现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就是在体验中表现的东西”“生命就是我们所要返归的本源”,一切返归生命本源的意愿都需要从“体验”开始。在伽达默尔的论述中,“体验”是一种整体性的事物,“如果某物被称之为体验,或者作为一种体验被评价,那么该物通过它的意义而被聚集成一个统一的意义整体”,这个“整体”有三种含义,一是“体验”本身是整体性的活动;二是“体验”所把握的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三是“体验”所体现的意义也是整体性意义上的人的含义。中国美学家叶朗在《美学原理》中引用王夫之“现量”概念说明了“体验”的另一个特点,即当下直接的真实性。王夫之对“现量”的定义,即“现在”“现成”和“显现真实”,叶朗做了详细又精彩地阐述,其精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体验”最原始的含义是当下直接的感兴,也是“现在”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心目之所及”;二是“体验”是审美直觉瞬间呈现的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即一个完整的世界;三是“体验”所生成的意象世界能照亮一个本然的生活世界。由此,我们得知“体验”的内在要求包括整体性和当下直接的真实性。“体验”的内在特性要求审美体验要贴近人生世界的整体性行为活动,是当下现实的瞬间感兴,在直接的生存活动中显现存在的“本真状态”和世界本身。
传统艺术的审美体验表现为纯粹的心理活动,对作品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想象和联想。然而,当艺术作品以抽象的形象呈现在欣赏者的头脑中,人的“体验”其实恰好被消解了。我们知道,视觉本身具有分离性、抽象性、分析性的特点,“体验”的完整性、当下直接和显现真实的特点在视觉或有距离的听觉活动中被肢解、破坏以及碎片化,从身体这一维度来看,在传统艺术的审美活动中,身体处于“缺席”状态,身体日常的自由行动在此时的审美活动中被束缚,身体的活动必须以支撑观看为导向的活动为准则,由此身体被约束在观看的二维空间,“体验”的完整、鲜活和生动也消失在此空间内,“身之所历”被等于“目之所见”,“体验”最原始的含义被遮蔽,人只知道“冰”是凉的,但却不知道“冰”的温度(当人摸到“冰”,并感叹“好凉”时,才真正“体验”到“冰”)。
与之相反,新媒体交互艺术所召唤的审美体验正是要感受“冰”的温度,是完整的当下直接的真实感兴,是生活世界的敞亮。首先,新媒体交互艺术的交互装置和场景空间要求身心“在场”,交互装置面对的是完整的审美参与者,开放式接触交互场景把人的身体活动纳入审美体验,隐性渗透式交互场景为情感的沉浸提供了空间。同时,新媒体交互艺术本身并非作为思维信号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空间,它引导审美体验作为事件自然发生。无论是开放式接触交互场景,还是隐性渗透式交互场景,都试图把意义生产还原至具体的情景,让审美参与者在当下直接的现场获得审美感兴。
以新媒介交互艺术家珍妮弗·霍尔(Jennifer Hall)的作品为例,其作品《世间果实的针灸疗法》(Acupuncture For Tem-poral Fruit,1999)用由西红柿、电动机、针灸用针和用来检测观众距离的声呐设备组成的众多电子装置单元记录参与者的动向,当参与者进入作品范围时,声呐设备感知到后,会触动发电机带动针刺进西红柿,当观众距离单元越近时,针会越激烈地穿刺西红柿,经过一段时间后,水果变瘪,并且长出夸张的霉丝。此作品让人联想到生命、伤害等内容,西红柿生命状态的变化记录了参与者进入作品空间所留下的轨迹,像是审美参与者在此空间的时间导致了西红柿“血液”的流失,时间在这里作为一个清晰的事件标示着审美参与者的存在。
除了把审美活动直接呈现为事件,把人从形式逻辑中“拉”出来,将其置于鲜活的人生世界,新媒体交互艺术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带来审美体验的回归,即将走向内省的主体,重新导向生活世界的生存性主体。新媒体交互艺术的交互形式不只是感官的游戏,前面提到的交互装置和场景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将人抛到一个可能性的空间中,生命与体验之间紧密的关联重新凸显,把存在的“真”放入“此在”自身在可能性境遇的体验,让人直接感受存在,而不是思考存在。
审美参与者的重塑
马克·波斯特曾说,“社会空间充满了人和机器的结合体”,此观点指出主体是在社会空间中组构的事实,并揭示了电子传播技术让人们重新认识主体的组构过程,又在改变人们交往方式上重新组构了现代主体。如今,马克·波斯特的预言得到证实,媒介技术的变革带来主体组构的困境和主体对自我组构的认识矛盾。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中,一方面,物理空间的城市建设和社会身份决定了我们的生存活动和身份建构,体现了各个身份的自律性;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中寻找社交,全球性的社会言论成为网络居民外在实现的主要方式,主体性在网络形成的全球性网格球面上成为结点式的存在。可见,当代人的“主体性组构”和主体性认知处于不稳定、分裂和充满矛盾的状态。身份的两重性模糊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技术复制力量潜移默化地削弱或淡化了我们的感知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和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艺术。
新媒体交互艺术在实现“完整的人”和获得与自然、与世界的连接上具有优势。首先,新媒体交互艺术能够唤回人的感知能力,在具身性经验方式下聚合知觉整体,实现对审美参与者感知能力的召回,对存在的本来面貌的敞亮,以及对人与万物最直观的联系的呈现。因为交互艺术家试图展现的不是感动后的结果,而是感动发生时的原初情景,或者是想法发生时的最初牵引,试图在作品中让这种真理在审美参与者的全身心参与中自行发生。从而,人作为一个整体会被纳入真理发生的情景,审美参与者在作品中往往能够放松身体、自由行动和自行探索场景的意义,在尽量消除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过程中表达符号的编码规则带来的媒介限制后,新媒体交互艺术确实将此中间环节还原成了一个鲜活的空间,不再是扁平、静止的抽象世界,审美参与者的一切感官在此空间中被放大、变得澄明。
其次,感知能力的召回和存在感的获得消解了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之间的裂缝,形成一个新的主体。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他需要美,是因为他需要感到他自己存在于世界。”因此,我们的审美体验实际上是感受自己真实存在的体验,在网络虚拟世界日益占据我们生活的现在,我们需要在鲜活的世界中获得审美体验,在具体感受自己的美感中获得存在感。新媒体交互艺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给予人们与世界、与自己获得连接感的审美体验。在新媒体交互艺术的具身性经验审美方式中,审美参与者的感知能力在体会到自己存在的瞬间被寻回,人们能够获得对“此在”的体悟,以及对身边的花草树木产生存在上的认识。能肯定的是,这种具有全新感知能力的主体是一个更能感受自我存在的主体,这是一种存在感的唤回,是对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最精彩的建立。
新媒体交互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作品就具有这样的力量。其作品《介导运动》(The Mediated Motion,2001)通过控制湿气制造“雾”的天气效果,让人在感官消失中更加关注其他事情。人们可以让自己暂时消失在“雾”中,但也因为短暂的消失,人实际上是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回归。因为人只有在感到虚无时,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以及存在的价值,这种对人生的思考和对存在的追问成为个人生命中四射的光彩,以及个人灵魂的深深叹息与呐喊。于是,一个人就不再仅仅是作为肉体的人而存在了,而是拥有精神的独立,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奥拉维尔·伊利亚松的作品撕裂了一切虚假,只呈现虚无,让人在虚无中无所适从,并在虚无中获得新生。
人与生活世界之间总被插入一个翻版的“现实”,使人获得独立思考的空间,但也让人离生活越来越远。交互艺术场景让人们直接面对自己的体验,树的触感、泥土的味道、风的吹拂和阳光照射到身上的温度等,与我们拥有真实联系的万象在交互艺术场景中不是在内省中呈现,而是一种“触兴”,是与物“相值相取”获得的通达体验。交互艺术场景将人的感知聚合,促成整体性的人的活动,当人的感知被无限扩大时,人的存在就变得无比清晰,便能将目光从内心世界转向围绕在人身边更广阔的生活世界。
美感的扩张
艺术家的体验和欣赏者的体验不同,艺术家的体验是在整体中当下、直接的体验,欣赏者的体验是间接的。新媒体交互艺术对美感的扩张是基于艺术表达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的还原上而言,主要表现为多感官聚合的沉浸感和感知能力澄明的存在感,还有平等交流和自由创造的满足感。
多感官聚合的沉浸感在新媒体交互艺术的各类型中都有体现。但真正的沉浸感在于感官的解放,并不在于感官的封闭。感官的解放不是感官能力的扩大,而是感官从一切外在目的中解放,回到纯洁的状态,正如丰子恺先生所说:“眼睛要能看见形象的本身,耳朵要能听到声音的本身,心思要能像儿童一般天真烂漫。”因此,新媒体交互艺术中的沉浸感表现为能够弱化作品物性的存在,在潜移默化中让审美参与者忘却感官目的,融入交互空间。例如,兰登国际(Random International)在MoMA美术馆展出的大型艺术互动装置“雨屋”(Rain Room,2012),该作品并没有直接引导参与者做出某种动作,也没有给感官发出任何指令,审美参与者在“雨屋”中却玩得不亦乐乎,他们沉浸在一片雨声中,漫步在无边的丝雨中,自在地在这生命中常见的场景中玩耍,不用担心别的结果,只用感受这场雨带来的所有情感。
感知能力澄明的存在感在新媒体交互艺术中是与沉浸感结合在一起的,沉浸是感官的解放,感官的解放既是在潜移默化中让人忘却感官,更是在忘掉感官之后能更清晰地感知世界。这就是感知能力澄明的内涵,也是新媒体交互艺术美感扩张的重要部分。当审美参与者结束参展,走出新媒体交互艺术,回到日常生活中,他们并不是从一个世界走出来再回到另一个世界,因为这本就是一个世界,新媒体交互艺术的感官能够与日常世界无缝连接,带着更加强烈的感知能力对自己的存在进行体会和认识。
在新媒体交互艺术中,我们能通过审美活动清晰地体会自己的一举一动,能够产生“诗意涟漪”,这是对自己存在感的确认,也让我们对自身行为所具有的力量有了具体认知。通过这种审美体验,审美参与者能够获得一些超越性的视角,对自己、对自己和所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拥有更多感触,正如王阳明所说的“一时明白起来”。例如,詹姆斯·特瑞尔(James Turrell)的灯光装置作品,他将光线扩展到一个空间,使整个空间都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人置入其中时,感官所及都是莫名的色彩,包裹着人的灯光消解了参与者对空间与光的理性思考,在此空间内,人们只需要感受光与色带来的视觉震撼和场景无法忽视的存在感,视觉被消解之后,其他感官会变得无比清晰,无处安放的心也异常跳动,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奇异般鲜活起来,正契合了维科所言:“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交互艺术场景的任务就是让起初的感触无比真实,才能让人的反思建立在更加清醒的心灵之上。
在新媒体交互艺术中,平等交流和自由创造的满足感得到最集中的体现。面对景观社会,新媒体交互艺术的创新之处,正是通过“实践”和“创造”的“真”来消解一切不确定性,以及消解虚拟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人云亦云的无意义。当代,既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重要和突出,那么如何在各种关系中不迷失自我,如何使主体之间的关系保持本真状态成了重要问题。一般而言,交互艺术的审美活动如下。参与者进入交互空间,在对场景作品全身心感知的基础上进行审美体验,传统艺术作品在审美活动进行到这一步时就完成了其使命,但新媒体交互艺术却还需要进一步反馈信息,呈现参与者对作品的二次创作效果,这种直观直感的体验,呈现了参与者本质力量的一种外在实现,更呈现了参与者与作品之间的一种平等、自由的关系。正如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一书中所言,“人通过‘你’而成为‘我’”,参与者与作品之间只有通过这种超越性的本真共在,才能让参与者在审美活动中与另一个自我,即作品,自由交往、和谐共存。
新媒体交互艺术美感扩张内涵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沉浸感、存在感还是满足感,都紧紧围绕审美参与者的生存活动展开,美感的扩张实际上表现在参与者存在意义上的延伸,即从视觉空间的分裂人回归到整体的空间,以及从现实和虚拟主体的分裂还原整体的人。
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网络文艺批评理论创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30)。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