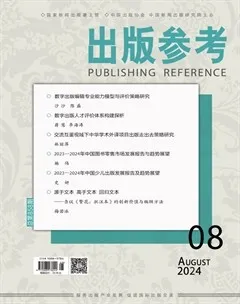《大鸟》翩跹:彭学军儿童小说的开拓与坚守
彭学军的新作《大鸟》带给我们的惊喜是双重的。一方面,《大鸟》为我们构建了一幅以白鹤为轴,融合人性探索、成长轨迹、生态哲思与文化底蕴的独特画卷;另一方面,经由《大鸟》,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辨识度却又有些陌生的彭学军。我们不妨用“二”加“一”来描述彭学军在其新作中展现的变与不变。所谓“二”加“一”,指的是两种开拓与一种坚持。两种开拓,一是指彭学军对儿童文学创作范式的创新与拓展;二是指她在儿童文学领域所展现出的深度与广度的双重掘进。一种坚持,则是彭学军自踏入儿童文学殿堂以来,始终秉持着“心灵面向”的文学创作初心,这份坚持在以盈利为目的的儿童文学创作氛围中,更显卓尔不群,且弥足珍贵。
一、文化儿童小说创作范式的自觉开拓
自《建座瓷窑送给你》起,彭学军便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边界进行了勇敢的探索,逐渐开辟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儿童小说创作路径。在《大鸟》中,这一创作范式展现出更为纯熟与自觉的风貌。文化儿童小说,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或元素为创作的基点与载体,精心构建了一个既植根现实又超越凡尘、既色彩斑斓又富含智慧与深情的文学世界,引领孩子们在故事中遨游,体验文化的深邃魅力,领悟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而在内心深处种下对文化的尊重与认同的种子。文化儿童小说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让故事深刻体现作家试图展现的文化内涵,而非仅仅将文化作为背景点缀,或是猎奇噱头以吸引读者眼球。在《大鸟》中,彭学军不仅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鸟类文化知识,更实现了故事与文化之间无缝且深刻的融合,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叙事新境界。
首先是其内在而深刻的文化视野。大鸟并非仅仅作为元素或背景来点缀文本,而是直接结构了整个故事。周蔷因大鸟之舞开启了另类的选择和别样的人生,并在此过程中结识了一群可爱的人,其童年创伤也得以在这一系列经历中逐渐抚平。而对于小男孩蒿子而言,大鸟则填补了他因母亲缺席而留下的心灵空缺,那是一个充满爱、希望与力量的位置。同时,也是由于大鸟的存在,故事中的人们完成了各自的蜕变,那个大鸟曾经停留的空间——芦洲村,也因此变得赏心悦目、温暖而和谐。
其次,大鸟被赋予了高度人格化的审美理想,它不仅是人类应当守护的宝贵存在,更是美的使者,是治愈人类精神创伤的“神鸟”。读者在这片大鸟栖息的大湖里,心灵得到了冲洗与净化。某种程度上,大湖,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芦洲村,这样的空间不仅仅是一个事实空间或地理空间,而且也是一块精神飞地,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代际、不同文化背景乃至不同国别的人在这里汇聚,因为大鸟,这些异质性人群得以因爱之名而相互连接。
最后,西方人讲物我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在彭学军的《大鸟》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心物”关系被放置在一个显著的位置或坐标之中。阳明先生说:“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大鸟》理解为一个关于“修心”“养心”“安心”“正心”的故事。有趣的地方不在于,这些可爱的人们保护了这些珍稀动物;恰恰相反,正是经由这些可爱的大鸟,人们才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因而给予和索取的二元关系恰恰在小说中发生了有趣的倒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彭学军的文字耐读、耐品并且韵味悠长,她的文字因情真而暖心,因“关心”而动人。彭学军的文化儿童小说的价值也正在于,她吁求或邀请孩子们以及那些自闭的大人们,从自己的小天地中走出来,去迎接、接纳一个更为广阔而多姿的世界。
二、“成长”叙事的深度开掘
在《大鸟》中,彭学军不仅聚焦于儿童的成长历程,还深刻描绘了那些内心仍如孩童般纯真却面临再次成长挑战的大人们。这两种成长并非孤立,而是相互映照,互相给予。也就是说,真正需要成长的不仅仅是孩子们,还有那些身体或生理上已然成熟,但是其内在却是如此封闭、孱弱、匮乏、苍白的大人。反讽的地方正在于,不仅仅是那些大人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相应的养分,同时也是那些儿童给予了那些尚待成长的大人们一些非比寻常的勇气与希望。
因为断角羊事件,内在的精神创伤使得周蔷的生活始终被阴影所覆盖,或者说她始终生活在自我囚禁的状态中;大鸟则为她走出阴影,完成解放提供了契机。尽管已是成人,但在文本中,我们多次看到周蔷的无助与逃避。小说开篇为我们呈现的就是一个因为无人帮忙种藕而独自哭泣的女人,此时的周蔷是那样的无助与委屈,而在蒿子的帮助下,才露出了笑意。在经历了“和刘芬妈的‘战争’”“水塘放水”等事情后,周蔷似乎在守护大鸟的路上也逐渐强大起来。但突然而至的“停车场事件”,使得周蔷再度陷入迷茫和沮丧之中。面对她无力改变的现实,周蔷的选择是逃离。与此同时,那些年轻的生命却并没有放弃,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叫停了正在施工的停车场。正是这些孩子给了周蔷以力量,让她学会直面挫折,并最终因为自己的努力守护了大鸟,并感染了周围的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恋人的大齐,并未真正理解周蔷的内心世界,他的不解与逼迫反而加剧了她的困境。而最终拯救周蔷的,是孩子们广博的爱与对大鸟的守护。因而,在彭学军的书写中,爱的主题显得更为宽阔也更为宽广。
当然,彭学军不是为了迁就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才舍弃了爱情,她只是觉得,同爱人、爱自然相比,爱情并不具有更优先或更突出的位置。不仅如此,那些丧失了爱人的人们,也只有重新融入人群以及自然之中,只有重新把爱投注到周遭的对象世界中,才有可能走出那个忧郁的、狭小的自我来。
每个人的内心都藏着一个“阴影小孩”,阻碍着人们的继续成长,只有将其抹除,本心方得复归。作为镜与灯,《大鸟》不仅滋养了孩子们的成长,也照亮了迷茫中的大人们的心路。
三、儿童文学书写的本心坚守
所谓的“一种坚持”应该是儿童文学的底色,或者说它应该是儿童文学的底线或者本色。但是在一个所谓的全民娱乐时代,我们看到大量以娱乐儿童为目的的图书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大有要将那些真正的儿童文学掩埋的趋势。无论如何,儿童文学的功能首先不是娱乐儿童,甚至也不在于传授一些外在的知识,而是为儿童提供一些内在的力量,使得儿童能够勇敢地面对困难,并且给予儿童战胜困难的信心。这本该是儿童文学的题中之义,但是在当下反而成了一种奢望。
在彭学军几十年来的创作中,她始终在坚持“心灵面向”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一个个充盈着爱的故事中,彭学军为读者们带来了一系列生动可爱、积极攀爬的孩子形象:从《腰门》中自闭走向开朗的沙吉,到《奔跑的女孩》中勇敢追梦的驼驼;从《你是我的妹》中给予“我”精神支撑的阿桃,到《浮桥边的汤木》中独自面对困境的汤木,再到《戴面具的海》中在爱中找回自我的海,《森林里的小火车》中热爱探索的罗恩,以及《建座瓷窑送给你》中被“窑火”淬炼成长的少年们。在《大鸟》中,这一创作传统得到了延续。主人公蒿子小小的身躯,却有着大大的能量。在他与周蔷、江韬等来自别样空间的“闯入者”的相处中,小主人公能够自主地重新认识世界并且调整自己,发奋学习。不仅展现了自己真诚、善良、勇敢的品格,还照亮了周蔷以及蒿子爸爸。爱会传递,也会“传染”,在沐浴着爱的芦洲村,在这个桃花源般的空间里,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
如果说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描写儿童的,写给儿童看的。那么儿童文学就必然牵涉关于写作伦理、写作要求、写作内容、写作方法等的问题,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时刻克制、时刻警觉。不仅如此,儿童文学更不应该被资本所裹挟,不能为了经济利益,将儿童文学的基本功能弃之不顾。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要坚守阵地,这既是作家的职责,更是作家的使命。正是在此意义上,彭学军的坚持才显得分外珍贵。
总之,作家之责,在于勾勒一幅我们亟需凝视的心灵地图,以此映照时代之镜,唤醒沉睡于日常尘埃下的真实与美好。在《大鸟》中,我们不仅目睹了彭学军的艰辛攀爬,更感受到了她勇于挑战自我的非凡勇气,以及那份对儿童文学纯粹与深度的不懈追求。
(作者单位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