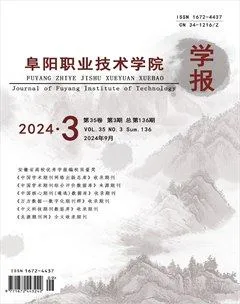中国古典美学“奇”范畴探究
摘要:“奇”作为我国古代美学范畴之一,南朝后在《文心雕龙》中被确立为一种文学风格,后又与儒、法两家及老庄思想不断交流融合,以“奇正”开文学批评实践先河,使“奇”正式成为一种文论范畴。“奇”兼有“美”和“味”的义项,也具广泛而深厚的互文性,在书论、画论及人物品评方面均有所涉及,在其随后的发展演变中对各体文学体裁的创作实践也产生重大影响。从哲学及美学两种不同的维度完整全面地把握“奇”的内涵与意蕴,以进一步探索“奇”在古典诗歌以及小说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奇;演变;美学价值;美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4)03-0051-07
“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范畴之一,其含义不断发展变迁,历经多重演变,可将之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缩影。范畴研究其意义在于,“范畴研究通过对古代个体范畴的集中性研究,把握其内在演变规律和外在关联对象,运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的思维方法,展示中国古代文论内在的生命力、延展力和粘连性、丰富性,在区别于西方文论的同时,将传统文论的审美价值传递到当代文艺与文化研究中。”[1]与西方强调利用概念以把握理论系统的方式有所差异,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实践活动,往往强调个体的领悟与感受,话语体系的使用常包含较多直观经验性质的内容。古人借助天地自然,运用观象思维以山水雄奇比喻文章打破传统阅读惯性,提出文章“尚奇”的观念。刘勰《文心雕龙》提出的“观奇正”奠定了古代文论“奇”范畴的发展基础。明代陶望龄将刘邵《人物志》中的“偏至”思想引入文论,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创新,提出“偏嗜必奇”,逐渐成为后世评价文章的准则之一,因此可以说,“奇”范畴为我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开拓出一定话语空间。
一、“奇”范畴的美学内涵
“奇”范畴的产生既具有丰厚的哲学渊源,也有着丰富的美学意蕴,其中儒、法、道三家思想的相互交流融合,使“奇”具有了丰厚的哲学基础,其美学意义便蕴藏于不同时代各类审美形态的内涵阐释中。
(一)哲学渊源
“奇”含义的抽象化代表着哲学之“奇”思想的兴起。“奇”的哲学渊源最初可以追溯到《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2]246思想中表现出的“奇”,具体即指一如既往地坚持“道”并有所收益,这也是“奇”哲学思想产生的一大前提。老子的“奇”论对于哲学奇正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说文解字》将“奇”解释为具有“异”特征的“异也”和“不耦”两义,在老子提出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思想中,“奇”即为前者所代表的奇异、惊奇、奇妙的意思。“以奇用兵”意味着没有兵、没有战,实际内涵为“不武”,意为不以兵器示强,武器仅以自卫为前提,实际意义还取“不敢”,即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提倡哲学中的兵法智慧。在此基础上先秦兵家提出“奇正相变”,认为要掌握奇正变化的规律,奇正相生,以奇制胜。而文学创作中的谋篇布局与兵家的排兵布阵相类,因此,兵家提出的“奇正相变”为后人“奇正观”的文论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老子认为,“奇”有“非道之奇”与“合道之奇”二分。他将“合道之奇”归入“正”的范围,批判“天下多忌讳,而人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2]241-242的“非道之奇”。《老子》第五十八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体现了“正、奇”与“善、妖”间的相互转化,表现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正”即有“奇”,体现出“奇”在老子哲学思想中的存在价值。与此相类,“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中,“正言”往往通过“反言”或“奇辞”体现出来,对于这种用“奇辞”来表达“正言”的“合道之奇”,老子也持肯定态度。
庄子与老子有所不同,庄子主张“齐物论”,万物归一,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有其自身价值。庄子还肯定得道的“奇人”与“奇语”,“奇人”指形态外貌奇异的人,在内心修养达到道的境界甚或畸人(畸于人)却“侔于天”时,庄子并不作武断批驳。“奇语”指一种合道之言,是有道之人“发之于中必形于外”的结果。这里,庄子对“奇人”“奇语”中“奇”的态度表现出其与儒家明显不同的态度,为后世人们追求个性自由与天性解放提供了有利前提与理论基础。同时,受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美”与“丑”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中让位于表现出具有超越性特征的“奇”范畴。
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奇”,各学派说法不一,并且在其内部也呈多向动态发展的姿态。儒家对“奇”的态度有一个调转改变的过程,儒家崇尚礼法“尊正抑奇”,为维护统治者利益,宣扬正统思想,在价值选择上首先表现为不取“奇”。儒家认为“奇”是对世俗礼法既有行为准则的背离,从新工艺、新技术上创新从而破坏了传统礼制,对正统言语思想的打击以及对中庸观的种种背离等[3]。直至战国末年,儒家对“奇”的批评态度才有所松动,出现视“奇”为中性词来使用的情况。南朝文论批评家刘勰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4]573表现了个人对孔儒思想的肯定。文学领域中,彦和受到法家思想“以正合,以奇胜”的影响,提出“观奇正”,将奇正关系作为评价文章的标准,因而能够在此看到信仰儒家思想的他对“奇”旗帜鲜明的肯定态度。但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评价《楚辞》“奇文郁起”“词赋之英杰”时,既肯定其语言以“奇”为特征,体现出发展创新性,同时也强调要避免“逐奇而失正”(《文心雕龙·定势》),其对过分追求“奇”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二)美学溯源
“奇”范畴的美学溯源可以追溯至古人对自然界的高度崇拜。先民睁开双眼看到世间万象,诞生了如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等一系列神话传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5]今人所言的种种不可抗力因素,如山洪、风暴、地震等,使古人产生无尽的恐惧心理,古人便试图依靠神明,借助占卜巫术诸种方式求得帮助,获取对于“祥瑞”“星象”“灾异”等“自然奇象”的心理慰藉或对此寻求合理解释。《易传·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6]直至后来产生图腾崇拜,流传千古,汇聚而成众类“尚奇载体”──图腾崇拜成为古人奇思审美的物质载体。
战国末期,屈原《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7]20“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7]34便具有巫术痕迹,屈原诗歌中所具有的“异采”特色,与儒家官方意识形态规定的“雅正之美”相去甚远,屈原实指文质方面的奇美,完全脱离儒家经义礼教约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对此总结为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8]四大异彩特点,又为“奇”开辟了不同的审美格局──巫鬼文化拓宽尚奇场域。
两汉魏晋时期,人物品鉴之风大为盛行,刘邵在《人物志》中以“奇”作人物品评,他认为在品评人物时存有七大陷阱,可能致人误入歧途。其中提到“观奇有二尤之失”[9],指在观察奇才时不能够很好地分辨出尤妙之人与尤虚之人,“尤妙之人”即“含精于内,外无饰姿”之人,“尤虚之人”即“硕言瑰姿,内实乖反”之人,含徒有其表之意。单看“硕言瑰姿”误指为奇才,导致“拔奇而奇有败”,选拔重用了“奇才”却导致失败,这种重内在之奇而非形体之奇的尚奇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后起的书论画论的不断丰富发展。随着人们对“奇”认识的加深,品鉴人物之“奇”逐渐延伸至艺术领域,同时,也体现出“奇”的互文性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大量画论作品,“‘气’者‘生气’,‘韵’者‘远出’。赫草创为之先,图润色为之后,立说由粗而渐精也。曰‘气’曰‘神’,所以示别于形体,曰‘韵’,所以示别于声响。‘神’寓体中,非同形体之显实,‘韵’袅声外,非同声响之亮澈……”[10]谢赫在此认为绘画要旨在于追求神韵,而不求其表露于外形之中,如此才能达到那种奇美的境界──这是首次在绘画中将老庄玄学“贵无”思想引进艺术领域。绘画艺术与老庄玄学思想结合从而达到奇美的审美境界,不失为“奇”的又一创新变迁。在六朝书论中出现的“字外之奇”一说,与谢赫“神韵新奇”说类似,都在强调超越形似,实现神韵之奇美。随着书画作品风格与内容的日益丰富,书论、画论思想发展逐渐成熟,“奇”范畴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深入。
“奇”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形态的诸多方面,同时也逐步影响了古人的文学创作与鉴赏,对后世产生较为深厚的理论应用价值,也为自身文学审美内涵奠定了一定基础。
二、“奇”范畴的演变
春秋时期,礼乐松动王权式微,“奇”受《孙子兵法》《庄子》《离骚》等作品影响,价值内涵转向至此发微。《孙子兵法》“以正合,以奇胜”[11]思想打破了“奇”“正”两相对立的局面,“奇”转而成为传统战术思想“正”的变相形式,体现出“奇”的正面价值内涵,重新确立了“奇正相生”的关系,进一步影响了后世刘勰、钟嵘诗论中对“奇”的肯定态度。
(一)从社会价值到文学审美范畴的变迁
“奇”至周代开始作为社会价值范畴,此时初涉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演变。周朝为使中央集权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实现进一步巩固,以维护官方统治秩序的正统思想作为主流价值观,但随着礼崩乐坏,传统秩序新变,价值取向开始趋于多元,“奇”作为“正”“常”传统礼治秩序的对立面出现,冲击了封建正统思想,被视为处于传统礼法秩序之外的消极思想,是一种破坏当时社会秩序的负面社会价值判断。“奇”的价值转向首先受到《庄子》思想和屈宋作品的影响,“奇”逐渐完成由社会价值范畴到文学审美范畴的转变。
道家思想与屈宋作品赋予了“奇”一定美学内涵。一方面源于庄子自由浪漫的文风特点,另一方面从庄子个人对当时社会的批评可以看出,庄子对人物品评的角度不拘礼法、大胆创新,促使“奇人”成为超越世俗的理想人格,也体现出撼动世俗的精神力量。南朝文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伊始便有“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4]44《离骚》中奇异浪漫的丰富奇辞表现出浓厚的艺术感染力,被认为是古代奇崛诗风源头之一,横绝千代,令后人难以并驾齐驱。如屈辞表现的种种服饰之“奇”,具体有“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7]2、“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7]13,主要借助香草意象运用比兴想象,寄托了自身高洁品格。宋玉在《高唐赋》中借《离骚》体现的奇伟艺术想象,“纵纵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谲诡奇伟,不可究陈。”[12]意象上常取奇事怪物,手法巧用修饰夸张,以山水物色自然景象之奇体现出奇崛的审美趣味。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结合具体文学创作实践对“奇”作出进一步阐释,系统地体现在刘勰个人倡导的文学创作与发展的具体要义中。《文心雕龙·定势》篇“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逐弊” [4]362,提出“执正以驭奇”和“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的文学创作风格及方法要求;《辨骚》篇提到“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4]51的文学创作目标;《通变》中可见到关于“望今制奇,参古定法”[4]354的文学创作发展理念。《文心雕龙·物色》中“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4]524此处构成“奇巧”,事物具体可感,为人勾形状貌。但因创作者的思绪无边无际,这时如若抓住事物根本,“因方借巧”“即势会奇”经过巧妙的构思,创作内容依旧能实现历久弥新,体现出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辩证文学发展观。同时关于文学创作的欣赏与批评活动方面,《文心雕龙·知音》篇“四观奇正”[4]554指出了创作实践中新奇与平正的辩证关系。“奇”的价值内涵逐渐渗透于文学审美空间。
(二)由局部呈现到整体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南朝批评家钟嵘不满齐梁腐糜文风,将表现出卓越正面价值的“奇”内涵作为品评五言诗歌的一大标准。主要从诗歌创作方式与风格方面将“奇”与儒家经典中的“正”割离,扩大了“奇”在诗学范畴的内涵,提高了“奇”的独立地位。
钟嵘主张少用事,提出直抒胸臆的“直致之奇”,评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13],多推崇情感自然流露,不拘个人才性的“奇”志自由抒发;认为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类。又巧构形似之言。”[14],“净”字足以见出钟嵘对少于驳杂繁复,不加雕琢“直致之奇”的审美追求。陆机诗句“准古法”“尚规矩”从而表现出多凝重、诗情繁冗的特点,钟嵘认为其强调诗歌格律,有损于诗歌自然“直致”,直言道“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15]200钟嵘主张诗歌在于真实情性的自由抒发,推崇表现个人真情,同时继承了庄子与屈原、宋玉“奇”观念,认为“奇”是超脱世俗,甚至推及“雅”的高度,如在《诗品序》中评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15]175赞赏其文辞奇崛、卓尔不群的特点。
唐宋诗论中,“奇”又进一步发展到诗歌创作全过程、各层面的整体实践要求中,即从诗歌创作方式、风格进一步延伸到诗歌的选材、运思、句法、造语、用韵等方面,由点及面,不断完善。中唐诗人皎然写道:“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16]皎然认为诗歌奇句的生成规律具有苦思而得自然的特点,主张创作“惨淡经营”,站在诗歌整体观上把握炼字、炼句、炼意的多重原则,经过一番苦思冥想,文字实现化工之奇不至陷入诡怪窠臼。“奇”在诗论方面也对诗歌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创作追求由“奇”至“平”的调转
宋诗前期受乐天、义山影响,后又学韩,最终造就独特文风。其中诗论以黄庭坚为代表,提倡“遇变出奇”被时人奉为圭臬,遂使整个江西诗派尚奇成风,以致后来形成一味追求“奇崛形式”的单一格局。过犹不及,宋由此转入“平淡”“自然”的诗风境界。
如陶诗《饮酒(其五)》中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语言初看平淡,但富有奇趣。陈寅恪认为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17]五柳先生思想广博多元,含有同老庄思想相类于世俗生活中保持完善自我独立人格之精神,也含有“生命”课题中深邃幽微意蕴之求索,更具有对“自然”哲学思想的深刻体悟。其中五柳先生对于“自然”的追寻,既是寻求带有“自由”意味的自然,也体现为追求“自然的文学”。保持个人的本性自然,尊崇诗歌贴近人生实际,诗句中常常平中见奇,语言少于雕饰,但意蕴隽永,又合乎性情,自然流露出诗歌“奇美”。
这与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奇崛”有异曲同工之妙,语词不艰涩,稀松平常间见出语境的淡美,少于雕饰多自然,组句言平意深,炼字可达意胜,不以逞奇当先。如此也在宋朝文论中拉近“奇”与“平淡”及“自然”的关联,动摇了前期韩孟诗派“奇”“平”失衡的局面,此类以“平淡”“自然”求矫“好奇”之弊直至明代仍有所保留。
三、中国古典诗歌与小说中“奇”的美学价值
为适应维护儒家传统话语系统的要求,文学创作多表现出具有典范代表特征的“雅正”之美。然而由于作品自身传播的需要以及内容创新发展的要求,无数文人墨客选择打破传统藩篱,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的“奇美”创作追求便为其中体现之一。“奇”在中国古典诗歌、小说中都表现出一定的美学价值。
(一)“奇”与中国古典诗歌
在宋以前较少涉及对“奇美”的讨论,自宋以来,古典诗歌的文学批评才渐出“奇美”风尚。诗歌“奇美”即要求“文”与“意”相得益彰,不以逞奇为美,通过“遇物而奇”“遇变出奇”和“破体求奇”三种方式表现诗歌奇美。
1.“遇物而奇”
“遇物而奇”是指诗人所描写的自然物象或生活事件自然地引起作者情感抒发,不在于词藻的奇谲夸饰。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间,审美客体对创作主体产生审美感召,因而,创作主体为审美客体作用,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受到外界自然环境刺激,形成自然纯粹的审美体验,由此产生创作主体的自然奇思,进一步实现文学创作活动。如杜甫诗歌《子规》[18]209:
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
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
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凄。
客愁那听此,故作傍人低。
诗人客居到一云安县,江边阁楼上屋瓦整齐排列,两边的树木郁郁葱葱,似乎要将阁楼包裹住,杜鹃鸟儿的啼叫声不绝于耳。春风轻轻拂过,草木随风摇落,只叫人觉得此刻的夜色更加凄凉。作客他乡的人儿哪经得了这番景致,一时间思乡愁绪涌入心田,从心底开始细细蔓延。可是那鸟儿恍若通得人性,故意傍人低飞,惹人烦恼。诗人描绘自己客旅他乡,画面层层递进,空间层次分明,由低见高、由远及近、由静到动,同时调动视听感官,极富有动感。
因周遭自然景致,触发诗人个人情志,于是便将这平日间的耳闻目状、实景实历、所见所闻所感一一抒写描摹,映现出一系列自然的真情实感。题为《子规》,但仅于全诗第四句和第八句两处有所描写,用墨虽少但诗人客旅愁思却已化于纸上,遇物而奇,奇景映奇情、美景照美情,表现出诗歌“奇”“平”两端达到和谐平衡状态的奇美意蕴。
2.“遇变出奇”
“遇变出奇”则是从文学通变的角度,讲究诗歌创作手法的新变,方式上多采用语法颠倒、典故化用、风格新变等以达到诗歌的奇美意境,以求诗歌的情感意蕴与外在形式达到具体而统一的奇美文辞风貌。如杜诗《月夜忆舍弟》[18]146: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避,况乃未休兵。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句语法颠倒,顺句实为“从今夜露白,是故乡月明”。王彦辅说:“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句,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也。”[19]运用陡峭的空间形象和新鲜奇妙具有生命力的诗歌语言,对语法结构进行有意识地破坏,强化诗歌的艺术张力。
一、二句言兵后中原荒凉,唯听边疆独雁哀鸣。五至八句意味深长:一弟分散,与众弟皆分散,分散而无家,“无家问死生”唯有寄书去,书信尚未到达,况且又“未休兵”,音书绝,死生不可知,诗境自然渐出。再说三、四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倒作使寻常之语不再熟悉,变得新奇陌生。调用话语的阻拒性特征,使人们对平日间素常之物的感受发生二次加深,宛转曲折,更映衬出浓厚情思。运用语言的陌生化,产生出其中本质性艺术效果,同时倒作后仍保留了诗歌的韵律节奏,错落有致,延长了艺术的感受性,奇正配合相当,意蕴概出,使得诗歌奇美直泻无余。
3.“破体求奇”
“破体求奇”主要体现在诗歌的形式方面,是宋诗求奇求变的方式之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他将散文代入诗歌,以形式强调内容。梅诗通过描写现实客观景物,表现个人思想情致的自由抒发,具有日常化、亲临感。如梅尧臣的《鲁山山行》[20]: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首句诗人抒发自己热爱山野的志意,连绵的鲁山,千峰奇拔,高低起伏无穷无尽。一路走来,奇峰峻岭变换无穷,独自沉醉于小径之中的美景,不知不觉走入鲁山深处,迷失了方向。不觉间薄霜渐渐消融,熊开始爬到树上活动,空荡的深林里,小野鹿惬意地在溪旁饮水。从远处传来啼鸣,可能会有住家在那边吧。诗人进入山中,情志满怀,描写了自己真实的一段游山历程,将情感、见闻一一巧妙和谐地融于散文化的诗句中。如同一位老友,娓娓诉说这一山路历程,把这富有美感的自然画面带到读者眼前,诗中的偶句“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又表现出具有律动节奏的技巧美,“奇”而不失“稳”,二者相辅相承,达到一种“奇”而又“稳”的艺术境界。梅诗也同样具有奇险与平淡于同一首诗内的完整表现,这种开阔的创作思维与创新意识,也进一步开拓了宋诗的审美空间,从而促进了宋诗发展。
诗歌奇美要旨实际不在于肆意浮华的偏涩行文,是一种实现奇美与自然统一后达到的艺术境界。古代诗歌中的奇美之感,可以说是由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二者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不单于形式层面获得美感,实现字句之奇与意蕴之奇两者间的辩证统一,诗歌内容与意蕴达到平衡寻及界点奇美特征自然俱出。
(二)“奇”与中国古典小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小说同诗歌、散文相比,可谓“后起之秀”,因而小说中的理论批评范畴常常会从诗文理论范畴借鉴而来,小说批评中的“奇”也来源于诗文理论批评术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及唐代传奇尚乏现实色彩,对于唐传奇来说,虽然同前代小说创作相比,已初具文学创作自觉意识,开始不断向现实深入,但总体上也呈“以幻为奇”,以“奇幻”取胜的创作规律,认为幻奇是小说的主要特点。同时,这一时期主要借小说发挥劝惩世人的教育功能,带有古典主义色彩的至美境界。
《搜神记》被认为“序鬼物奇怪之事”,蒲松龄《聊斋志异》也有“才非干宝,雅爱搜神”[21]之说。“搜神”意即广泛搜集神异鬼怪之事,因此其故事情节构思往往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具有强烈的奇幻色彩。《搜神记·左慈》描写一故事:因在曹操举办的宴席中缺少吴国鲈鱼,左慈当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22]12片刻就从“铜盘”里钓到鲜活的鲈鱼,接着又迅即买到鲁国的生姜返还,后来又仅用一罂酒与一片肉脯供近郊的百余人大快朵颐了一番,“放乃赍酒一甖,脯一片,手自倾甖,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22]13
再如,《搜神记》第二十卷中《病龙雨》一则讲述:
晋魏郡亢阳,农夫祷于龙洞,得雨,将祭谢之。孙登见曰:“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水果腥秽。龙时背生大疽,闻登言,变为一翁,求治,曰:“疾痊,当有报。”不数日,果大雨。见大石中裂开一井,其水湛然。龙盖穿此井以报也[22]353。
一位农夫在龙洞祈到雨后,打算去祭祀表示感谢,孙登却言:“此病龙雨,安能苏禾稼乎?如弗信,请嗅之。”龙当时背上生了一个大疽,听到此话,便变成一位老翁,前求医治,并表示医好后一定有所报答,孙登将之治愈不久,果然下起大雨。同时,大石中还裂开一口深井,井水清澈湛然。由此可见,彼时志怪小说通过短小精悍的故事,简单的情节,形成奇妙造意,具有奇幻色彩,骋心游目富有理趣,体现出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保留了小说“尚奇”价值。
在此创作基础上,唐传奇表现出一定进步性,实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地位,为后世小说的叙事架构提供了观照范式,令后世文学的再创作获得大量素材和艺术启发。明代胡应麟有语“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23]不同于志怪小说文字简省的“丛残小语”,唐传奇开始具有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唐中期李复言所撰传奇小说《续玄怪录·薛伟》篇,故事情节、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多表现出奇美色彩。小说内容先以叙事者的口吻介绍薛伟其人身份,其因病“忽奄然若往”二十日后“忽长吁起坐”,此时叙事视角陡转,将薛伟“既出郭”以后,人形化鱼的游历过程开始以第一人称进行详尽细致的描画,从“策杖而去”“跳身入潭”,经“河伯宣诏”终“人形化鱼”,薛伟化人身为红鲤痛快地在水里畅游数日后,因“贪食钓饵”,落入河边钓鱼的同僚掌中,虽“大声呼之”,可只见得“口动,实无闻焉”,最后鱼头在同僚、仆人的眼下被厨司亲手斩掉,“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诏尔”,众人闻后大惊,“三君并投脍,终身不食”,三位同僚决定今后再不吃鱼,结尾薛伟渐渐病愈,“后累迁华阳丞乃卒”[24]85-86。
这是一则想象奇特且技巧纯熟的传奇小说,早在前文薛伟开始正式回忆前,已有其自述因病“不知其梦也”,整个游历过程全部笼罩在梦的叙事下,将梦境带入现实,似真似幻,虚实难辨,更增强了故事的奇幻性。文中还有如“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24]86,这是薛伟化人形为鱼身前,河伯告诫它的内容,预叙了化为红鲤的薛伟终会被同僚擒获,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故事到达高潮。作者在此处运用预先叙事的方法设置悬念,又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暗含讽喻意味。故事情节离奇多设悬念、叙事结构奇幻“引梦入实”、叙事技巧奇特丰富多样,使读者身处于完整的小说空间内。
至明中叶神魔小说《西游记》出现后,小说由志怪传奇一类“以幻为奇”的审美趋向开始向“无奇之奇”变化,从而也促进了近代美学的萌生。
“无奇之奇”的美学意蕴主要体现在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上,强调小说人物个性的客观真实,主要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表现出虚拟的小说空间无限向真实世界伸展。“四大奇书”之一《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细节上的精雕细琢俯拾即是,如第十五回写正月十五众人看花灯一幕: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袄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磕瓜子儿,把磕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一回指道:“大姐姐,你来看,那家房簷下挂的两盏绣球灯,一来一往,滚上滚下,到好看。”一回又道:“二姐姐,你来看,这对门架子上挑着一盏大鱼灯,下面还有许多小鱼鳖蝦蟹儿跟着他,倒好耍子。”一回又叫:“三姐姐,你看,这首里这个婆儿灯,那个老儿灯。”[25]
文中对潘金莲的服饰、外貌、动作、语言作出细致刻画。潘金莲走出家门,此时从封闭的家庭空间置身在人群闹市当中,呈现出人物不同的精神风貌、性格特点,体现小说人物的日常百态,人物塑造更加立体多元。潘金莲与众人出门游耍时,同玉楼一起嬉闹非常,兴致盎然,“搂着”“露出”“带着”“探着”“吐落”“嬉笑”等一连串多个动词,浮夸的动作表现,令读者感受到潘金莲随意自由、自我张扬的生命状态以及她泼辣轻浮,喜爱热闹的性情特征,顺次叫到三位姐姐指看花灯,又显她俏媚活泼、可爱非常。小说充分重视细节刻画,将潘金莲的神情表现、动作举止进行逐一真实细致的描摹,以细微真切的描写打动读者,并且具有日常生活的真实性,以细节描写实现艺术真实,人物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体现出“奇”与“常”间的艺术张力,白描的运用,又巧妙增设出“无奇之奇”的审美意蕴。
参考文献:
[1]赵玲玲.逸范畴的审美空间[M].广东: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2.
[2]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魏东方.中国哲学中的“奇”范畴发微[J].洛阳师范学报,2023(01):25.
[4]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
[5]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
[6]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57.
[7]楚辞[M].林家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8]刘勰.文心雕龙注:第1卷[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6-47.
[9]刘邵.人物志[M].梁满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155.
[10]钱鍾书.管锥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65.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
[12]宋玉.宋玉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1:58.
[13]钟嵘.诗品集注[M].曹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10.
[14]徐达.诗品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59.
[15]张怀瑾.钟嵘诗品评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16]皎然.诗式校注[M].李壮鹰,校注.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39.
[17]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8.
[18]杜甫.杜甫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9]王得臣.历代笔记小说大观:麈史·候鲭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2.
[20]朱东润.梅尧臣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55.
[21]蒲松龄.聊斋志异“聊斋自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2]干宝.搜神记全译[M].王一工,唐文书,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2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371.
[24]牛僧孺,李复言.玄怪录·续玄怪录[M].田松青,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5]秦修容.金瓶梅:会评会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