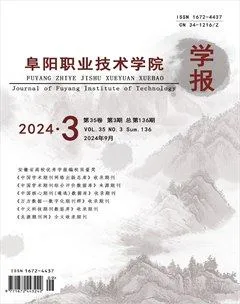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认识价值论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家,鲁迅和沈从文都对故乡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杰出的描绘与反映,不同读者透过他们的小说了解时代的风云变幻,体察社会发展与变迁下的众生相,洞悉宇宙人生与人性隐幽,在今天依然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认识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4)03-0045-06
一、真实性与小说创作
谈到文学艺术的认识价值,首先避不开的是如何处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托尔斯泰有一句话:“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一个村庄,一方水土,其背后往往折射出来的是大社会。可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无论其具体内容怎样,都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社会现实。”[1]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中,“文学来源于生活”指向文学的真实性,这是文学认识价值的本源所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倘若文学漂浮于生活之上,或者是对生活歪曲反映,那么也就谈不上文学的认识价值。文学的真实性也是文学美感的基础,真为美之本根,美为真之升华,文学的真实性为作品和读者搭建了一个有效沟通的桥梁,使不同的读者在不同时代都可以进入文本,获得不同的审美体验,并达到共鸣。同时,文学的真实性也反映出作家的写作姿态是面向大地,面向芸芸众生的,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素质。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到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时说:“处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最常见的办法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文献,当作社会现实的写照来研究。某些社会画面可以从文学中抽取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2]111当然,也不能过于机械地将作品中的事物在现实中都一一坐实,找出它的对应原型,这样容易陷入死胡同,也曲解了作品本身的意义与韵味,文学艺术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依据。“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2]110,“实际生活经验在作家心目中究竟是什么样子,取决于它们在文学上的可取程度,由于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观念的左右,它们都发生了局部的变形。”[2]80也就是“文学高于生活”,它是作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一种超越和思考,是以文学的方式介入时代,并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百态的审视和反思,对人类未来的深层探索,对人性隐幽的剖析和多维度挖掘。
鲁迅坚持文学要面向生活,要求文人们要有正视社会现象的勇气:“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3]255鲁迅的一系列创作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即是这一要求的杰出体现。同样,沈从文也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品格:“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4]413“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人事’上面。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5]233无论是鲁迅笔下的鲁镇、未庄还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都对旧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思考。因此,要了解二三十年代的苦难中国,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恨悲欢,就不能绕开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写作,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可以了解到近百年来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并在憧憬未来乡村发展之时有个可贵的立足点。
二、乡土小说的界定与认识价值
早期关于乡土小说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的为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所指出的:“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6]这段文字透露出三点信息:第一,作者的地域性差异;第二,作品的地方性特色;第三,不尽的乡愁。茅盾则进一步指出:“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7]。这里除了指出乡土小说的地方性风土人情之外,也指出优秀作品对于时代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甘肃评论家雷达的看法更为具体:“我认为,所谓乡土文学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一、指描写农村生活的,而这农村又必定是养育过作家的那一片乡土的作品。这‘乡土’应该是作者的家乡一带。这就把一般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与乡土文学作品首先从外部特征上区别开来了。二、作者笔下的这一片乡土上,必定是有它与其他地域不同的,独特的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山川景物之类。三、作者笔下的这片乡土又是与整个时代、社会紧密地内在联系着,必有‘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或者换句话说,包含着丰富广泛的时代内容。”[8]这里认为乡土文学的要点有三:一为农村生活;二为地方风物人情;三为时代内容。进入新世纪,丁帆认为:“乡土小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干,‘乡土小说’的重要特征就在于‘风俗画描写’和‘地方色彩’”[9]1,并说“乡土小说一定是乡村、乡镇题材的作品,没有这一前提,乡土小说便是名存实亡的”[9]25。
可见,乡土小说的核心要素为:乡镇及农村题材,地方性风情习俗,乡愁,时代与人类命运的映射与思考等,而这些要素同时也是乡土小说认识价值的根本体现。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仅描写了地方性的客观之景,亦刻画了二三年代旧中国特定乡村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群像,并对当时的时代和个人命运作了深度剖析,呈现出一个有着共同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与信仰的社会共同体。阅读他们的作品,如杨义所说:“一代又一代会思考的中国人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古老的父母之邦的土地、空气和灵魂,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社会的血脉,探求着历史的遗迹何在,时代是否前进,从而获得智慧的启迪和审美的愉说。”[10]156
三、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认识价值的三维审视
乡村,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社会习俗等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让他们去爱、去感受、去生活,甚至去承受折磨和苦难,生老病死,代代相传。无论是鲁迅笔下的乡村世界还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地,他们都以杰出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独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风土民俗、人情冷暖等。不仅是一种精神文化存在,也是特定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礼仪制度以及信仰的鲜活载体,展现了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乡村儿女们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也表达了鲁迅和沈从文对自己所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深深的依恋与审视。
(一)时代风云的共名与超越
面对一个大的时代转折,一个优秀的作家不是写了什么,而是为什么写、为谁写、怎么写,这里就涉及到了作家的价值观与写作立场。鲁迅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11],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直面时代、迎难而上的写作立场。关于“作家与时代”这个人们时谈时新的命题,陈思和教授有一个精彩的概括,即“共名”:“所谓‘共名’是指一种时代的主题,它可以涵盖一个时代全⺠族的精神走向。”并说:“一个伟大作家,他是不会回避时代主题的;不仅不回避,他要包容、穿透这个时代主题,使自己的思想超越这个时代的共名”[12]58。
鲁迅和沈从文都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作出了杰出的反映,尤其是鲁迅的小说,就一些大事而言,中国的政治风云如辛亥革命、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等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出现,并以此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民的生活面貌,同时又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共名”。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药》,写出了以华老栓为代表的底层人生活的苦难以及骨子里的愚昧、麻木和自私,也写出了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的大义凛然,然而可悲的是如此视死如归的英雄,事后却被沦为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鲁迅以这两类人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写他对于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只是一些觉醒者以满腔热血去奉献、流血,是很难使革命走向成功的。另一篇以此为背景的小说《阿Q正传》,将无业游民阿Q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大背景下,写以阿Q为代表的底层中国人的苦难以及对革命本身的态度,以此来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国人根深蒂固的愚昧、自私、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鲁迅以阿Q这样的小人物来曲折反映时事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而不是以一些高官显贵之人来呈现,更能刺激读者设身处地去思考,发现自己身上何尝没有阿Q的影子。杨义先生说得好:“写一个慈禧太后尚不足以表达的东⻄,却只须写一个卑微的阿Q,就能够透视整个⺠族中无孔不入的病态心理特点了。”[10]165
相对于鲁迅以一个战士的姿态积极介入时代,并对时代的种种问题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反映与思考。沈从文仿佛是另一种形式,远远地逃离时代、躲避现实,沈从文对鲁迅有过很高的评价:“对统治者的不妥协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嘲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5]165,而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他却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要求,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5]376那么,沈从文是否只在诗意浪漫的文字中建造着自己的“希腊小庙”呢?答案是否定的。沈从文的这段坦言与其是说自己作品仿佛落后于时代,不如说是一种自谦。沈从文作为作家的黄金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此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跌宕、内忧外患的时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都以各种形式对中国将何处去作了相应的思考。只不过与鲁迅不一样,沈从文从另一方向来思考这个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的命运,在看到西方各种思想对人的侵蚀,以及都市男女思想与道德的下滑、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后,他便从民间寻找力量,以健康的人性和蓬勃的自然与生命力来与之抵抗,批判古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先天性不足。因此,在他的乡村题材的系列小说中,主人公多大胆地生活,勇敢地爱,自由而无束地舒展生命的力与美。用苏雪林那句有名的说法就是:“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3]这一独特的写作路向,使他从当时的作家群中脱颖而出,站在主流思潮的对立面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并没有完全回避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幻。在小说《菜园》中,曾经一个幸福的母亲,因儿子和进步青年惨死校场,后半生只能孤苦度日,在这背后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的白色恐怖,大量屠杀共产党员的恐怖事实。同样的背景在小说《新与旧》中也有体现,旧世界正在走向毁灭,新世界还未建立,人们在新与旧的时代夹缝中苦苦挣扎突围。部分乡土小说也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军阀统治时期底层劳动人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严峻现实。不可否认的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在触及一些时事时,尽量采取冷静描述的角度,很少透露出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情感倾向。他认为:“一个伟大纯粹艺术家或思想家的手和心,既比现实政治家更深刻并无偏见和成见的接触一切,因此它的产生和存在,有时若与某种思潮表面或相异,或独立,都极其自然。它的伟大存在,即于政治、宗教以外更形成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14]231沈从文的写作方式与鲁迅的写作方向尽管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体现了对民族前途的深层忧虑,对底层大众的深情关怀。两者互相补充,共同构筑了那个时代的民族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精神担当。
(二)社会现实的映射与审视
文学作品在社会层面的认识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读者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体悟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当地的风土民情并感知人物的命运起伏。法国史学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主要受种族、时代、环境三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他又特别强调地域及风俗对作家的影响作用。鲁迅的作品里有许多地方反映了家乡独特风俗人情,包括:地方化的动植物和工具——花脚蚊、乌桕树、芭蕉扇;特有的玩法——狗气杀、雪地捕鸟;许多风俗——拆灶捐门槛、社戏、迎神赛会;民间故事——“许仙和白娘子”“猫和老鼠”等。沈从文也一样,其作品多次提到湘西的山山水水、吊脚楼、船夫等、茶峒,“那黄泥的墙,乌黑的瓦”等。其中《边城》记录了两大民俗: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走马路与走车路的说媒方式。一些小说还描写了湘西乡村许多年轻男女之间的情爱,尤其是情歌对唱,展现了一种充满着原始生命活力又不乏浪漫的爱情,这对于处在新时代的年轻读者,无疑打开了一个新的界面,致使他们重新审视爱情、审视生活本身。而风俗的描写无不是以作家们的生活为基础,这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和当时人民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文献学意义和价值。
然而杰出的作家从不会止步于此,他不仅要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是怎样的,还要揭示为什么是这样的,即要刻画出社会的内在肌理与本质。《故乡》相对于鲁迅其他小说,忆旧色彩浓重,小说写到自己的玩伴少年闰土,脑海里有好多关于“捕鱼”“刺猹”“捡贝壳”等稀奇古怪的事,以至于作者在文章中惊讶道:“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 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3]504。可是如此爱玩会玩的闰土,在作者最后一次回故乡搬家的时候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手变得又粗又笨像松树皮,而且见我第一反应便是恭敬地叫了一声“老爷”。两组镜头,戏剧化的对比,将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承受的苦难与不公鲜活地呈现了出来,正如母亲和我的叹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3]508《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更是将封建旧社会强加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不公、冷酷及其所承受的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摧残深刻地表现了出来,揭示了深深压在旧社会女性身上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绳索。
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世界,不可否认,少了鲁迅的犀利、辛辣、嘲讽以及沉甸甸的痛感,但其一些作品亦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书写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只不过由于沈从文对于湘西这片土地深切的爱与他独特的写作追求和审美理想的过滤,使他作品呈现出别样的诗意和美,但底子确是悲剧的、苦涩的。其以“湘西”为核心的系列乡土小说不仅讴歌了乡民们敢爱敢恨、热烈大胆、奔放果敢的一面,也深刻批判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麻木自私和不自知。沈从文在小说《丈夫》中着重描写湘西边地的一种特殊风俗,年轻妇人通过做肉体生意挣钱养家,“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挖园的人家,离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轻而强健的丈夫的怀抱,跟随了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15]47-48这样一种不怎么光彩的行为不影响名分和健康,还可以改善自家的生活,以至于“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安分过日子,竟是极其平常的事了。”[15]48使妻成妓,这一典妻与卖淫相结合的勾当,却是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这畸形的生活方式背后,是社会的动荡不安、生活的不公带给良善的人们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和压迫,以至于使他们慢慢适应了这种不光彩的生活而变得麻木顺从,而在这背后则是二三十年代多灾多难的古老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
(三)人性隐幽的探索与挖掘
一个杰出的作家在写作时,不是对生活事件的简单刻画,而是要写出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对于个体留下了什么。要找出个体在历史中的位置,以及他的微笑与落寞、苦难与挣扎,这也是文学认识价值的体现,即在作品中要体现对个体的尊重、对生命的思考、对苦难的反思、对人性的审视、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毫无疑问,乡土小说主要是将写作目光聚焦于那一片土地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都将“人”作为小说的重点,写出了一曲曲荡气回肠又发人深思的人性悲歌。
鲁迅作品始终以“立人”作为写作核心。所谓欲立先破,如何才能让一个人真正的“立”住,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要正视他、走进他、理解他、挖掘他,甚至解剖他。鲁迅的乡土小说,以普通人的平常悲剧入手,迫使读者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 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3]3-4
鲁迅的乡土小说里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演戏也看戏,生活单调枯燥,却总是不忘在其中加点料。而由于演戏是将自己置身于一个被“观”的情境中,多少有点孤单无助,因此鲁迅小说描写更多的是看客,他们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祝福》中,人们起初还对祥林嫂有点同情,为她打抱不平,但当她的故事被人们所熟知,并且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倾诉自己悲惨的遭遇,人们便感到厌烦,鲁迅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写到:“她就只是反复地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16]可见人们对于祥林嫂的看法不是出于同情和热心,而是生活本身的无聊和单调。鲁迅的其他小说如《示众》《药》中亦不乏大量的看客形象。钱理群先生甚至认为:“看戏(看别人)和演戏(被别人看)就成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17]。尽管程度不同、形象各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点:刻薄狠毒、自私冷漠,且单调无聊、欺软怕硬,缺乏独立思考,试图在群体的行动中获取安全感的最大状态,以释放出平常生活中被压抑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在不自觉中竟也扮演了吃人的角色。陈思和指出:“吃人是一种社会环境,人人都有份。这涉及到群众暴力的问题。”[12]49-50这样的群众暴力是古老中国大地上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是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之下对弱者的隐形伤害。
对于人性的探索,沈从文同样看到了人性的异化:“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灭。因此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都庸俗呆笨,了无趣味。某种人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14]32也许是因为他常将自己定位为“乡下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他执着地构建“希腊小庙”的艺术努力,使他对底层大众充满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同情与关心。这一方面使沈从文的人物形象更加舒朗健康,带给读者审美的快感,但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他对人物作更深层次的剖析,也因此其小说中的人物少了鲁迅笔下的压抑木讷和无奈沉重。
《边城》中的翠翠聪明伶俐、单纯可人,仿佛是大自然的女儿;老船夫则辛劳本分、善良忠厚,不贪图便宜,有求必应;船总顺顺生财有道、正直平和。整个小说的气氛宁谧自在且诗意浪漫。《萧萧》里面的女主人公萧萧,可以说是古老中国农村童养媳制度的牺牲品,年仅12岁就嫁给了刚断奶还不到3岁的幼童做童养媳,生活忙碌却不繁重,尽管因为没经得住诱惑做了在当时看来伤风败俗的事,但她并没有被夫家及村人逼到绝境甚至死去,最后竟也和丈夫正式拜堂圆房。这让我们不得不想起萧红笔下的小团圆媳妇,同样为童养媳,一个被残忍对待以致死亡,一个则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在萧红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冷漠、无知、愚昧和残忍。而在沈从文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性闪光的一面:温暖、良善、友爱、纯朴,人性的美稀释了主人公坎坷命运,温情的人际关系淡化了封建旧制度对人的禁锢。至于其他人物形象,夭夭、三三、贵生、龙朱、水手等,女性多善良温柔、柔情似水、敢爱敢恨;男性则坚韧顽强、果敢有力;甚至妓女也充满了人情味;土匪并非无恶不作、杀人放火,相反他们杀富济贫,仗义疏财。尽管沈从文笔下人物也有缺点和不足,但整个人性的底色是饱满的。
相比较而言,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要比鲁迅笔下的人物更健康、充满活力,更具有人性和血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沈从文笔下人物的生存环境要比鲁迅笔下人物的生存环境更开放,那种来自自然本身的原始之力较为浓郁;二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湘西边地百姓所受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封建礼教的程度要远远低于鲁迅笔下生活在鲁镇的人们;三是作者的写作立场不一样。鲁迅以笔作匕首,剖开人性的纵深,写出了人物的灵魂。沈从文则是从伦理道德和审美的角度,在湘西这块土地上找寻现代文明中即将失落的理想人性,以近乎原始主义的书写姿势构建他的“希腊小庙”。张新颖先生说得好:“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的人性,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18]鲁迅以批判的眼光看到了人性幽暗且懦弱的一面,而沈从文则以诗意的笔调讴歌健全的人性。
两种不同的人性呈现,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令人叹惋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在今天并没有改变多少,而是在时代的发展中包装成了新的“看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重新走进鲁迅的乡土系列小说,去感受其中人物的爱恨与悲欢,并从中去思考社会的本质和人性的本来面目。而当我们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和各种利益诱惑,盘算着各种利害关系与得失时,对比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也许可以审视自己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从而进一步认识自己以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本身。
四、结语
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真实地展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古老中国面对时代的风云变幻所作出的艰难努力,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中华儿女们的挣扎与守望、疲弱与健全,并以其杰出的笔调刻画出不同的生命情状和人的精神世界。作家笔下的那一方乡土,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缩影,以其独特的样貌,传达出处于时代大变革时期的作家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反思、对国家和个体命运的深层忧虑,不仅深刻地影响以后的文学创作,更启发着不同时代的读者以此为镜,反观自身,认识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
参考文献:
[1]狄其骢,王汶成,凌晨光.文艺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6.
[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3]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13.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5.
[7]茅盾.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241.
[8]雷达,刘绍棠.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J].鸭绿江,1982 (1):69-74.
[9]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1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2.
[12]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3]苏雪林.苏雪林选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456.
[1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6]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18.
[17]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8.
[18]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