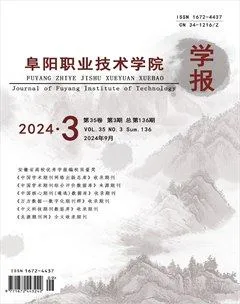论人“神”关系背景下刘慈欣小说中的人性主题
摘要:人性作为科幻作家刘慈欣小说中的常见主题,集中体现于《三体》系列作品及作者众多短篇创作中。刘慈欣小说中的人性主题分别体现于宇宙生存图景和宇宙发展图景中。其中,人“神”生存图景体现刘慈欣以人性作为人与外星生物区分的重要准则,并以之为基准设想宇宙间物种的生存关系;人“神”发展图景则体现刘慈欣对人性普适性的理解,并由此引申出对宇宙发展的终极拷问。人性的存在,在宇宙生存图景与发展图景中分别起到不同作用,这将成为解读一些特殊角色和追问小说深层内容的关键,也将成为挖掘作者对于人性认知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人性;人与“神”;黑暗森林;刘慈欣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24)03-0038-07
近年来,国内外(以国内为主)对刘慈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作品的文学史意义、译介工作及主要作品的主题和思想上,而对于刘慈欣作品频繁出现的“神”的意象则很少提及。从小说内容看,“神”是人类对无法匹敌的文明程度(科技实力)的代称。与国内外流行的“外星人”科幻主题一样,刘慈欣在其长篇小说《三体》及许多短篇小说中均描绘不同种类样貌的外星生物。外星生物从未出现,人类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许多科幻电影或小说常采用“类人”形象,即从人的样貌和生活习惯出发,将外星生物的形象置于以人为原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想象。而刘慈欣笔下的外星生物则更为“随意”,它们有的无法为人所观测,有的外形类似恐龙,有如白发慈祥的“上帝”形象,也有能随意脱水补水的“三体”人。形象的各异并不影响其文明程度的发达,作者笔下外星生物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文明程度相较于人类的领先,于小说中的人类而言,其文明水平(主要集中在科技层面)已成为令人赞叹和不解的存在,正如刘慈欣赞赏的科幻作家克拉克在其小说《2001:太空漫游》中所描绘的绝对比例的长方体,以其无需质疑的精确度无声地与人类技术水平拉开距离[[1]]。刘慈欣的“外星人”形象不再与人类在同一水平线上交流,它们成为令人仰望的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精神寄托的载体,如《三体Ⅲ:死神永生》中众人跪倒在作为三体文明代言人的“智子”脚下,企望它能为地球的出路提供指引[2]。可以说,“神”在小说中是以科技水平为支撑、借以在人类心中树立无可匹敌形象的外星生命体的统称。
然而,对人“神”形象及关系的分析不能仅限于表面,刘慈欣对人与“神”两类形象的描述依旧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其中“人性”,这一包括情感(共情)、计谋(欺骗)、自私(利己)等特征的属性,在人与“神”的对比中显得尤为突出,而“人性”主题的重要性同样在差别对立的描写中彰显无遗。
一、人“神”生存图景——以人性为划分准则
(一)人眼中“神”的形象
刘慈欣小说中的“神”没有古希腊神话中“神”近乎完美的体型,它们在人类眼中的威严建立在其科技水平领先所形成的神秘感和给人的危机感上。刘慈欣多以人类视角描述“神”形象。《诗云》中,“神一族”在人类的眼中“仿佛是从计算机图库中取出的两个元素,是这纷乱宇宙中两个简明而抽象的概念”[3]45;《梦之海》中,“低温艺术家”的形象无法用肉眼观察,只能看到由于其冷冻场产生的冰球[3]3;《山》中,来自“泡世界”的生命体由机械构成,短路对于它们便意味着死亡[3]354-355;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吞食帝国”的外形为恐龙的“大牙”,来自三体世界的三体人等。此类生命体普遍具有以下共同点:文明发展程度较高;外形不同于人类;能与人沟通。宋明炜曾在《中国科幻新浪潮》中提出,刘慈欣的小说是在某种设想、前提下,在科学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严谨推理产生的[4]35,这也符合他“硬科幻”的评价。而在人“神”接触并产生互动的叙述中,以上三点能大致构成“神”形象的基本前提。
而另一个描写的相似点似乎更需要引人关注——人“神”发生交流后,“神”对人的态度基本保持一致,冷漠、不屑是其感情基调。如《梦之海》和《山》中的“神”,其文明处于人类难以想象的水平,它们甚至不愿以“虫子”称呼人类;它们能轻易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理由仅仅是满足自己的艺术创作。而那些人类稍能理解的文明里,不屑、不顾依旧是主色调,《三体》中三体世界对三位面壁者和地球文明发出“主不在乎”的嘲讽以及“毁灭你,又与你何干”的不屑;《山》里机械文明掀起地球的排天巨浪,只是为了寻找能沟通的使者。如果说“神”的文明水平、外形等是作者预先设立好的条件,是小说得以推动的起点,那么“神”对人态度的一致性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以人性角度考虑,即使双方实力存在较大差距,良好的交流、合作仍是存在可能的,但“神”的反“人性”说明了在刘慈欣小说的宇宙观里,一直存在某种写作准则和规律,它能使高等文明同低等文明的谈话推演出不屑、冷漠的态度,而此“神性”与“人性”的不同之处,成为区分人与“神”的主要依据。
(二)“非人”与“神”:《三体》“非人”与短篇中的“神”对比
“非人”概念来自小说《三体》,当小说人物章北海驾驶“自然选择”号战舰逃离地球、飞往外太空时,战舰中的人虽然逃避三体探测器“水滴”的追杀,但由于回归地球的希望被完全切断,他们的精神状态将会发生完全变化,舰长东方延绪以“非人”来称呼此类人。“非人”保留人的外形、习惯,但丧失了最基础的“人性”。“非人”为了生存竭尽所能,不惜杀害同类。“非人”的存在,无异于太空中独立生活的一个群体。从人变为“非人”,刘慈欣形象说明了建立在技术爆炸和猜疑链基础上的宇宙“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是对“费米悖论”的形象化说明,《三体》如此描述:“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宇宙文明的图景”[5]446。舰体上的“非人”,与小说中其他“神”的形象有些出入,他们本就是人类,只因为身处“黑暗森林”的宇宙规则之下,一些人性被迫泯灭——他们无暇顾及对别的舰队的同情,满脑子只有猜疑和算计;章北海在关键时刻动的恻隐之心,导致了整艘战舰的覆灭。“非人”形象的提出,使小说人物除人和“神”外又新增了一类,他们兼具两者的共同点,既有“神”的冷漠,又带有人的习惯和文明,其与“神”的对比,恰恰可以说明人性在刘慈欣小说中的重要位置。
首先,对“非人”的描写,从根本上阐明了人性是人与其他生命区分的主要依据。吴飞在《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中指出,那些被人认为的“神”一般的生命,其实只是拥有神一般科技的敌人[6]26。小说中的“神”不再是庇护人类的形象,而是无情的杀戮者和征服者,人们对“神”的敬畏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这不免让人联想“神”是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虽然作者并未在小说中说明,但从其中一些片段我们仍能发现,作者对科技改造人性持否定态度。如《三体Ⅱ:黑暗森林》中,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经历“大低谷”,仍有人提出“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5]309;经历低谷后人类科技迎来大反弹,地球并没有成为战争的试炼场,而是向民主和自由的方向迈进。无论处于低谷还是高峰,刘慈欣笔下的人类社会发展都处于读者的理解范围之中,换言之,即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可以接受如此的变化。而作者的精妙之处在于,他用同样易于理解的“黑暗森林”法则,阐述了宇宙的真理,使得舰队上“非人”的举动既在常理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小说如此描写“非人”的境遇:“以前,不管人类在太空中飞多远,只是地球放出的风筝,有一根精神之线把他们与地球相连,现在这根线断了。”[5]410人性是与地球相连的,是与“黑暗森林”相对的,当地球不再适合返航,航行变成几乎漫无目的的前进时,人类便会在“黑暗森林”中丧失一部分人性。
其次,“非人”与“神”的区别也说明了人性之于“黑暗森林”的独特。小说中,二者的最大区别并不在科技实力上,从宇宙的宏观视角看,人类与“三体人”的科技差距可忽略不计,但“三体人”之所以可归为“神”,主要在于它们对“黑暗森林”理论的参透。“黑暗森林”的比喻中,二者都可视为婴儿级别的文明,但不同在于人类还是引火自焚、主动暴露自己的“傻孩子”,而“三体人”已经是隐没在黑暗中、端着猎枪的孩童。刘慈欣在提出这般宇宙图景时,将人类与地球放在最为特殊且幸运的一点——绝大多数人不了解宇宙法则的情况下,人类尚未受到“黑暗森林”的打击与制裁。“非人”与“神”的最大区别在于,“神”已把宇宙法则视为公理时,“非人”则刚经历从人性到“黑暗森林”的转变,舰长的自杀、章北海的犹豫,及大多数船员的抑郁,虽纠人心弦,但也从侧面证明人性相对于宇宙的独一无二。
因此,在人与“非人”,或者说人与科技水平较高的“非人”的对比中,能否领悟宇宙的“黑暗森林”法则,以及是否收到“黑暗森林”的威胁,成为两者最大的区别。“黑暗森林”法则下勾心斗角的宇宙,被宋明炜概括为“以生存为第一要义的‘现实主义’或‘犬儒主义’”[4]31。而这种“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能为人所理解接受,因为其对应人性的某一部分,比如对生存的第一需求、对敌人的猜疑等。实际上,刘慈欣的小说还涉及另一类“神”,它们脱离了“现实主义”,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在生存的约束之下,而是生存对于它们来说是近乎永恒和易得的,如《梦之海》中的“低温艺术家”脱离了肉体的束缚,驾驶以光速航行的飞船,在各星球间寻找艺术创作灵感。虽然它同样置身于法则之下,但相当高程度的科技水平使得它能很好地躲避威胁、维持生存,即完全游刃于宇宙法则之中。它在面对地球世界时,并没有因实力领先过大而表现出应有的人性的“善意”,而是尽可能地减少了除艺术之外的谈论话题,为了它心中的艺术作品,毁灭整个星球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说宇宙“黑暗森林”的“零道德”是对标人类社会“道德”的结果,那么刘慈欣描写的“神”中,当文明发展越趋近于顶端,“道德”就越将失去它的约束作用和标示意义,真正的生存规则将越向宇宙生存法则靠拢。《三体》中的三体世界,因其所处行星受三颗恒星不规律运动的困扰,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由此演化出思想透明、高度中央集权的群体。他们的情感很少有恐惧、逃避等因素,即使家园最后还是惨遭毁灭,身为三体世界代表的“智子”依旧表现平静,而对于它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欺骗”,在与人类世界周旋的几百年中也逐渐融入其思想。它们的特性与人性相比的不同,是由强烈的生存需求导致的,目的是更好地应对灾难、更快地占领“殖民地”。而对于《梦之海》《诗云》中超脱肉身的“神”,欺骗变得没有必要,就如“低温艺术家”所言:“生存,咄咄,它只是文明的婴儿时期要换的尿布,以后,它就像呼吸一样轻而易举了”[3]11。“神”表现的态度如何,是否与我们认知中的逻辑匹配,其实都是从人性出发、以人性为参照物的结果。文明水平相近或相差不远的“非人”和“神”身上,或多或少有人性的影子,而在遥不可及的“神”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全宇宙普遍适用的生存标准。吴飞曾说明,宇宙概念里的“善”指虽有星际航行的能力,却选择在自己星球上生存,不去打扰他者[6]52-53。以此观之,所有造访地球的“神”都没有达到宇宙的“善”,人类又有何能以人性标榜,企图以人性衡量和制约其他生命呢?
(三)“黑暗森林”与人性的闪耀
当然,刘慈欣描写的由“费米悖论”引发的“黑暗森林”图景,终究是作为科幻小说的一种想象,宇宙是否处于“举目皆敌”的拥挤状态尤未可知。前文也已提及,刘慈欣的小说是在假设的基础上经过逻辑推理而创作的,这也使得其小说的许多细节能前后呼应,以及一些重要观点的提出有其明显的作用与意义。例如《三体》中作为面壁者之一的雷迪亚兹,在某个黄昏见到夕阳后患上了“恐日症”,而这正与其面壁计划相关。实际上,作者在小说中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对人性主题同样有凸显作用。
刘慈欣小说中的人类,以《三体》主人公之一罗辑的话来说,就如同“黑暗森林中的傻孩子”[5]447。《三体》里罗辑通过叶文洁的提示悟出了宇宙终极理论,但全人类对宇宙依旧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即使之后“黑暗森林”被大家熟知,仍有人身处太平岁月而选择将其遗忘。刘慈欣其他短篇小说,虽未提及“黑暗森林”,但人类无一例外是被动的、毫无准备的接受者形象:被迫与“神”交流,从而得知宇宙的某些真理或无抵抗地被“神”取走其需要之物。就如前文所说,人类与地球仿佛是一座自生自灭、同时又自融自洽的孤岛,在周围的“神”已形成发达的“海洋文明”时,“闭关”的人类还在苦苦思索“出关”之道。刘慈欣在谈及《三体》及《流浪地球》等小说创作过程时说:“这一阶段的共同特点,就是同时描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灰色的,充满着尘世的喧嚣,为我们所熟悉;另一个是空灵的科幻世界,在最遥远的远方和最微小的尺度中,是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这两个世界的接触和碰撞,它们强烈的反差,构成了故事的主体。”[7]由是观之,所谓的人与“非人”、人与“神”的区别,不如说是地球与宇宙、“傻孩子”与“黑暗森林”的对比。“黑暗森林”法则将人性所处的境地具象化,同时将不同于人性的“神性”和“非人性”模糊化、背景化——结合小说中人类面对“神”的被动,人性与其他“性”的区分更加清晰,随之而来的是孤独感与独特感的加强。在对人性位置的独立进行强调后,小说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也可得到更好的阐释。
人性位置的独立也引发了另一个疑问:难道宇宙中没有和人类相似甚至相同特性的生命吗?在小说未提及的外星生物中,是否存在相似的“人”尚未可知,而出场的“神”均有一个相同点:他们不远万里前来地球造访。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懂得“黑暗森林”法则,也知道如何运用法则并在它之下生存。无论这些种群在开始星际航行之前具有怎样的特性,一旦融入宇宙法则之中,就决定了其与人性不相容。这也是刘慈欣为何很少畅想人类踏入星际旅途的未来,因为单以《三体》中“自然选择”号等四艘舰体为例,就能看出人性将在太空中发生怎样的扭曲和异变。“黑暗森林”法则设立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几乎给宇宙中所有高等文明附加了“人性异变”的大前提,这使得小说能在人性与“黑暗森林”图景二者的比较中展开。
此外,对于处在家园星球、未外出航行的生命的描写,最有代表意义的须属“三体人”。《三体》里“三体”文明通过一款拟真游戏,向主角汪淼讲述了“三体人”生存环境之恶劣,这也为三体舰队出征地球奠下基调。地球上之所以能发展出健全的法律制度、道德规章和普遍的人性,不仅在于“猜疑链”的不成立,还在于大多数人的生存能被满足。《三体》中罗辑曾说:“猜疑链只能延伸一至两层就会被交流所消解”[5]444,在有效、可靠的交流下,猜疑不攻自破,“黑暗森林”也难以成立,而“三体人”几乎全透明的沟通更是保证这一点,可惜它们的生存发展远没有地球稳定。可以说,“三体人”是在半逼迫下接触宇宙法则。此外,刘莘在《宇宙的真理——刘慈欣科幻文学解读》里提出了“伦理共同体”,这成为人性与“三体人性”之间的另一道鸿沟——就像我们对待狗和蚊子有不同的道德规则一样,不同物种间的交流取决于两者伦理联系的紧密程度,人类是否在伦理上与“三体人”有较大关联、人类是否全面了解“三体人”,以及“三体人”会如何看待人类,本质上构成了伦理关系上的“猜疑链”,两个种群注定无法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8]。
二、人“神”发展图景——人性的普适性
(一)人与“神”的共通之处:《山》中的宇宙发展图景
人性与“神性”相隔,并不代表二者没有共同点。情感、思维难以达到统一时,人类却和“神”有着相似的好奇心,包括对已知世界之外空间的探索、对真理的追求,这类探求的欲望在刘慈欣的笔下,是全宇宙共有的特性。如《山》中的机械文明,当其祖先生活在狭小的“泡世界”时,一代代的进化使其“走到了对宇宙进行思考的那一天”[3]347,对“泡世界”之外空间的想象成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并引发了对外探索的狂潮,这与人类对太空的畅想和开拓何其相像;《朝闻道》里的“排险者”,作为宇宙的最高智慧体,掌握着一切真理,仍无奈于对宇宙终极意义的无知;《诗云》里的“神族”认为“龙族”无法向更高维度进发的原因在于其缺少对周遭的好奇心。正是这些好奇趋使不同生命体朝自己理想的远方努力,从而构成刘慈欣小说异彩纷呈的宇宙发展图景。
发展不同于生存,不是生命的必需品,但却是所有生物的本性。《山》曾以“登山”来比喻生命向高处进发:“登山是智慧生物的一个本性,他们都想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这并不是生存的需要。比如你,如果为了生存就会远远逃离这山,可你却登上来了。”[3]360当《山》的主人公冯帆体验过“海上顶峰”的感觉时,“他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怕死的人。他攀登过岩石的世界屋脊,这次又登上了海水构成的世界最高峰,下次会登什么样的山呢?”[3]362欲望是无止境的,攀上了这座山头,欲望会使你遥望更高的山头,即使攀爬的代价很大,依旧会有人冒着无法生存的风险去尝试,就像《山》里的机械生命抱着无法返程的决心开凿岩石,也像《朝闻道》里的精英们以生命换取对宇宙真理的片刻拥有。由此,刘慈欣在“黑暗森林”的生存图景之外,刻画出另一幅发展景象——不同生命在各自星球或太空中,因对未知的好奇而奋发向前,形成“百舸争流”的喧闹局面,宇宙在读者眼中不再变得寂静冷清。
(二)“无意义”存活的“神”
刘慈欣小说中还存在另一类角色,它们在作者的描述下显得“无欲无求”,它们的“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存活”,读者很难从其言行中看到活着的意义。这类“神”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如前面所述,如《梦之海》的“低温艺术家”和《诗云》的“神族”,生存对于它们不再是需要苦苦追求的东西,因此两者不约而同地将兴趣转至“艺术”和“文学”,通过获取其他行星的资源满足创作需求;另一种的代表为《三体》中的“歌者”文明,通过不断将自己与敌人降维,达到消除威胁、维持生存的目的。一个整日于太空游荡来获取艺术灵感,一个宁愿将自己从高维度降至平面化也要保持存活,从人的角度思考,它们的生活缺乏“意义”,也就是探索和向上进取的好奇心。
设置技术、实力深不可测的文明,根本上是为了创造人“神”对峙或交流的大前提,这也是刘慈欣乃至许多科幻小说的写作方式。而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无意义”的“神”实际为人性的最大程度想象创造了空间。
首先,“神族”和“低温艺术家”为“人”披上了最高技术的外衣。无论《三体》提出的“黑暗森林”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小说,“神族”和“低温艺术家”所表现出的,并非如宇宙法则所说的立刻对地球进行毁灭性打击,相反,它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与人类进行交涉谈判。尽管技术不处于一个层面,谈判往往以“神”的意愿为准,但它们的表现已经展现出人类的共情一面。更为有趣的是,《诗云》有将“神族”附身于唐代诗人李白的设定,作者如此描写化身为人且喝醉的“神”:“李白的嘴上黑乎乎的全是墨,这是因为在喝光第四碗后,他曾试图在纸上写什么,但只是把蘸饱墨的毛笔重重地溅到桌面上,接着,李白就像初学书法的小孩那样,试图用嘴把笔理顺……‘尊敬的神?’大牙伏下身来小心翼翼地问。‘哇咦卡啊……卡啊咦唉哇。’李白大着舌头说。”[3]55-56这段让人忍俊不禁的文字不仅说明当“神”褪去科技的外衣、回归肉身后,与常人行为并无差别,也从侧面说明在排除“黑暗森林”的影响后,人性并不会随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升华,甚至可以说人性的发展仍在原地徘徊。
其次,“歌者”为人性提供了揣测“神性”的空间。“黑暗森林”法则下的“歌者”,尽管手握可以二维化整个宇宙的“二向箔”,但是自己也终将被其反噬,沦为二维生物。这也正是为人所不解之处:平面化地存活,真的有意义吗?而这恰恰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刘慈欣的所有人“神”叙事,都基于对“神”的想象,也就是从人性角度去揣摩“神”的思维。一方面,作者和读者都是人,在没有经历任何外星遭遇、且要保证小说逻辑能在人类逻辑框架里发展的情况下,从人性角度出发是唯一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我们能也仅能从人性出发去理解“神”,这使得小说中“神”的行为都是以人性为标准进行批判——努力向上攀登,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正常的发展图景。对于某些生命来说,生存就代表意义吗?我们尤未可知。
最后,刘慈欣《山》中讲到:“山无处不在,我们都还在山脚下。”[3]360《山》中的表述指明了人性的想象限度。山脚下的人很难领略到山顶的风景,就像进入四维空间的三维人类一样,无法用语言表述感受。因此,从人性出发,无论从思考角度还是高度来看都有很大的局限。尽管如此,刘慈欣在描述“神”时仍掺杂了很大的“便利”,我们能以人的视角理解小说中“神”的行为,本身就是神奇且幸运的事,这一描写角度也进一步证明了刘慈欣小说中人性的普适性。
(三)发展图景引来的终极询问:宇宙是否有意义?
如果把人性的普适性理解为对未知探索的欲望,那么这种欲望的来源便成为一个疑问,正如《山》所言:“进化赋予智慧文明登高的欲望是有更深的原因的,这原因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3]360也是当《朝闻道》里的霍金先生问出“宇宙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时,无所不知的“排险者”第一次沉默的原因[9]。我们可以说询问宇宙的目的、宇宙让人充满欲望的意义这类终极问题,仍是从人性出发的思考,或许宇宙只是如此存在着,但可以肯定的是,刘慈欣将科幻文学的尽头引向了哲学思考,这是发达科技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将人们对生存意义的思考上升至全宇宙,无论结果如何、无论有无意义,都是人性对所能想象的最大限度问题的探寻。这种询问,如宋明炜所言,对于刘慈欣来说,“科幻小说的终极理想,就体现在描绘崇高的体验中。”[4]120
三、人性之余
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人性主题比人“神”主题涉及面更广,几乎分布于每篇小说。而通过对人“神”生存图景和发展图景的分析,小说中人性存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更加清晰地展现眼前。人性主题的表达,对小说写作倾向的表示、思想内容的阐明以及对现实的预警都有重要意义。
(一)《三体》与《微纪元》:人类的乌托邦
刘慈欣曾在《三体Ⅱ》里写道:“即使在毁灭性的三体危机面前,人类大同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5]31的确,每个个性不同的人能相互理解包容、共同认可一些规章制度,共同组建成社会和国家,本身已十分不易,就如吴飞在《生命的深度》中所言:“地球上的人类通过社会政治制度,不必攻击也能存活,这是黑暗森林的最大奇迹。”[6]57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刘慈欣的写作倾向仍朝着人类大同而去。
这种写作倾向与小说内在逻辑和作者主观感情均有关系。首先,人类在小说的处境是被迫、弱势的,“神”的到来往往决定整个地球的命运,因此国际的划分被削去了,人类必须组成共同体面对来者;其次,贯穿小说的人性作为粘合剂,概括了全人类共有的特征,从天性方面进一步加深人类的聚合;最后,刘慈欣的主观倾向起着最大作用。《中国科幻新浪潮》指出,刘慈欣不同于韩松的“中国崛起”主题,他的科幻小说更偏重于“后人类叙事”,这使得其并不会在小说中刻意强调政治、种族、地域的划分,相反,还会有意规避[4]16。体现在小说中,除人类被迫团结抗敌外,《三体》中未来人类的中英文混用、地球国际国家实力普遍削弱、太空舰队没有地域概念所属、全球人集体搬迁澳洲等预言一次次将现有的国家划分冲碎;在小说结尾,程心写下“与宇宙命运融为一体”,从而“召唤出了‘终极乌托邦’”,人和宇宙在归零和重启中合二为一[10]。
刘慈欣是否存在主观的“乌托邦”倾向很难判定,因为其写作倾向正如小说中的人类一般,有些被动与无奈,在“后人类”与“神”两个主题面前,特别是人“神”二元对立的结构中,乌托邦式社会似乎已成定局,同时乌托邦的倾向有助于人类联系更紧密、表现更一致,从而深化人性的主题;而在作者另一篇小说《微纪元》中,人类为了躲避灾难将自己无限缩小,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微型社会。结尾原人类火化胚胎,实际是对原有的人类世界和人性作最后的告别。看似没有烦恼的“乌托邦”,在失去人性后,也成为了恐怖的“恶托邦”。由此,人性成为乌托邦理想的基石,也是人类社会叙事得以延续的基础。
(二)人性与科技:对人性的最后坚守
刘慈欣小说的人“神”叙事之所以能够进行,很大程度得益于小说中人“神”的友好沟通。除《三体》中恒星被类光速粒子快速击穿以及“二向箔”平面化太阳系外,我们很少再能见到外星文明对地球及其他星球的快速打击。这当然是出于人“神”叙事的需要,但要维持人“神”表面上的平等交流,人类必须拿出自己的优势。于是,刘慈欣又瞄准了人性。
《三体》中的“面壁计划”是人性优势最充分表达的一次,利用“三体人”没有计谋的特性,面壁者试图通过自我思考来躲避智子的监视和破壁人的猜测,但大多数面壁者仍败给了同为人类的破壁人,只有不受关注且自我“破壁”的罗辑取得了成功;《诗云》中“神族”企图用科技的力量穷尽诗句的组合,最终败给了人特有的创造力和对诗的鉴赏力,这是人在艺术鉴赏上的胜利;《梦之海》中的人类相比“低温艺术家”,虽同是取冰创造“艺术”,一个竭尽所有水资源而不顾全人类死活,一个“只取一瓢”用作欣赏,人性的共情展露无疑。刘慈欣没有直接说明科技与人性孰优孰劣,但他“硬科幻”的叙事往往落脚于人文关怀,人性、文化显然是他留给人类社会的底牌,作为可能与“神”一较高下的特性存在。
作者也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了提示,《三体》中“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5]409点出从人性出发思考的局限;吴飞在《生命的深度》中也指出,由于罗辑对人类世界的成功保护,人们渐渐忘记其存在的重要性,甚至怀疑“黑暗森林”的真实性[6]126。只有当危险来到眼前时,人类才知道害怕,才会去寻找救世主,甚至相信人类必将存活,人性的懒惰、安逸、自大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
结语
科幻文学之所以被称为“文学”,而非科幻想象或科学理论,是因为其作品的落脚点最后在人,文学最终是“人学”,本质上,刘慈欣与自“五四”始的现代文学传统并无差别,这也是本文为何选择以人性主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与传统文学的相异之处在于,他不仅将目光放置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更将其投向遥远的未知,试图在宏伟的想象、瑰丽的图景与可能的预测中探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种探讨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不失为可叹的理想。
经本文的论述,可见刘慈欣小说中的人性主题以或隐或显的姿态分布小说之中,以人“神”关系为切入点,不仅能在人与“神”的对立统一中发掘、凸显人性,而且能在人性与科技、地球与宇宙等比较讨论中发现作者的写作倾向和对人性主题的认识,从而逐步靠近作者在科幻写作中想要构建的宇宙图景和人类社会。
刘慈欣的创作伴随着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经历了逐步繁荣的二十余年。用刘慈欣的话来说,“在中国,科幻在大众中还是一支旷野上的小烛苗,一阵不大的风都能将它吹灭”[11]。笔者从刘慈欣的小说入手,试图在内容与主题方面对其做一些讨论与拓展,并希望中国科幻文学能愈燃愈旺,渐成星火燎原。
参考文献:
[1]阿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M].郝明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2]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253.
[3]刘慈欣.梦之海: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Ⅱ[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4]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5]刘慈欣.三体Ⅱ:黑暗森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6]吴飞.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
[7]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J].南方文坛,2010(6):31-33.
[8]刘莘.宇宙的真理:刘慈欣科幻文学解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9]刘慈欣.带上她的眼睛:刘慈欣科幻短篇小说集Ⅰ[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10]杨宸.从“终极乌托邦”到“宇宙中的人”[D].北京:北京大学,2016.
[11]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J].科普研究,201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