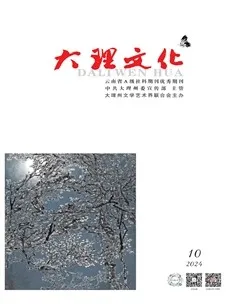吾辈亦当“朝洱海而暮苍山”
“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
银苍玉洱,乃大理胜景。品读《滇游日记》,一路向西去大理,重走“徐霞客之路”,踵其步而畅游,吾辈亦当“朝洱海而暮苍山”,在苍洱游踪中印证人事物景,体味情理意境,以言践行,以行践言,以了其愿,以慰平生。
找“油鱼洞”之奇,寻“上关花”之谜,见“蝴蝶泉”之异
三月初十,“游圣”出邓川驿后依西山南下,下渡峡口,过坊逾坡南行,来到接近洱海的油鱼洞。对于油鱼洞所处的“庙崖曲之间”的地貌特征,生动地用“水石交薄,崆峒透漏”来形容,真可谓奇人遇奇境而成奇句也。而“崖之后”的石耸片,则用“如芙蓉裂瓣”来描述,足见其心细周密,观察岩洞周边地貌的细微之处。
傍观必审。他还发现“盖其下亦有细穴潜通洱海”和“亦有水外通,与海波同为消长焉”的岩溶现象。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油鱼洞为什么会“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其中”,而“过十月,复乌有矣”的缘由。那就是每年秋冬季节,洱海里的油鱼都有洄游繁殖的习性。而油鱼洞温润适度,洞深水暗,蜂窝状岩穴交错,石苔藻多,拥有适宜油鱼产卵繁殖的自然环境。
油鱼“为此中第一味”。“游圣”有幸闻其说而见其身,却没有福气食其鱼而尝其味。特别对于油鱼豆腐汤这一美食,或许也因没有食味而成为“未了之兴”中的又一憾。
因其阙憾,所以哀其不幸。“游圣”抵达之际更是不逢时,也错过了民俗盛宴“渔潭会”。
“南崖之下,有油鱼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树,皆为此中奇胜。”从游记中我们可以知晓,“游圣”在尚未开启苍洱之行前,早已对“土人谓之‘十里香’”听闻许多,期待已久。从“南瞻沙坪”到“望所谓三家村”,也可读出他翘首跂踵、望眼欲穿的急盼心情。为尽快一睹“奇树”之容,他甚至还做出“急令仆担先觅寓具餐,余并探此而后中食”的决定。这也足见,“游圣”宁可中食之时饥肠辘辘,也要尽兴而游的求真精神。
而在询问“老妪”,按所指“至其下”后,“游圣”还借机转告我们“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以此,用来说明除了“上关以此花著”,“风花雪月”更是各有千秋,魅力无限,值此一游。
“来去匆匆,怎能品出‘风花雪月’的味儿呢?”
是啊!就连现代著名作家曹靖华在游过大理之后,也同样会对“风花雪月”美景说出这句耐人寻味的感叹之语。甚至,他还曾赋留“风花雪月”诗一首:“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照苍山雪。”
有幸读过《洱海一枝春》,作者能够把抒情散文当作游记来写,或许与《徐霞客游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其树高临深岸,而南干半空,矗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庙奇树之半,而叶亦差小。其花黄白色,大如莲,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闰增一瓣,与省会之说同;但开时香闻远甚,土人谓之‘十里香’,则省中所未闻也。”
这是“游圣”现场观看“上关花”时留下的情景定格画面。他通过与省城土主庙的奇树比对,觉得“十里香”很像娑罗树,花则更像娑罗花。但是,他又根据志书记载:“榆城异产有木莲花,而不注何地,然他处亦不闻”,加上“花自正月抵二月终乃谢,时已无余瓣,不能闻香见色,惟抚其本辨其叶而已”等原因,从而又得出“岂即此耶”的推断,也进而提出上关花究竟是不是木莲花的疑问。
“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
诸多典籍有关“上关花”的记载并非编撰者亲眼所见,大多依据传说、听说、大家说所著,各种说法或许也不足为据。
天启《滇志》中关于“上关花”的记载,乃刘文征亲眼所见。对于“此花即会城土主庙娑罗树也”与“游圣”判断基本一致,“奇树”盖乃“娑罗树”。而“娑罗花”(优昙娑罗花)又是传说中的仙界极品之花。《法华文句·四上》载:“优昙花者,此言灵瑞,三千年一现。”据此可推知,前人所见“上关花”为“娑罗花”也就存疑。
而有关“上关花”乃木莲花、龙女花的推测,也无据可证。因仅以《滇游日记》中所载,在一个月内,“游圣”还曾先后在大理感通寺、永平宝台山分别见过龙女花、木莲花,但对于“三种花”的树高、叶态、花形、大小、颜色、花瓣数量、花开季节等记述也不尽相同。
在大理感通寺,游记中对于龙女花的记载为:“其前有龙女树。树从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叶长二寸半,阔半之,而绿润有光,花白,小于玉兰,亦木莲之类而异其名。时花亦已谢,止存数朵在树杪,而高不可折,余仅折其空枝以行。”
在永平宝台山,游记中对于木莲花的记载为:“其上多木莲花,树极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叶生矣。”
综上,游记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过“上关花”就是龙女花或木莲花其中之一,也没有自圆其说的只言片语可查。因而,游记中所述只能佐证“上关花”的确曾经存于世上,但究竟是何种花皆已成谜。
“蛱蝶泉之异,余闻之已久。”“余在粤西三里城,陆参戎即为余言其异。”
“游圣”对于蝴蝶泉奇异之处其实早就听说过很久了,来之前就曾有人告诉过他。这里,还特别提到粤西三里城的陆万里。
彼时,“游圣”曾与老乡陆万里还同游过“韦龟岩”。期间,陆万里慷慨解囊为其捐赠“游资”,对于“游圣”更是关照备至、帮助甚多。“万里霞征”中,“游圣”许多时候其实都是靠着沿途求友以解“游资”之困,却很少与官府中人打交道,陆万里算是个例,两人之间的亲密友情甚至可用“谊逾骨肉焉”来形容。
“询土人,或言蛱蝶即其花所变,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类而来,未知孰是。”
蛱蝶虽普通,却令“游圣”很纠结。因为,就连当地人也不知道泉边合欢树上的蝴蝶究竟是从何处而来。而“游圣”询问未果之不幸,或许也正是他前往探奇的原因吧。
阳春三月间,“游圣”行走于充满诗情画意的苍洱风光中,喜悦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尤其在观上关花、赏蝶泉树后,内心也不禁油然而生“然龙首南北相距不出数里,有此二奇葩”的感慨。
“游圣”所遇“第一奇葩”有感来自“十里香”奇树,所谓“上关花”;所遇“第二奇葩”则有感来自“蝶泉树”奇景,所谓“蛱蝶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
而“二奇葩”的感慨背后,却也留有“二遗恨”。
“一恨于已落”,缘于所遇上关花“时已无余瓣”。
“一恨于未蕊”,则缘于所遇蝶泉树“时早未花”。
不幸中的有幸。相较于“皆不过一月而各不相遇”的不幸,“游圣”至少还能“折其枝、图其叶而后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探“古佛洞”之险,访“名禅寺”之圣,觅“波罗岩”之迹
游完蝴蝶泉后,“游圣”并没有乘兴而归,“乃北上蹑之”前往古佛洞。
路上虽遇樵夫,但其中一人只知道有条樵道,却不知前去古佛洞怎么走。幸运的是,另一老者却说“君既万里而来,不为险阻,余何难前导。”
从“其坡甚峻”到“悬崖绝壁”再到“危崖绝壁”,“游圣”不畏险阻跟着“导者”背负蛱蝶枝艰难前行。
其实,从“游圣”与樵夫的对话中我们便可知道,当时的古佛洞已是人迹罕至之地。而如今,知晓此处的人也是屈指可数,去过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游圣”之所以冒险前往,一方面或许受到明末“儒佛会通”思想的影响,与高僧大师或僧侣力荐有关;另一方面也或许深受“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的探险家精神影响,更与喜好探索洞穴有关。在苍洱之行中,“游圣”几乎逢洞必探。他曾先后探查过油鱼洞、古佛洞,而游记中有关考察洞穴的文字描写也颇多。
“于是缘峡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绝壁,积雪皑皑当石崖间,旭日映之,光艳夺目。下瞰南峰,与崖又骈峙成峡,其内坠壑深杳,其外东临大道,有居庐当其平豁之口,甚盛。”
“游圣”行至南峡之上时,那些远离世俗,深藏于佛系之中的山野美景、田园风光令“游圣”大开眼界、一饱眼福。近看,可见一幅光艳夺目的“苍山雪”山水画;远眺,向下看向南面的山峰,峡谷外东边靠近大道的地方,有村居在平敞开阔的峡口,十分兴盛。宛如一幅绝美的乡愁画卷。
但这些风景比起爬山之时所遇到的“崖石愈巀嶪(jié yè),对崖亦穹环骈绕”和“上崖飞骞刺空,下崖倒影无底”等险境,其实都不值一提。只是轻描淡写间,“游圣”便已将攀崖过程中的千辛万苦化解于无形之中。
古佛洞“四睇皆无路”,“游圣”只能“遂由庋石之西,攀树直坠”。以此,说“游圣”是冒险家并不过分,但非要说他是个“硬汉”,其实一点儿也不为过。
“险而为猿”!成功挑战过徒手攀岩的高手,已然由冒险家蜕变为“硬汉”。
再则,勇于铤而走险,敢于履险蹈难,以致后来“双足俱废”的行径,也足以彰显其“硬汉”形象。
“以性灵游,以躯命游”,足以让人可悲可叹、可怜可惜、可尊可敬。
洞以“古佛”为名,是因为数年前有一僧栖此崖间,多置佛而得。很是不幸,因“级废灯无”,“游圣”只能探洞的中、上两层。经过探察,发现其中别有洞天,不同寻常,甚至还有“不闭塞不奇”和“但无其层叠之异”的意外惊喜和收获。
说到“古佛洞”的奇异之处,一直鲜有人知,后人更是很少有人提及,因而“古佛洞”也得以较好保存。
但此洞已非彼洞。
过往,洞内石壁上没有题字。而现今,洞内南石壁上已有赫然醒目的楹联题字。其内容为:“何处寻仙境上前即是,此间真佛地瞻望依然”。
此洞外也非彼洞外。
过往,洞外无摹刻崖壁。而现今,有人将洞内石壁上的楹联摹刻于崖壁之上。过往,洞外并无古佛塔。现今,洞外有古佛塔(2003年重建)一座。而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原塔,已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间(据说1983年)因自然倒塌而毁。古佛洞现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便后人敬而可观,惠以珍存。
“游圣”从清碧溪下,还造访过“松桧翳依,净宇高下”的感通寺。感通寺旧称荡山寺,至今还留有“插杖成活”选寺址、立“恩彼灵株”碑等有关名人名士、名树名花、名物名迹的传说故事。
明末高僧担当大师曾题联说:“寺古松森,西南览胜无双地;马嘶花放,苍洱驰名第一山。”
“马嘶花放”故事就缘于此寺。
在感通寺,“游圣”不但发现其与三塔寺的僧庐位置大有不同,还有幸巧遇在大觉寺遍周禅师处会过面的王赓虞。晚饭后,“游圣”更是与何巢阿“复与之席地而饮”。觥筹交错、推杯换盏,“游圣”能有如此闲情雅致与友人在静室叙旧实属难得一见,只是感觉夜里的月光大不如前一天那样皎洁。
为何“夜月不如前日之皎”?或许还是因为前日“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
彼时,“游圣”与何巢阿一同夜游“三塔寺”,徘徊在塔下,踞桥而坐,看着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感慨万千……
也许,风景不同,境遇不同,心意便不同。然则夜月亦不如前日之皎也!也或许,曾因读过冯时可的《滇行纪略》,忽然想起“洱海之奇在于‘日月与星,比别处倍大而更明’”这句话。因“移步换景”使其触景生情,心情大变,有所感伤。
总之,夜游“三塔寺”,踞桥观塔,踏雪赏月……这些有关夜景的记述,在此篇游记中更是难得一见。
“已乃由寺后西向登岭,觅波罗岩……波罗岩者,昔有赵波罗栖此,朝夕礼佛,印二足迹于方石上,故后人即以‘波罗’名。”
“游圣”之所以前往波罗岩,观看赵波罗朝夕礼佛而在方石上留下的足迹,可能与“性又好奇人”和耳濡目染的禅修有关。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
远游的抱负和游学的使命,既是一种信仰,抑或是一种苦修。“游圣”此行目的极有可能是以“游学之迹”比“悟禅足迹”,以“至此足印”比“方石之痕”。以此,彰显其“万里霞征”的决心和恒心。
沧海桑田,几度春秋。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还隐藏于幽静的山寺之中,伴随着鸟语花香若隐若现于波罗岩之处,待人寻觅……
现在的波罗寺则坐落在感通寺后波罗悬崖下,在寺附近的波罗岩下还有波罗洞、波罗墓塔等古迹,而波罗洞处却还留有“波罗在此成正果,人生到内得清古”的题刻。
“游圣”到访“波罗岩”后,则重返感通寺。
“楼已非故物,今山门有一楼,差可以存迹。问升庵遗墨,尚有二匾,寺僧恐损剥,藏而不揭也。”
“游圣”有幸再观“写韵楼”,恐怕是想沿着杨慎贬谪永昌寓大理的脚印,探寻才子居此楼呕心沥血转注音韵时的孤灯清影,从中聆听杨慎、李元阳在此吟诗作对,共话友情的不羁余音。
杨慎《游点苍山记》载:暮投感通寺楼,篝灯夜坐,闻寺僧诵等字。中溪曰:“六书中转注实非‘考老’,而宋人亡拟。后世学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无述,愿公任之”。予遂操笔书转注之例千余字,汇成一编。中溪题其额曰“写韵楼”。寓此凡二旬日而去。兹寺有高皇诗十八章,镌碑山门院,凡三十六。今存在仅半耳。
遥想嘉靖年间,杨升庵与李元阳同游大理点苍山,居住感通寺斑山楼二十日,杨升庵著《转注古音略》,以补字学之缺。李元阳则题其额为“写韵楼”。
杨升庵甚至还有诗《感通寺》以记其事。“岳麓苍山半,波涛黑水分。传灯留圣制,演梵听华云。壁古仙苔见,泉香瑞草闻。花宫三十六,一一远人群。”
何其不幸,“游圣”所见皆已是人去楼空,楼已非故物。不幸中的有幸,杨升庵遗留下的墨迹,还有两块匾得以被寺僧保藏。
或许,知己所见略同。担当大师也是因为仰慕杨慎品学,才会移徙感通寺,并重修“写韵楼”而居。后来,还因此留下“名士高僧共一楼”的一段佳话。而现在,感通寺内还存有担当大师手书“一笑皆春”牌匾。
“一笑皆春”?不知又有多少有缘人曾慕名前往解读其意。
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有诗、书、画“三绝”之誉,更有“云中一鹤”“南中高士”之称。
“游圣”由黔入滇后在晋宁与唐大来有幸初次相见。游记中有载:“既见大来,各道相思甚急”和“夜宴必尽醉乃已”。
从相思相见相识,到相知相交相醉,再到“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陈继儒)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因而,两人也成为一生挚友。
唐泰更有诗《先生以诗见贻赋赠》:“朝履霜岑暮雪湖,阳春寡和影犹孤。知君足下无知己,除却青山只有吾。”诚然,两人之间可谓“人生难得一知己”。
“游圣”之所以与担当大师成为挚友,还得要感谢陈继儒的“转介之恩”。“游圣”虽与陈继儒相识恨晚,但彼此之间还是结下了“忘年之交”。甚至,还可称之为“君子之交”或“莫逆之交”。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有载:“先生名弘祖,字振之,霞客其别号也。石斋师为更号霞逸,而薄海内外,以眉公所号之霞客行。”
“霞客”别号就是陈继儒所送,而“霞逸”更号则是好友黄道周所送。
在感通寺正殿前面,“游圣”之所以徘徊不前,怅然若失,皆因“宸翰已不存”,而令其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不幸中的有幸,“诗碑犹当时所镌者”。进而,“游圣”还对李中谿(李元阳)《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与文献同辑,竟不之录”提出些许质疑。
现在,在感通寺内大殿前还有一副对联:“古刹何奇,状元写韵,才子参禅,总督题壁,霞客记游,名士名僧名官名流登临览胜;班山独秀,龙女献花,无极观帝,波罗正果,悲鸿好马,有文有赋有诗有画荟萃云堂。”
从对联中也可见,历代名士名僧名官名流的造访,使得感通寺声名显赫、名扬天下。
说感通寺就不得不提及崇圣寺。崇圣寺,在苍山第十峰之下。“游圣”与何巢阿遍游崇圣寺,先往三塔,后“由山门而入”,见有钟楼与三塔对,还见到“中溪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和“雨珠观音殿”等物。
“游圣”有幸见到当时“镇寺之宝”有三。一曰三塔,二曰鸿钟,三曰雨铜观音。不幸的是没有见到“四曰证道歌,佛都匾”和“五曰三圣金像”两样重器。
明代督学副使吴鹏在《重修崇圣寺记》中说:“南中梵刹之胜在苍山洱水,苍洱之胜在崇圣一寺。”而“游圣”当时所见到的崇圣寺却是“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和“廊倾不能蔽焉”的景象。
不幸中的有幸。崇圣寺虽已没有了往日的恢弘气势,但“游圣”却在李元阳墓处(崇圣寺后)找到了“颓败不堪”的原因,那就是“而熟知佛宇之亦为沧桑耶!”
明代督学副使吴鹏在《重修崇圣寺记》有载:“郡人李内翰中溪氏,率子弟罄货财,竭力兴复。盖自嘉靖壬寅经始,至今癸亥乃得讫工。凡三阁七楼百厦,其位置之向背,基础之崇卑,片瓦寸木皆出自李公之擘画。”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毕竟,上一次重修崇圣寺还是在李元阳动员号召下“售罄货财”捐建,加上亲力亲为“竭力兴复”才得以完成。而八十多年后,“游圣”所见已是“人逝寺衰”。
望“洱海滨”之形,瞻“苍山麓”之势,视“龙首关”之貌
“高眺西峰,多坠坑而下,盖后如列屏,前如连袂,所谓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坠为坑者也。”
这是“游圣”在赏完“上关花”的第二天,也就是从沙坪往南行一里到达“龙首关”时,第一次见到苍山时的惊叹之记。
而“游圣”从“古佛洞”下山后,步入通向龙首关方向的大道后,其笔下对于苍山的描述要比第一次更为详细。
“十九峰虽比肩连袂,而大势又中分两重。”北重自龙首关往南至洪圭山(今弘圭山),“其支东拖而出,又从洪圭后再起为南重”,自无为山往南至龙尾关,“其支乃尽”。
由上可见,“游圣”在遥望洱海东湾时,对苍山进行过系统的观察,甚至对于山脉走势都能做到“察其四隅”。
“洪圭之后,即有峡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东出者为某村,又东错而直瞰洱海中,为鹅鼻嘴即罗刹石也。不特山从此叠两重,而海亦界为两重焉。”
作为地理学家,“游圣”其实已经发现苍山特有的沟壑纵横,褶皱起伏的地貌特点。不幸的是“游圣”那时还不知道,属于横断山脉的苍山,与其他地方的山形地貌的确大有不同。
“十三里,过某村之西,西瞻有路登山,为花甸道;东瞻某村,居庐甚富。”
也许,“游圣”并没有想起李元阳的《游花甸记》。否则,花甸怎会不去?
甚是可惜!不知“惜未至”,是不是“未了之兴”中的又一殇。
作为曾在“游圣”家乡为官的知县,李元阳当时声望极高,对于“游圣”的影响可谓深远。从“游圣”路过崇圣寺时,顺道拜谒其墓就可看出原委。游记有载:“至寺后,转而南过李中谿墓,乃下马拜之。”
而对于苍山脚下,喜洲附近见到的“某村居庐”和从攀爬“古佛洞”时所看到的“居庐”,“游圣”则分别用“甚富”“甚盛”来形容。从中,也可窥见当时两地的百姓生活就已经很是富足,这也诠释了王士性所说的“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唯大理得之”这一深意。
作为“游圣”推崇的榜样,“王十岳”的名号也是出自“游圣”之口。但是,“号取有因”。
“游圣”髫年蓄五岳志。而以游记所载考镜,“五岳”之中他只去过“其四”——《游嵩山日记》(嵩山),《游太华山日记》(华山),《游恒山日记》(恒山),《楚游日记》(衡山)。
但对于王士性而言,则全部都去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两次即“十岳”),“十岳”名号也因此而得。
即便这样,也不能将两人相提并论,分出高下。“游圣”与“王十岳”,在地理学方面的建树可以说是不分伯仲。前者因为是“穷游”,足迹遍布“两京十二布政司”,仅四川未到。“游圣”在自然地理方面更有所成就。后者因为是“宦游”,也游遍“两京十二省”,而独缺福建。“王十岳”则在人文地理方面更有所成就。
“西山之支,又横突而东,是为龙首关,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
根据《一统志》里面的记载,点苍十九峰的次序,由南向北排列,反而是以龙尾关所处的山峰为首。
“而东垂北顾,实始于此,所以谓之‘龙首’。”“当山垂海错之外,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锁钥,俗谓之上关,以据洱海上流也。”
作为大理的“北大门”,“龙首关”自古就是兵家重地,其锁山控海、易守难攻的屏障作用,可用“北门锁钥”来形容其重要性。而与之齐名的南天屏障“龙尾关”,更有“龙关锁匙”与之隔空相望,遥相呼应。
“又南,则西巍峨之势少降,东海弯环之开渐合。”
“游圣”离开“榆城”去往“龙尾关”,再过五里桥、七里桥和上睦(今上末)后,见到的苍山、洱海则又是另一番景象。
“又十里,则南山自东横亘而西,海南尽于其麓,穿西峡而去。西峡者,南即横亘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苍山,至此南尽,中穿一峡,西去甚逼。而峡口稍旷,乃就所穿之溪,城其两崖,而跨石梁于中。以通往来。所谓下关也,又名龙尾关。关之南则大道,东自赵州,西向漾濞焉。”
过阳和铺后,苍山山形地势则又变。而就在这悄然变化之中,“游圣”便已见到“龙尾关”。作为“以通往来”的险要之地,其与上关“龙首关”相得益彰,共同诉说着世事苍茫、风云变幻的烟云往事。“龙尾关”曾聆听过天宝之战的惨烈战事,而“龙首关”也曾目睹过元世祖忽必烈的蒙古铁骑,见证过金戈铁马的厮杀战场。
赏“清碧溪”之韵,览“大峡谷”之幽,赞“感通茶”之雅
“十二日觉宗具骑挈餐,候何君同为清碧溪游……泉一方在坡坳间,水从此溢出,冯元成谓其清冽不减慧山。甃为方池,其上有废址,皆其遗也。”
“游圣”在游玩清碧溪之前,路过石马泉,转借“冯元成谓其清冽不减慧山”这句话来赞叹其水质之佳。
冯时可,字元成,曾任云南布政司参议,著有《滇行纪略》。其中有载“城外石马井水,无异惠泉。”
这里说到石马泉,还转借冯元成的话,可能是因“游圣”在此睹物思人,不自觉地再次想起家乡旁边著名的惠山泉。
无锡惠山泉号称天下“第二泉”。“游圣”早年曾与江阴诗人许学夷同游过惠山。许学夷还写下《同徐振之登惠山》这首诗,以纪念他们寻泉时的过往。
其诗曰:“宿雨溪流急,扁舟向晚移。山因泉得胜,松以石为奇。楼阁高卑称,园林映带宜。幽探殊不尽,策杖自忘疲。”
“游圣”在游记中曾先后四次提到过惠山泉。譬如,崇祯十年在湖南祁阳,在甘泉寺品尝甘泉后说:“极似惠山泉。”崇祯十一年三月,在柳州宜山雪花洞,品尝洞中的滴水时称:“甘洌不减惠泉也。”同年四月在贵州关索岭跑马泉,他饮后称:“甘洌次于惠泉。”崇祯十二年则在云南大理,转借冯元成的话:“其清冽不减惠山。”
说其中之事,看其中之人。“游圣”所到石马泉,其实并非惠山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游圣”虽在外远游,但心里总是难免会有思乡之痛。尤其,情景交融之际,便会不由自主地在游记中对惠山泉有所记、有所忆、有所思。
无独有偶,同样杨慎的《石马泉亭诗页》(九月廿六日始会于石马泉亭二首)也有此番意境。
“胜地荒芜久,华亭结构新。清泉分马颊,白石动鱼鱗。玉泻琴中韵,花摇镜里春。还将濯缨意,拟问钓璜人。”“苍霭环城下,红云指海东。登薠临远水,摇蕙感回风。归望微茫外,生涯烂醉中。故园千万里,秋色可能同。”
诗中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则借景抒情。杨慎(明代三才子之首)也是想借此形容升沉荣辱、芝残蕙焚的境遇,用以表达孤苦伶仃、孑然一身在滇漂泊时的思乡之情,思乡之痛。
“又南半里,为一塔寺,前有诸葛祠并书院。又南过中和、玉局二峰。六里,渡一溪,颇大。又南,有峰东环而下。又二里,盘峰冈之南,乃西向觅小径入峡。峡中西望,重峰罨映,最高一峰当其后,有雪痕一派,独高垂如匹练界青山,有溪从峡中东注,即清碧之下流也。从溪北蹑冈西上,二里,有马鬣在左冈之上,为阮尚宾之墓。”
“游圣”路过“一塔寺”(弘圣寺)的诸葛祠和书院,往南过中和、玉局二峰,渡溪、盘峰后来到清碧溪北,蹑冈西上,来到阮尚宾之墓。
阮尚宾,太和人,明隆庆五年辛未科进士,历官运长(四川龙安府知府、长芦盐运使),其守不淄。
“游圣”蹑峻凌崖,由于“溪嵌于下,崖夹于上,俱逼仄深窅”,加之“路缘崖端,马不可行”,便与何巢阿父子和两僧溯溪入。
“西眺内门,双耸中劈,仅如一线,后峰垂雪正当其中,掩映层叠,如挂幅中垂,幽异殊甚。觉宗辄解筐酌酒,凡三劝酬。复西半里,其水捣峡泻石间,石色光腻,文理灿然,颇饶烟云之致。于是盘崖而上,一里余,北峰稍开,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复与涧遇。”
游记所载,诚不欺我。苍山大峡谷,果真是山高谷深,险峰峻岭,峭崖绝壁,清幽旷远。“游圣”有幸与友人结伴而行,深入其中,一探究竟,不枉此行。
一行几人在西眺“一线天”时,感觉山中幽暗,加上还有积雪互相掩映,层层叠叠,特别幽雅奇异,顿感寒气逼人。而觉宗不耐严寒,只能解下竹筐斟酒用以抵挡严寒,还曾三次劝说“游圣”与其共饮。
“游圣”再向西走半里,看到溪水捣入峡中奔泻在岩石间,石头的颜色光洁细腻,花纹灿烂,颇富于烟云的意态。从这里绕着山崖上走,一里多,北面的山峰略微敞开,找到一块高高隆起的平地。又向西半里,从平地向西下走,再次与山涧相遇。
“时余狎之不觉,见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从涧北上,余独在潭上觅路不得。遂蹑峰槽,与水争道,为石滑足,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水及其项。”
在清碧溪,“游圣”玩性大发,但为追赶两僧和何巢阿父子,不幸“为石滑足”,导致“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潭中“水及其项”,“游圣”赶快“亟跃而出,踞石绞衣”。
“游圣”之所以会滑入潭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腻滑尤甚;即上有初层,其中升降,更无可阶也。”
再逾西崖,下觑其内有潭,方广各二丈余,其色纯绿,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十分美丽。尤其是中午时分,才是最美的。
“游圣”有幸见到此景,更是将其称赞为“金碧交荡,光怪得未曾有。”对于美景,“游圣”还从崖端俯而见之,感觉好像踞石坐潭上,令人“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
沉醉于山水画卷般的景致之中,“游圣”感觉不仅山影可使人心荡去一切杂念,甚至觉得每一根汗毛每一个毛孔,无不晶莹透彻。
“亟解湿衣曝石上……可下瞰澄潭,而险逼不能全见。”
“游圣”借着晒衣之际“就流濯足,就日曝背”,感觉冷暖之间便将烦恼洗去,心情大变,好似拥抱过太阳。而何巢阿父子涉险而至,对于美景也是啧啧称奇。
值得庆幸的是,“崖日西映”时,矢志不移的“游圣”,终于披上衣服成功登上山崖顶端,居高临下观察清碧溪。
“游圣”还想游石门内的水潭,并想去往积雪高悬的山峰。面对不情之请,何君这些人并不想去,也不好阻止,便说:“我们出去在马匹休息的地方等候。”很不幸,“游圣”只能只身前往。
渡栈道,过阳桥;渡桥北,历涧石而上,“小者践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则转夹而梯之。”
“游圣”而后有幸遇见一樵者。而樵者立即告诉“游圣”前行方向已是无路可走。“游圣”不相信,为最终到达目的地更是“去巾解服,攀竹为 。”直到亲眼看到“与垂雪后峰,又界为两重,无从竟升”,还在疑惑地自问:“闻清碧涧有路,可逾后岭通漾濞,岂尚当从涧中历块耶?”
若不是因为找不到涧中通往漾濞的路,加上“时已下午,腹馁甚”,“游圣”恐怕真的会徒步从苍山东坡翻越至漾濞。
于是,“游圣”索性折返。
不幸中的有幸。“游圣”在下山返途中还可以“随水而前,观第二潭”,以弥补前行中“时第二潭已过而不知”的遗憾。
清碧溪可谓苍山十八溪当中风光最美之一,下潭深青色,中潭鸦碧色,上潭鹦绿色。今朝如若前往,定要步行,做一个还淳返朴的“负刍之游者”。而且,一定要在“游记”的导引下循涧而上,亲身感受“重峰罨映”和“水声潺潺不绝”的自然美景。或许,也可乘感通索道,居高临下领略苍山大峡谷的绝美自然风光。
除了此中美景,引人之处还有许多儒官雅士留下的摩崖石刻,而且大多数为明代、清代及民国三个时期的祈雨求福类的题刻。其中,最出名的则莫过于明太守杨仲琼(四川邛崃人)所书的“禹穴”二字题刻。
如有喜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观字篆刻的文人雅士,定要前往一探缘由。但不知何故,“游圣”反而没有前往参摩。
因清碧溪四时不竭,灌溉千亩良田,明嘉靖年间人们又将其称之为“德溪”。而“游圣”有幸亲临清碧溪,可谓不虚此行。
再回首之间,清碧溪已成为连接苍山与洱海的情感纽带。一端,承接苍山生态天堂的静谧与柔情;另一端,则接纳洱海历代文明的喧嚣与壮丽。时今,清碧溪与十七条溪流一同注入洱海,汇聚的润泽之力,滋养着苍洱大地这片沃土,哺育着苍洱儿女,给这里带来了文明与繁荣。
“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
感通茶的历史悠久,记述也比较多。比如,冯时可《滇行纪略》有载“感通寺茶,不下天池伏龙。”明代谢肇淛撰《滇略》:“云南名茶有三种,即太华茶、感通茶、普茶。”李元阳《感通寺寒泉亭记》:“寺旁有泉,清冽可饮。泉之旁树茶一株,计其初植时不下百年物也。自有此山即有此泉,有此寺即有此茶。采茶汲泉烹啜之几数百年矣,而茶法卒未谙焉。”
茶因寺而得名,寺因茶而闻名,可谓自古名寺出名茶。从古至今,其实有很多的名茶,最开始都是由寺院种植、炒制。而寺院中的僧侣除了栽培、焙制茶叶外,对饮茶之道也精于研究,勤于写实,以致世上留有很多有关品茶的诗作。
“寺院茶”一般都有供佛、待客和自奉的用途。因而,感通茶抑或是因香客的口碑传播与扩散,才得以声名远扬。
感通茶作为“寺院茶”,也理所当然成为“三道茶”的首选茶之一。尤其品茗论道之时,通过一苦二甜三回味,便能感悟“茶禅一味”中的禅意雅致。这里说到茶与禅,不禁让人想起唐代高僧从谂禅师那句“吃茶去”的历史典故。
或许,“游圣”在感通寺也有幸闻茗过其香,品茗过其味。因为,十三日的游记中有载“殿东向,大云堂在其北。僧为瀹茗设斋。”甚而,“游圣”还曾在游记中给出“茶味颇佳”的赞茶好评。
赶“观音街”之趣,享“叶榆城”之逸,结“点苍石”之缘
“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减大半矣。”
那时的三月街就已十分热闹。“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的独特魅力,也吸引着“游圣”反复两次欣然前往。
第一次赶三月街,“游圣”很是不幸,可谓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皆因“中途雨霰大作”,与“街子人俱奔还”一样,不得已“余辈亦随之还寺”。
第二次赶三月街,“游圣”有幸看到赛马大会上“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的火爆场面。
“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而已,无足观者。”
三月街上人声鼎沸好不热闹,琳琅满目的“十三省物”很多,令人“乱花渐欲迷人眼”。然而,“游圣”却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的眼睛里面,能够“吸睛”的东西或许只有“奇书”。但是,“观音街”上只有类似“吾乡所刻村塾中物及时文数种”,更不幸的是“无旧书也”。
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中有载:“仲昭又言其游有二奇。性酷好奇书,客中见未见书,即囊无遗钱,亦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半得之游地者。”
从“游圣”族兄仲昭口中我们可以得知,“游圣”非常爱书,而且特别喜好“奇书”。因而,他在所游之地购买了大量不曾见过的书籍。
“游圣”除了在集市上体验“赶街”的乐趣,还在大理府闲逛游玩、叩访友人。而且,曾“六进六出”大理郡城,好不快哉。
一进,从感通寺游玩后沿“龙尾关达郡城大道”由南门入。一出,是日“乃出北门,过吊桥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二进,“余由西门入叩吕梦熊乃郞。”二出,是日“既暮,返寺中。”
三进,送别何巢阿,“送至寺前,余即南入城。”三出,是日“知吕郎已先往马场,遂与同出。”
四进,“由东门入城,定巾,买竹箱,修旧箧。”四出,是日“吕命其仆为觅担夫,余乃返。”
五进,“同刘君往叩王赓虞父子,盖王亦刘戚也,家西南城隅内。”五出,是日从清真寺出而“还寺”。
六进,“余乃入西门,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六出,是日“出南门,遂与僧仆同行。”
“游圣”在大理郡城虽与当地清雅文士往来甚多,相交甚笃,但闲暇之余也会穿行于闹市,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商贾市肆和阜通货贿情况。期间,“游圣”就曾有幸“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可是,得到的却是“亦无佳者”之憾,只因没有相中、看中的物件。
“观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与余各以百钱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峦点缀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
观赏大理石不如购买一小方“把玩”,这是“游圣”对于当时商业活动的又一具体记述。虽是偶有所得,但也是游玩苍洱胜景后,留给自己最好的纪念品之一。
说到苍石,在崇圣寺前殿佛座后方,“游圣”还见过“巨石二方”,认为“二石”与清真寺碑趺“为苍石之最古者”,并通过与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比较,发出“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的赞叹。
同时,“游圣”还发现,苍石除具有观赏性,还有很多实用性,主要体现在建筑中的应用。譬如:“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以为栏壁之用焉。”
对于清真寺二门内屏风样的大理石碑,“游圣”则认为奇异之处是“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黯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为一探真伪,“游圣”还曾两次前往清真寺。
第一次,借叩拜王赓虞父子之时入寺,不幸的是“不得所谓古梅之石”。
第二次,借找吕梦熊的儿子帮助挑夫向其索要定金之机,再次入寺。幸运的是终于得以“观石碑梅痕”,却发现“乃枯槎而无花”,并没有“张顺宁所寄者之奇也”。
因为,“张石大径二尺,约五十块,块块皆奇,俱绝妙著色山水,危峰断壑,飞瀑随云,雪崖映水,层叠远近,笔笔灵异,云皆能活,水如有声,不特五色灿然而已。”
“过寺东石户村,止余环堵数十围,而人户俱流徙已尽,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数十家,今惟南户尚存。取石之处,由无为寺而上,乃点苍之第八峰也,凿去上层,乃得佳者。”
“游圣”在“榆城”可随时一睹“苍石”之容,并且知道最好的“苍石”其实是取自点苍山的第八峰。在石户村,他还亲眼目睹了“止余环堵数十围,而人户俱流徙已尽”的荒芜与落魄。并且,对于石工“不堪其累也”的无奈与无助深表同情。
因而,他在游记中,也从人文地理方面如实地反映了明末百姓生活的惨痛现状。这些,也是“游圣”在大理期间少有的关注政治和人民生活疾苦的记述,从侧面也深刻地揭露了明朝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情况。
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中有载:“山腰多白石,穴之腻如切脂,白质墨章,片琢为屏,有山川云物之状,世传点苍山石,好事者并争致之。唐李德裕平泉庄醒酒石即此产也。”
其实,从唐朝开始,大理“苍石”便已名震朝野。
明万历年间,云南提学佥事邓元岳曾在《点苍山石歌》中写道:“朝凿暮解苦不休,诏书昨下仍苛求。前运后运相结束,道旁叹息声啾啾,耳目之玩岂少此,十夫供役九夫死。”
作为贡石之一,官吏们则为了完成进贡任务,实行“取石之役”。进而,也引发“人户俱流徙已尽”等诸多社会问题。
如今,天坛公园祈年殿地面中间还存有进贡给明朝朱棣皇帝的“龙凤呈祥石”。从古至今,穿越时空,但它依然记得那段不为人知的“苍石”采运血泪史。
大理郡城的一街一巷、一墙一瓦、一树一草都承载着光阴的故事,见证过历史的足迹。
“蝶翩翩兮山水秀,云朵朵兮万里晴,榆郡之繁华比及京都。”这里甚至还留有“榆华近京师”的传说故事。
“游圣”有幸邂逅充满人文风情的郡城,也并没有走马观花,匆匆而行,而是停留七日慢慢游玩,品评人城往事……
三月二十,游圣“既度桥出关南,遂从溪南西向行”。行至天生桥前,但见“崇峰北绕苍山之背”,心中难免想起在大理郡城与好友何巢阿分别时曾定下的“东返之约”。
“巢阿别而归,约余自金腾东返,仍同尽点苍之胜,目下恐渐热,先为西行可也。”
何其哀哉!令“游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尽点苍之胜”的美好约定,竟最终也与“未了之兴”一同成憾又成殇。
“游圣”过天生桥、潭子铺、核桃箐,便来到茅草房,不幸遇到“榆道自漾濞下省”,因为“恐桥边旅肆为诸迎者所据”,所以“遂问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第二天,“天明乃行,云气犹勃勃也。”
“游圣”向北仍然行走在溪流西岸,经过四十里桥这个治所和辖境犬牙交错之地,出大理向漾濞,朝着金腾[金腾兵备道,设于明成化十二年,道署永昌府城(今保山城)]方向,一路西行……
诗与远方,还看大理。挥手道别间,还恍如昨日。三月苍洱好风光之行,于“游圣”而言,是幸欤抑或不幸欤?
唯有劝君,开卷再读“千古奇书”游之山水,阖书再思“千古奇人”旅之悲喜,方能答疑解惑以辨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