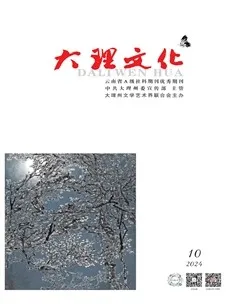乡下的奶奶们
一
我生于乡村,从小喝着山野的泉水长大。住城里这么多年来,泡茶、做饭仍然喜欢用山泉水。对于山泉水有深入骨髓的执念。见家里的山泉水快用完,便和妻子去城郊的山上打山泉水,沿途时常与一些健身的城市老奶奶擦身而过,瞬间勾起我对乡下奶奶们的回忆。
大奶奶姓邬,从小在县城里长大。大爷爷早年在夔州府(奉节县)一店帮忙做账房先生。自从和大爷爷结婚后便一直住在祖屋旁边,很少走出村庄。大门前有两棵高大的香椿树、三两棵桃树、柑橘和两大丛竹子,一条小河沟从屋旁缓缓流过。
大奶奶家旁边有一座高高的山梁,夏天可以挡住西坠时依然撒泼的骄阳。夜晚阵阵蛙鸣,门前一坵一弯的稻谷缕缕清香,自然会扒开竹叶飞过来。呈阶梯状的水田,最底层的长田一年四季都蓄着水,水稻收割之后,空闲的水田里就是鸭子、鹅、黄鳝之类的天下了。早春吆喝着大黄牛犁田的刘家伯伯,有时会把被犁铧翻耕出来的黄鳝、泥鳅丢到田坎上。那个贫瘠的年代,村民们不喜欢吃黄鳝、泥鳅,费油,腥味重。于是,这些被村民丢弃的黄鳝、泥鳅便成了猫和狗的美食,它们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一时间,寂静的村野多了一份闹热。
知道大奶奶名字的人不多,不知道大奶奶名声的人很少。一个早年的农村女性,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都被一层层地摊薄,名字是属于个人的秘密,称呼才是社会角色的反映。她的真名也只有后来在选举的时候,才会有人茫然失措地提及,余下的日子就悄无声息地湮没在从邬大大(大大,当地方言,称呼辈分高年长的女性)、大嫂、大婶子到大奶奶的称谓中。
大奶奶的脚很小,称得上是“三寸金莲”,齐肩短发,用黑色的韭菜叶夹子别得齐齐整整、爽爽朗朗,不像和她差不多大小的老太婆,脑后梳着髻(我们称为“挽簪”,天然带着一股子行将就木的腐朽味道)。在我们家族奶奶辈中年龄是最大的,穿一身洗得泛白的带点花色的大衣襟,蝴蝶一样的布纽扣,沿着小立领从右肩一直到左下摆,热天腰身略略宽大些,衣袖齐肘而已;60来岁就掉了好几颗牙齿,由于几乎没出过村庄,也舍不得花几个钱去街上的诊所把牙齿补上。平时有意无意地紧抿着嘴;勤快得像一面干净的镜子,打碎了都能把村里的那些妇女们都比下去。一个老婆婆,年龄大,辈分高,又从不多言多语,不倚老卖老。她和母亲相处很愉快,喜欢到我们家来小住三两天,帮着做些针线活儿。村里的人对她的尊敬,就藏在一声声烫人的呼喊中。这是一直储存在记忆里的模样。
身材娇小的大奶奶,身体里像藏了一个停不下来的精灵,你都不知道她究竟合上眼睡过觉没有。村里的人一睁眼,大奶奶迈着“三寸金莲”已经到河沟边把衣服洗完回来了,也可能打回了一大背篼的猪草;一闭眼,还能听到她在灶屋里忙前忙后的声音。那些零零碎碎的小活儿,偏偏她能够找出来,偏偏她几百次几千次地重复,都不露出一丁点儿厌烦。一窝小鸡仔会准时吵醒刚刚绽放的桃花,大奶奶的脸庞已是绯红,她用一把碎米安抚了叽叽喳喳的鸡,双手一张低低几声吆喝,把鸭子轰进了门前水田,圈里的猪,早已埋头在热气腾腾的石槽里,两只耳朵扇出来的声音,成为清早大奶奶最爱听的音乐。等她扛着锄头,把菜园子里挖出即将开花的莲白菜,准备雨后栽种红苕的时候,太阳都还没来得及把脑壳从屋后的山梁处冒出来。
大奶奶特别喜欢在厨房做事,做的一手茶饭在村里也是赫赫有名。生长在灶屋里,成熟在灶屋里,又守护着灶屋。为她博得名声的,是她非常爱整洁,要搁到今天,绝对应该划入有洁癖的这一类。谁也说不出大奶奶是哪个时候把房屋里里外外收捡得那个干净的,反正每次去大奶奶家,都能看到大奶奶勤快的身影在屋里忙个不停,屋里的旮旮角角,收拾得整齐清爽,这在乡下人的家里是很少见的。大奶奶说,自己的虱子自己捉,难不成还有哪个来帮你呀。
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看到已经非常干净了,找不到一点儿渣渣糊糊的影子。大奶奶依然如故,用薄得像云彩的抹布擦擦桌子,拿高粱秆儿的扫帚扫扫地,就没见停止过。他们家的地面是用三合土夯的,看上去平展展的,经过几十年不轻不缓地摩挲,已经有了一层半透明的包浆。嗑瓜子的时候,要是有瓜仁儿掉到了地上,我们会毫不犹疑地用右手的食指在舌头上舔一舔,然后轻轻地将瓜仁儿粘起来,不用担心有灰,直接妥妥地送进嘴巴。
二
自记事起,二奶奶一家就住在我们房子坎下。
二奶奶姓何,出生在海拔1300米以上的红椿淌,是个裹小脚的中国女人。她时常面带笑容,有中国女人的传统思想,心地善良。每次看到她,总是满脸笑容。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要从小裹脚,她说家里人是希望这一双“三寸金莲”会为她带来幸福,带来好运,带来圆满。但是,命运却给了她难以忘怀的伤痛。她说那裹脚的滋味可比死了还难受,3寸宽的布条缠3米长,让她整整哭了3个月,声音没了,魂也没了。那可真是活受罪呢。到现在我都还能清晰记得小时候二奶奶指着她那双状如鸡爪一般的“三寸金莲”对我的诉说。
对于二奶奶和四爷爷是否是一家人这个问题,小时候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后来,等到年龄大些了,才从父亲口里得知,二奶奶和二爷爷结婚后,二爷爷年轻时因为一场病早逝时已育有一女,我们喊大孃孃。那时候,在农村,兄长去世了,后面有合适的兄弟可以和嫂嫂成家生活。当地称为“圆房”。
二奶奶和四爷爷成家后,分家单过。修建了3间土墙屋。房子开间很小,进深又深,土墙房子的窗户小,即使外面太阳再大,中间的房屋也几乎没有光亮透过来。有时候在他们家玩,进门的时候经常因视线不好发生迎面相撞的情形。在几十年之后,我才找到贴切的比方,这有点像很早以前的闷罐火车。
后来,二奶奶和四爷爷又生育了一儿一女。
二奶奶整天乐乐呵呵的,待人真诚和蔼。有一次,跟着父亲去二奶奶家。二奶奶看到我和父亲,让我们先坐,她去给我们煮点吃的。那年代,对于家里来了客人,一碗臊子面或煮两个荷包蛋加点白糖,就是待客的上品食物了。想着可以吃二奶奶弄的臊子面了,心中就异常兴奋。
在那昏暗的灶屋里,二奶奶取下一刀挂在房梁上的腊肉,洗净后一刀一刀地切成大小匀称、红白相间的肉丁,再将豆腐和胡萝卜切成小丁,加上切成小段的小葱一起炒,这样炒出来的臊子就有绿的、红的、白的,煞是好看。
待面煮熟后,挑在碗里,舀上几勺臊子,还有绿色的时令菜蔬,挑一筷,吸一口,香得不得了;入了口,暖了胃,润了心。那味道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美味。
除了厨艺,针线活儿也是二奶奶拿得出手的手艺,特别是修鞋样。别看脚的大概样子差不多,一副脚板5个趾头,实际千差万别。人的高矮胖瘦不同,走路轻重缓急不同,各年龄阶段的心思不同,职业习惯不同,角色地位不同,都从一双脚上反映出来。男人的田边,女人的鞋边。男人勤劳不勤劳,种田技术怎么样,看他打整田边地角的功夫就知道。女人是否心灵手巧,看她做的鞋。一双鞋是否好看、耐穿、合脚,反映了女人的心性智慧,鞋样就是最早的设计蓝图。鞋的胖瘦、长短、高低、宽窄、厚薄,既能照见人心和人性,也能照见能力和手段。巴心巴肝、费心尽力、熬更守夜做出来一双鞋,如果穿起来不舒服甚至不能穿,不光浪费灯油、布料和时光,更会浪费随着千针万线缝进去的那份情感。
时常看到二奶奶坐在地坝里,眯着眼纫好线,飞针走线,纳鞋底、缝鞋帮、缝衣服……纳的鞋底光洁、板正、结实,缝上带有松紧口的鞋帮,穿上去漂亮、合脚,走起来跟脚、踏实。
有一年,大奶奶到我家小住的时候给母亲讲,说她的男人我们的大爷爷托梦,下雪天冷得遭不住了。因二奶奶的针线活儿好,决定请二奶奶为大爷爷缝制几套老衣。整整3天,二奶奶用几十张白纸做了3套棉衣、3套单衣,哪个地方用浆糊粘接,哪个地方用针线缝合,哪些地方该铺上一层薄棉花,做得一丝不苟。然后,大奶奶让其儿子华大伯把这几套衣裳连同纸钱,焚烧在大爷爷的坟前。后来再也没听大奶奶抱怨她男人托梦喊冷,估计是大爷爷穿上了新衣不再喊冷的缘故。
有一天,二奶奶感觉有些撑不住,手里的针线不听使唤,一道闪电划过眼前的黑暗,身体彻底轻松下来,滚倒在地。无论谁喊都不答应。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走过了兵荒马乱的年月,二奶奶像一株顽强的植物,栉风沐雨,生机勃勃。78岁,无疾而终。临走的时候我已在部队。
这些都是后来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中得知的。
三
年少时的早上,父母亲都去地里给庄稼薅草、施肥去了。生火,刨洋芋皮,挑水把缸装满,这些活儿由哥哥、妹妹和我来完成。俗话说,龙多四靠,分工下来,一般是我挑水、妹妹刨洋芋、哥哥去对面半坡上的三奶奶家引火回来。
那年头除了不缺吃饭的人,啥都缺,为省柴火,头天晚上就得把火熄了,第二天一早重新生火。生火是个技术活儿,得有火种,有引火柴,还要有持久燃烧能点燃煤炭的硬柴。煤炭这黑不溜秋的玩意儿,要是伺候不到位,一点儿人情都不讲。篾黄、包谷秆、茅草、笋壳、稻谷草、棉花秆,都是很好的引火柴。如果头天晚上做了功课,将几块硬柴在火炉旁烘干了,第二天生火就轻松,一袋叶子烟,一根火柴就可能点燃这个生机盎然的事业。假如半夜下雨把堆在屋外的柴淋湿了,那就惨了。引火柴少了,根本就点不燃那些硬柴的激情;引火柴多了,要起灰,糊了灶王爷的鼻子眼睛,气息就很不匀称。家里还经常没火柴,或者火柴潮湿了划不燃。于是,仅有几百米远的三奶奶家就是借火种的好地方。
在对面坡上住的三奶奶,姓胡。娘家在高高的九台山上,其身材矮小,脸上有一些麻子窝窝。说是生过一场病留下的。对人和气,从不发脾气。当年从高山上出嫁和三爷爷成家后,她的脚步就在土地和家之间奔走,几乎没走出过村庄。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经常在三奶奶家里,到饭点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弄点吃的。母亲一直很感激三奶奶,说三奶奶小时候让我们三姊妹没饿过肚子。三奶奶有时会坐在屋门口,看着喂养的10多只鸡和鹅到地坝里抢食晾晒的谷物时,便拿起一根长竹竿去“撵鸡”,嘴里总是那一句“呿……哦……呿”每次听到那拐着弯儿拉着长然后又戛然而止的轰鸡声,我们都会忍俊不禁,其实这一声声轰鸡声,给这个寂寥的村野平添了一丝音乐的味道,也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引火柴一般是用葵花籽秆在水里浸泡后,将秆芯去掉,再将秆子晾晒干,就是最佳的引火材料。哥哥说,他每次去三奶奶家借火,总是看见她们家灶膛里的火苗愉快呼呼作响着。本来点得旺旺的,可是稍稍走得快一点儿,火种就可能熄灭,只好再跑一趟。有一次,我们家灶膛里的柴好像是铁了心要和哥哥作对,一时间灶屋里黑烟四起,我甚至还冒着危险,奢侈地败家子一样把煤油灯里的煤油倒了一丁点儿在柴上,居然还是不给面子。太阳已经快到三奶奶家的竹林上头了,我们家灶里还是冷冷清清,哥哥垂头丧气地坐在大门上,昂着一张花猫脸,喘着粗气,准备等到母亲回来后给一顿臭骂。
这时,三奶奶来了,她说看着哥哥手拿着燃着的葵花秆有点不放心,担心回来火引不燃。一瞧哥哥的大花脸儿,抿嘴笑了笑,走进灶屋,坐在灶门前,撅了两根芝麻秆,把灶炉子捅了捅,一把柴火放进去,奇怪,火苗子就乖乖地蹿出来,烧得轰轰烈烈,那一团红红火火的火苗,至今还温暖着我。
三奶奶会做豆瓣酱、晒面酱、做豆豉、做红烧肉、炸扣肉、蒸四喜丸子、熬苞谷糖等等,都是一把好手,母亲还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做菜的手法。三奶奶和别人一起捉回来大小差不多的小猪儿,到年底,她喂的总是要多出几十斤肉。
四
我爷爷排行老幺,有幺房出老辈的说法。
奶奶生于贫农家庭。佃地主土地,以农耕为营生。因从小就没了爹娘,由哥哥抚养。
很早以前,家家穷得吃不上饭,多一个人,多一张嘴,早嫁出去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当时,爷爷这边家境稍微好一点,那时兴童养媳。于是,奶奶便来到了周家生活,为爷爷生育下8个子女。
过去的女人是从小就要缠脚的。奶奶说她们那个年代,女孩子要是不裹脚,长大了就找不到好婆家。新娘一下轿,如果露出的是一双大脚,就会被婆家人瞧不起,甚至嘲笑。我一直很好奇,奶奶的脚是正常的。她说裹脚一般是从四五岁开始,越早越好。裹脚是一段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裹脚前先用热水泡脚,然后在每个脚趾的根部涂抹明矾,趁热把四个脚趾弯曲后紧贴在脚掌上,用一条长长的布条把脚裹紧,每个裹脚的女孩都要经历骨头变形的红肿和难忍的疼痛,几个月后,扭曲的脚趾开始成形,逐渐变成脚背拱起,脚心凹陷,脚的长度也因此不会再长。
奶奶最终还是受不了这种炼狱般的折磨,在裹脚还没定型之前,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彻底放弃了她的“三寸金莲”之梦。奶奶的脚也因此成了“解放脚”。“解放后”的脚板,上山下地,行走自如。
奶奶说,有的女孩子不想缠足,就一直哭,无奈拗不过只得把足缠上。我佩服的是,奶奶没缠足,这与她的抗争与能干是分不开的。奶奶做事干活利索,家人对奶奶也是有爱的,只是生活所迫,加上旧社会重男轻女,即使是亲闺女也要劳动,何况我奶奶是童养媳。奶奶从小就要干许多超出她年龄的重活,洗衣烧饭,针线活儿,打猪草、煮猪食、喂猪养鸡养鸭等等,她的童年应该是非常苦的,除了睡觉,她就像机器一般带着饥饿麻木不停地劳动。劳动,贯穿了她的整个童年生活,在生活的窘迫困苦中感受欢乐和阳光,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现实生活中,灾难就像魔鬼一样时时潜伏于身边,它会在人们毫无预感的状况下,突然发起致命的攻击,让人在猝不及防中大祸临头。爷爷55岁时确诊身患肺癌。虽经多方求医治疗,爷爷还是走了,什么也没留下,甚至连一张可以怀念的照片都没有。
爷爷的早逝,奶奶的顶梁柱轰然倒塌。这是一个注定要经受生死磨难、历尽千辛万苦的不平凡家庭,只有与残酷命运作不懈抗争才是唯一的生存之路。人在危难之中看担当。奶奶虽然外表瘦小柔弱,但是她的内心却是异常坚毅刚强。此时,我大伯已在重庆参加工作,父亲已在农村成家。奶奶带着6个还未长大的孩子,独撑家业。奶奶性格温和善良,能吃苦耐劳,任何苦难、悲伤、繁忙、绝望,都不曾把她压垮。在她身上仿佛蕴藏着一种惊人的能量。奶奶虽然没读过书,但她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她省吃俭用,供孩子们读书。她坚信,唯有读书才是农家子弟的出路。
年复一年,她凭自己勤劳的双手,先后把三叔、四叔和幺叔送出大山,他们也走出了属于各自的人生道路。在那个贫瘠困苦的时代,他们相互扶持,同食一锅饭,随着历史沿革、社会动荡与时代变迁,上演无数的欢乐、悲伤、烦恼、纠葛……
我小的时候,夏天的夜晚,在奶奶家旁小地坝的杏子树下歇凉,透过婆娑的树影,看深邃的夜空中眨着眼睛的星星,坐在身旁摇着蒲扇的奶奶说,“七夕”的夜晚,如果有星星,站在葡萄架下的井口边,就可以听到牛郎和织女的对话……而在七月的那一天,我真的去到葡萄架下,也似乎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们的呢喃细语……
时间如沙漏,一张张曾经轮廓分明的面孔,在凛冽的寒风中逐渐模糊,一个个和蔼慈祥的亲人,已经变成了山野间的一个个土堆。
她们的旧事,连同对她们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正被覆盖。我有时在想,一代人逝去了,便留在下一代人的记忆当中,而当下一代人也逝去,这记忆就破碎了,变成一些碎片,被后代拾捡着。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家族的故事,虽各不相同,但都书写着人世间最伟大的两个字——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