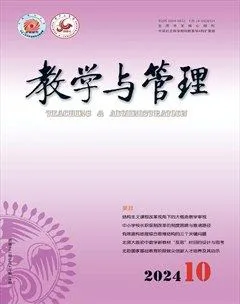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视角下的大概念教学审视
大概念教学与结构主义课程改革颇有相通之处。回望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观照其知识观及方法论,重访“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能否像专家一样思考”等命题,有助于审视并反思当前正在推行的大概念教学。基于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要有效开展大概念教学,应做到:目标指向上,重视学生真实性迁移能力培养,注重学生真实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教学内容上,把握好科目与学术的边界,平衡认知与经验的关系;教学实施上,开展跨学科结构化教学,践行真实探究,但也要警惕唯结构化,避免程式化、虚假性探究。
大概念教学;结构主义课程改革;核心素养;专家思维
李志远.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视角下的大概念教学审视[J].教学与管理,2024(28):1-5.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聚焦核心素养,强调课程内容内在联系,突出课程内容结构化[1]。核心素养的落实需要具体课堂的依托,课程内容结构化更需要体系性的教学设计,为探求联结两者与日常教学之间断层的桥梁,学者们将目光转向大概念教学。
以大概念推进结构化学习的构念,可追溯至美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开展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2]。这场教育运动未取得预期效果,但并不意味着这场改革一无是处。我们知道,课程改革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既有课程实施权力、政治意愿等外部因素,也有目标、内容、组织等内部因素,其成功与否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这次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中的一些先进教育理念对后世还是产生了积极影响。面对当前各学科都在开展的大概念教学,不妨把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当做一面镜子,学习借鉴其优点,警惕并改进其不足。为此,本文在反思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基础上,从为什么、学什么、怎么学三个层面,观照大概念教学倡导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助推大概念教学在超越中不断发展,为当下课程改革提供思考。
一、教学归旨:让核心素养更好落地
“核心素养”作为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中极具创新性和阐释力的关键词,反映了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基本发展要求。大概念教学作为素养导向下的教学转型,肩负着落实核心素养的任务。结构主义课程改革提倡以探究为底色的精神底蕴,但并未激发学生持久的兴趣与热情[3]。结合时代背景反思其误区,我们认为大概念教学应理性看待迁移难度,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
1.重视真实性迁移能力的培养
大概念教学重视迁移对学生学习的作用,这与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可谓同声相应。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倡导者布鲁纳(J. Bruner)把迁移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特殊迁移,指对未来有直接帮助、无需转换便直接运用的知识与技能,例如计算、识字等;二是非特殊迁移,即借助由学科基本原理与结构组成的“一般概念”进行情景调度、知识重组[4]。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强调非特殊迁移,但有学者认为这种迁移能力实为“算法思维”[5],并未脱离特殊迁移的局限。因为学生仅仅将已知原理嵌入陌生环境,教师通过所教内容为学生配备工具箱与路线图,学生只需进行信息匹配和利弊权衡,将已知放入未知,从而完成所谓的迁移,实为引导下的信息运用。依靠将已有知识概念化、结构化,学生或许可以在对应场合及时精准输出,但高质量的迁移并非“识别—提取”的重复过程,而是在应用中升华已知、提炼新知。灵光乍现的背后,是学生具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陌生化程度更高的环境中,以基本结构为工具,从中提取特定经验,与现实场景拼合重组。其间会有混乱、疑惑与迷茫,但屡经失败之后,学生会自己搭建出解决框架,以及灵活地填充所思所想。这其中的联结键便是直觉性思维,因此真实性迁移能力需要创新思维的依托[6]。高水平迁移需要创新,但创新需要大量的案例积累与经验支撑,这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并不容易实现。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中对迁移给予的不切合实际的期望,或许是导致课程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今大概念教学言必涉及迁移,似乎每次教学都可完成一次从课堂到生活的转换,但其真实性与创新性是否经得起推敲尚须具体分析。大概念教学应在话语中分清迁移与任务,避免对迁移能力口号式的目标追求,并警惕速成性的效果证据。固然,大概念的上位“透视”与统摄能使得知识学习跳脱浅层化、机械化的窠臼,得以实现深度组织,为创新提供可能[7]。但我们应明白课堂教学存在空间、时间等场合局限,能够实现高水平迁移的教学还需要学生能力的高度匹配。这并非否定大概念教学的迁移价值,而是要合理对待迁移难度,将迁移作为大目标,而非小环节;摆脱所学立刻变为所用的功利思维,给学生自由的创生空间。
2.注重学生真实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主张发现学习,布鲁纳将其概括为“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开展活动、评价验证、发现结论”[8],涉及大量的学生行为活动。学生在课堂上似乎有丰富的学习体验,寓教于乐、合作教学,但理查德·梅耶(R. Mayer)等学者却持否定态度[9],因为尽管学生可能在动手操作中很活跃,但缺乏认知活动,无法引导他们进行深入的理解,难以促进有意义的学习。进而言之,学生在发现学习中的活动被限定在板块推进中,五步法流程在起点与目标之间事先画好直线,相当于给学生提供了步骤图,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主体性、反思性和生成性。
课程是一段连续的过程,而非最后的结果,因此应注重学生真实且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大卫·库伯(D. Kolb)提出体验学习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10],描述了学生通过体验来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由具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积极实验四个阶段组成。其中,“具体体验”是学习过程的起点,“反思观察”是对自我体验的内省与思考,“抽象概念化”是建构概念的认知过程,“积极实验”则是在新情境中通过实践来验证和改进自我理解。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动态的学习过程,个体能够不断地从体验中学习,并将所学应用到实践中,从而实现知识和能力的持续发展。
体验学习圈的循环离不开学生的情感体验,诸如发现时的喜悦感、思索中的求知欲、遇挫时的沮丧感、解决后的成就感,这些宝贵的体验提升学生的自身兴趣,促使学生主动搭建认知结构,而非被动地进行“去自我化”的程式学习。应关注学生主体性带来课堂的流动感,学生间、师生间的关系特征会随着交流不断变化。正如德勒兹(G. Deleuze)在根茎理论(rhizome theory)中以树与根茎的复杂交错关系来隐喻人、时间、空间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11],任何一个点都可以连接到任何其他的点,它既无开始也无终结,总是在一个不断延续的环境中生长和分化,学习体验也并非固有内容的映射、铁板一块的输出,而是个体在动态互动中的吸纳与成长。从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角度来看,大概念教学应注重学习经历,在个体经验中提升核心素养。
二、教学内容:最有价值知识的习得
工业革命之际,斯宾塞(H. Spencer)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首次将学习的代价论推向前台,知识的学习具有机会成本。结构主义课程改革推崇知识,开发学术中心课程,强调知识的学术性,却效果欠佳。在目前大概念教学热潮下,能力、素养话语不断升温,甚至强调全程情境化、统领大单元,在一片“大”字当头中,语文课无暇顾及炼字炼句这些小问题[12],物理课追求项目式任务,“反知识”舆论似乎初露端倪。然而,这似乎背离了大概念教学的初衷。王荣生认为大概念即“核心的概括性知识”,追求基本问题间的相互联系,指向探究理解[13]。由此可见,“大”并不一味追求高屋建瓴,而淡化具体知识会导致认知基层不稳,知识不应被污名化。特别是在当下面临知识生产机制的转型,教学内容的价值选择决定着大概念教学的时代价值。基于这一背景,通过反思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知识观,我们认为要探讨大概念教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应在科目与学术知识、学生认知与经验等方面做出权衡与考量。
1.把握科目与学术的边界
知识是教育体系的输入端,对大概念教学的探讨不能脱离当前的知识生产框架。大概念作为舶来品,由学术界引至实践圈,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不免让人想起学校科目(school subject)与学术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的关联。如果大概念教学的目标是知识点的网格化,那么便易于转化为学术基础导引,呼应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学术中心课程。
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由学科专家主导,认为教师应首先理解学术学科的基本结构、原则与方法,然后才有能力教授相应的学校科目,而课程专家完全失势。这背后呈现的便是学校科目源于学术学科的观念,被斯滕格尔(B. Stengel)称为“连续性”关系[14]。学科基础无疑是教师的基本功,但其在多大程度上源自学术存在争议。以结构主义课程改革所关注的理科为例,科学前沿的关注点向来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中,这不仅与学习深度不匹配,更在于两者底层逻辑的差异。学术学科追求开拓知识边疆,因此在某一特定领域不断挖掘并寻求突破,而学校科目重视已有知识的掌握运用,因此学科优等生多以能解决压轴题、思考题为目标。高深的学术知识难以显性赋能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教学,甚至无用武之地,这也解释了为何如今诸多高校将以一线教师培养为目标的专业硕士点设立在教育类院系,而非对应的专业院系。
此外,不同学校科目与学术学科之间的偏离度也大有不同。亚里士多德将学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性学科,追求永恒真理;第二类是实践性学科,关注生活决策;第三类是生产性学科,设计创造技能[15]。从第一类到第三类,学科实质结构的稳定性大致呈弱化趋势,学科外延的弹性增强,更加强调发散性的演绎,因而在以基础性为核心的基础教育阶段中,不同领域的学术学科和学校科目之间的连贯性差异较大。例如,在数学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16],还是高中阶段的“数学抽象、逻辑推理”等核心素养,都反映了数学领域的专家思维。而在外语学科中,“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与外语类相关专业中的审美鉴赏、国别发展史等核心课程大有不同。理论性学科以基础教育为根基,体系严密、壁垒森严,故而发展脉络清晰;而在生产类学科中,架构松散、交融互通,呈现绵密铺张的涵括性。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课程学者支持的“连续性”关系不仅难览课程内容全貌,而且最终的结果是教师不能胜任教学,学生难以有效学习。因而大概念教学应慎重引入前沿学术成果,它可作为科普内容以拓宽视野,但不能追求尖端、高超的靶子。依照科目特性,紧扣课程目标,不违逆但不囿于学术研究,择取的知识果实才能充分实现教育价值,发挥育人的自主性和选择权。
2.平衡认知与经验的关系
大概念教学强调学科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指向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在教学中不断建构鲜活的核心概念,形成与生活相连的活水。然而,真实性与经验化之间不全然相等,如果教学以学生经验为指挥棒,则有实用主义之嫌;诸多知识虽不能满足学生需求,但却会构成心理图式,待日后补充养分。
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剔除外部因素干扰,大刀阔斧调整基础内容,如“新物理”“新生物”等课程一反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社会与儿童经验的关注,从学习科学角度调整为规整的学科知识。这种纯认知取向的课程内容对于学生的基础学习有促进作用,适合学生记忆、理解、强化等诸多进程,以最具“性价比”的方式吸纳核心知识,但同时也使得知识成为了现实绝缘体。知识产生于人类集体的实践总结,这背后的动力正是源源不断的现实问题和无数被吸引着去解决困境的智识卓见。
核心素养下的大概念教学也应融合认知与经验,既以科学的视角审视学习的发生,又观照学生自身,放眼学生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平衡贯通与分离的程度是把握教育与外在世界关联的重点。大概念教学应着力打造课堂的理想样态——既立足于实,保持关怀的态度与多样的视角,扎根于社会土壤,避免成为书斋的学问;又不拘于实,以期待的目光看待每一位参与的学生,激发他们对于当下的具身感,进而培养其超越现实的价值目标,形成持久的精神养料。
三、教学实施:像专家一样思考
大概念教学和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均寄予学生“像专家一样思考”的课程理想。布鲁纳制定了五步法、螺旋式结构等具体步骤,但并未收获如期效果。结构性和探究性是深度学习得以开展的有效锚点,也符合当前学习理论的研究成果。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经验也能帮助我们思考大概念教学中如何更好地赋能学生专家化思维。
1.开展跨学科结构化教学,但警惕唯结构化
目前有多个学科组成的课程体系犹如一栋高楼大厦,但内部的复杂构件(各个学科)却彼此以铜墙铁壁相隔而立,哪怕有极高相似度的化学与生物学科,即便有着相同的知识内容,也都在各自的框架中被定义和阐释,没有考虑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所应具有的思维一致性:不同学科分门立户,只管自己的四方天地,这种以学科结构为主脉络的教学会造成学生高度分隔的世界观[17]。这样的危害在于学生只能在高度理想化的学科真空中进行思考与解题,但当面对根脉交错的现实问题时却缺少了学科类属的标识,只能茫然无措。
结构化意味着对学科的提炼规整,取其支脉,呈现出学科内部及学科间的清晰脉络。关注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贯通知识网络,使学习体系化,甚至可视化,如同锚点般嵌入学生的学习过程,正如布鲁纳所言“学习结构就是学习事物是怎样相互关联的”[18];另一方面也使学习过程更高效,如同搭积木,垒砖砌瓦直奔图纸样板,没有四处拉扯的漫游,也无需添油加醋地点缀。
大概念教学摆脱碎片化的泥淖,以体系化的结构落实核心素养。大概念作为凝聚点,融汇单元与课时,成为统领单元整体教学的支点,贯穿单元的主题或核心思想,将教学活动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条理、连贯的学习框架,以完整的学习体验弥补了课时教学的分散、单元分离的编排。大概念的诸多隐喻,例如锚点、车辖、衣架、建筑材料等等,都表明大概念承担着统领学科内部或学科间知识体系的角色,打破课程单元进行教材重整,突破课时教学观,进行较长周期的系统化设计与合理的课时分解[19]。
大概念教学提倡结构化教学并不意味着结构化至高无上,凡事都要结构化。首先,结构化对不同学科难度不一。“数学和物理可以进行相当彻底的结构化,但是历史和文学的结构化,要那么彻底地进行是困难的。”[20]在高考复习中,理科科目的复习框架便是对所学知识的分类突破,高度吻合学生的学习历程,无论是在日常课还是复习课,块状化的知识都一以贯之;但文科科目,如语文,在最终复习时总给学生“如梦初醒”的感觉,现代文阅读、应用文写作等模块下列出了清晰的条目,但这与日常的课文教学并没有强而有力的对应关系,甚至不具备清晰的年级属性。例如语文的高考复习策略大多是应试导向下知识点的逐个突破,但就学科本质来说是否能够结构化也值得考虑。
吉鲁(H. Giroux)便将这种结构生成过程比喻为“硫酸浴”[21],认为强行的结构化会导致学科逻辑的生硬构造。因为在结构为上的语境下,相对松散的人文艺术等学科会被撕去合法化的标签而受到忽视,因此为了学科地位,只能削足适履,乃至曲意迎合。另外,体系化的知识就像是被分门别类地规整好的菜品,它首先要吸引学生的胃口,让学生从主观意愿上接纳,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以学生为中心,而是兼顾学生的主体性,将学习视为互动,将课程视为建构在合适的生长点上的有效教学。
因此,应加强不同学科的教师交流,避免各自为营的状态。施瓦布(J. Schwab)提出学科间的组织结构,关注学科间彼此关联的样态,因为良好的课程排列会以学科群的组织为学生提供看待同一事物的多样视角,如同棱镜般多维深入地发现学科立体性的不同面相。同时,大概念教学也应尊重学科知识结构,关注学科差异性。我们强调结构化,但排斥唯结构化,课堂不应单纯追求目标的线性达成,而应该敞开、纳入并思考这些迂回的、不明朗的但真实发生的学习体验。具体知识内容的教学并不落伍,而是结构化的基础、原料和参照。
2.践行真实探究,避免程式化、虚假性探究
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中的发现学习之所以失败,程式化的过程难辞其咎。布鲁纳试图让学生在课堂中模仿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探究过程,但科学家在实验中要面对不断失败甚至无果而终的不确定性。教学中不确定性的弱化严重削弱了真实探究的核心要素,正如卡普尔(M. Kapur)的“有效失败”概念对劣构问题的重视,为学生制造失败的机会,并引导学生“向失败案例学习”,通过曲折的教学设计有效教学[22]。发现学习使得科学结论成为已知靶标,精准射击的发现过程在碾平阻碍的同时,也无形中降低了发现的价值。其次,发现学习所带来的探究活动也容易造成貌合神离的虚假探究。布鲁纳为发现学习设置了螺旋式课程编排,其背后是对认知结构依照“行为表征、图象表征、符号表征”进阶发展的心理学认识。但发现学习并非适应这种非线性认知规律的各个阶段,在低年级,感性方式可以使学生获得体验,并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抽象化,在重复中不断深化所学。低龄的学生由于基础过低,需要教师搭建过多的脚手架,换言之,过早的发现学习可能超出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相比起直接讲授可能并无过多优势。即便是高年级的发现学习,也容易导致以探究之名包装的过程演绎。
目前正在推行的大概念教学倡导“像专家一样思考”,但仍可窥见虚假的身影,例如物理等学科的实验操作,多为按照课本的步骤体验一番,并未留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真正探索发现,而考试中常考查操作过程中细枝末节的知识,从而使实验操作沦为知识理解,学生只是熟练掌握了规定动作,并未在探究中发现新知。针对这一现状,有专家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从科学家的探究活动到一种学习方式间的理论空白,只是笼统地按图索骥,没有有效转化、启迪创智[23]。这种所谓的探究或许确保了学生可以表面上“像专家一样思考”,但本质上仍是传统的授受活动。的确,我国传统教育更注重结论性知识,相比西方的学法,更关注教法,学生自然也习惯听老师讲。有鉴于此,大概念教学应依据学科特性,给予学生适当的自由空间,让学生真正产生疑惑并发现问题,例如道德与法治课可以实行议题式教学,语文课堂进行群文阅读,教师提供适当支持,由学生完成资料检索、路径选择等关键步骤。其次,教师还要扭转学生传统的学习心理,不仅从技能上教给学生如何讨论、汇报、交流,掌握这些方面的基本能力,更要让学生学会聆听与尊重,发现经验互动的珍贵与独特,由此才可养成探究精神,感受所谓的专家心路及专家思考。
结构主义课程改革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课程观念,不能全盘否定,我们仍要看到它在当今课程改革中的身影与启示。大概念教学吸纳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进步理念,反哺当下,我们应在把握“如何让核心素更好落地”“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怎样像专家一样思考”等本质问题后,理性反思,让大概念教学更加有效率、有效能、有效果。
对于大概念教学,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全局性优势,又要看到它的局部性不足。若学生的学习心路中大概念的路标林立,学生自然可以领悟全貌,将全局了然于胸,但可能同时会忽视了身边的一花一草,这些细节性知识正是全局理解的血肉根基。大概念教学也需要与之相配的大概念评价体系。若只在教学中强调大概念的优势,而忽略了细节性知识,则会让一线实践大打折扣。另外,大概念教学不应盲目地用于所有教学实践,而应在实践中探索,在总结中优化,做到稳步推进。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1.
[2] 梁秀华,王向东.以大概念推进结构化学习:构念溯源、素养功能与协同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23(02):36-41.
[3] 袁慧芳,彭虹斌.20世纪中期美国科学课程改革及其成效[J].教育学报, 2009,5 (05):72-77.
[4][18] 布鲁纳.布鲁纳教育论著选[M].邵瑞珍,张渭城,何光荣,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31,24.
[5] Rohstock,A.Mapping Scientised Education in German-American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fter 1945[J]. History of Education,2021(03):395-412.
[6] 褚宏启.核心素养的概念与本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34 (01):1-3.
[7] 胡嘉康,田莉.指向深度学习的数字教科书设计:内涵重塑、应然路径与实践策略[J].远程教育杂志,2023,41(05):104-112.
[8] 钱佳宇.布鲁纳的发现式学习与研究性学习的比较——对布鲁纳的发现式学习的反思[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08):55-58.
[9] Mayer,R. E. Should There Be a Three-Strikes Rule Against Pure Discovery Learning The Case for Guided Methods of Instruction[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2004,59(01):14-19.
[10] Kolb,D. A.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M].New Jersey: Pearson FT Press,2015:51.
[11] 郭世宝,刘竞舟. 加拿大华侨华人新生代大学生的中文教育、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J].比较教育研究,2024,46(03):52-62.
[12] 任海霞,管然荣.课文尚需“篇篇读”——对“大概念大单元教学”的认知与反思[J].中学语文教学,2021(04):8-12.
[13] 王荣生.事实性知识、概括性知识与“大概念”——以语文学科为背景[J].课程·教材·教法,2020,40(04):75-82.
[14] Stengel,B.S.“Academic Discipline”and“School Subject”:Contestable Curricular Concepts[J].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1997(05): 585-602.
[15] 肖龙海,洪晓翠.教“学科基本结构”?——西方六十年来对结构主义课程假设的省思[J].外国教育研究,2023,50(12):3-15.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5-6.
[17] Smith,R.A. Patterns of Meaning in Aesthetic Education[J]. Bulletin of the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Music Education,1965(05):1-16.
[19] 郭绍青.教育数字化赋能新课程实施与教师培训转型策略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23(07):51-60.
[20]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32.
[21] Giroux,H.A. Critical Theory and Rationality in Citizenship Education[J]. Curriculum Inquiry,1980(04):329-366.
[22] 刘徽.“大概念”视角下的单元整体教学构型——兼论素养导向的课堂变革[J].教育研究,2020,41(06):64-77.
[23] 崔允漷,张紫红,郭洪瑞.溯源与解读:学科实践即学习方式变革的新方向[J].教育研究,2021,42(12):55-63.
【责任编辑 孙晓雯】